关键词:文学;汉字;字生性
内容提要: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关于“文学”的界定最为语义歧出:既有古今中西之异,亦有广义狭义之别。诸多关于“文学”的定义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能通约中西、融贯古今并兼顾广狭。就汉语“文学”而言,广义的“汉字”(包括“文”“名”“言”“辞”等),在文学的产生、生成乃至生生不息的发展之中,扮演着“文”明以健、“名”正言顺、一“言”九鼎、“辞”动天下之角色。字,孳乳也,文字乃经艺之本、文章之始,自文字至文章,本立而道生。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学作为人的创制,是用语言文字显示自然之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文学能鼓天下之动、成天下之美,缘于文字的孳生之力、哺乳之功和生生之德。追问并验明文字与文学的血缘关系,揭示汉语“文学”的字生性特征,可为“文学”的释名彰义提供新的路径。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项目号:12&ZD153)的阶段性成果。
刘勰(约465~521)《文心雕龙·序志篇》为其文学理论批评自订四项原则:“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①其中“释名彰义”是最为基本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文学的定义尚未厘清,文学的追源溯流、识深鉴奥从何谈起?而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其语义歧出、情志纠结之处正是关于“文学”的释名彰义:既有古今中西之异,亦有狭义广义之别。当学界为着各种关于“文学”的定义而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之时,却忘记了几乎所有的文学教科书都会提及的一条常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以为,这条常识性定义既可通约中西亦能融贯古今还可兼顾广狭。《文心雕龙·原道篇》对“文学”的释名彰义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心”不是文心而是天地之心即人,这里的“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即文字。有了人就有了文字,有了文字就有了文学,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当然,西学背景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先在性存有学科预设:“文学”与“语言”分属不同的学科;再往下,“语言”与“文字”亦须囿别区分。20世纪初,随着西方哲学及文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文学”与“语言”的壁垒被拆解;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思潮兴起,“语言”与“文字”相互越界。在索绪尔(1857~1913)那里,文字与语言还是外与内的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表现②;而到了德里达(1930~2004),其《论文字学》解构外/内二分,认为“文字并非言语的‘图画’或‘记号’,它既外在于言语又内在于言语,而这种言语本质上已经成了文字”③,故“文字学涵盖广阔的领域”,甚至可以用文字学替代语言学,从而“给文字理论提供机会以对付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压抑和对语言学的依附关系”④。逻各斯中心又称语音中心,声音使意义出场,不同于汉字的书写使意义出场。
当我们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来讲汉语“文学”时,也是可以用“文字”来代替“语言”的。个中缘由,除了受德里达后现代立场的启示,更为基本的是出于对本土前现代学术传统的理解。口诵之语言与笔书之文字,在西方并无太大差别,故他们的语言学也就是文字学。汉语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唐兰(1901~1979)《中国文字学》指出:“中国文字是注音的,语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时期就已经不一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所以,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而中国“从纪元以前就有了文字学”(西汉人称之为“小学”)⑤。因此,对于汉语“文学”而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与“文学是文字的艺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这一点,正是我们讨论汉语“文学”字生性特征的学理前提。
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
在汉语“文学”已经遭遇现代化(西化)的20世纪初,章太炎(1868~1936)给“文学”做出如下界定:“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⑥从字面上看,章太炎似将“文学”与“文字学”等同;究其奥义,则是从源头(竹帛)处找到汉语“文学”与“文字”的内在关联。按照陈梦家(1911~1966)的说法,汉代以前“文字”的名称经过三个时期:首称文字为“文”(如《左传》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和“于文皿虫为蛊”),次称文字为“名”(如《论语》“必也正名乎”,皇疏引郑注“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末称“文”“名”为“文字”(如秦始皇《琅琊台刻石》“同书文字”)并沿用至今。⑦章太炎亦称“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可见文字包括了“文”“名”“言”“辞”等,故本文探讨汉语“文字”与“文学”的关系,对“字”的使用是广义上的:在文学的产生、生成乃至生生不息的发展之中,汉语的文字扮演着“文”明以健、“名”正言顺、一“言”九鼎、“辞”动天下之角色。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的“文学”定义,还就“文”与“彣”,“文章”与“彣彰”之关联作出辨析:“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⑧“推论文学,以文字为准”,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讨论“文学”的一大传统。这里的“准”既有标准、法式之义,亦有本根、源起之义。刘勰著《文心雕龙》,专门辟有《练字》一篇,叙述“字”的历史,表彰“字”的伟绩,楬橥“字”的诸种功能。《练字篇》论“字”从苍颉造字说起:“苍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苍颉造字是华夏文明史上伟大的文化事件,动天地泣鬼神,孳文明乳文化。汉字的历史也就是汉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历史,汉字的功绩也就是汉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功绩,故《文心雕龙·序志篇》讲文学之功德时称“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亦即《练字篇》所言“官治民察”。刘勰之前,东汉许慎(约56~147)《说文解字·叙》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赜)而不可乱也’。”⑨许慎“故曰”所引两段文字,前者出自《论语·学而篇》,后者出自《周易·系辞上传》。由此可见,从《论语》到《易传》,从《说文解字》到《文心雕龙》,中华元典对“字”之文学及文化本根义的体认是一以贯之的。
《文心雕龙·练字篇》称“字”乃“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汉语的方块字是言语的生命体,是文章的宅基和家园。《尔雅》有“言者,我也”,“我”以何“言”?字,故《练字篇》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无言,心何以托?无字,言何以寄?《文心雕龙·章句篇》赞“字”,称其“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亦即许慎所言“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字乃统末之“本”,驭万之“一”。《章句篇》胪列“立言”的四大要素(字、句、章、篇),“字”居其首,“字”立其本:“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无论是单篇的文章还是整体的文学,其创制孳乳,其品赏识鉴,只能从一个一个的方块“字”开始。⑩在源起与流变、创作与鉴赏、传播与接受等多重意义上,“字”皆为文学之“始”或“本”,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字生文学”。
许慎《说文解字》对“字”这个汉字的解释是“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段玉裁(1735~1815)注曰:“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引申之为抚字,亦引申之为文字。《叙》云:‘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11)字者,孳乳也。“孳”是生孩子,“乳”是哺孩子。由“字”我们想到“孕”,两个汉字都是会意:“孕”还只是十月怀胎,“字”则不仅是一朝分娩,更是含辛茹苦地将孩子抚养成人;“孕”还只是怀一个(胎)孩子,“字”则是生产并哺育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引而伸之,则表明一个字可衍生出许多个词和短语。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叙》“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作注时,还将“字”拿来与“名”和“文”相比较,先讲“名者自其有音言之,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之”,后说“独体曰文,合体曰字”,强调的都是“字”的“孳乳”“浸多”“滋生”“合体(再造)”之功能。
当然,许慎和段玉裁说“字”,还只是在小学(文字学)的场域内讨论“字”的孳乳性或繁衍力。如果我们将“字,孳乳也”放在广阔的文化领域,来追问并验明“文字”与“文学”的血缘关系,则不难发现汉语“文学”的字生性特质。《文心雕龙》开篇“原道”,追溯“文学”之本原与起源,《原道篇》在为“文学”释名彰义即解决了“文学”的本原问题之后,继之回答“文学”的起源问题:“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皋遗事,纪在三坟”,从“唐、虞文章”到“益、稷陈谟”,从夏后氏“九序惟歌”到周文王“繇辞炳耀”,从周公旦“制诗辑颂”到孔夫子“熔钧六经”,刘勰为我们描述的这一部上古文学史,分明滥觞于“文字始炳”,分明嬗变为文字的“符采复隐,精义坚深”,又分明完成于先秦圣哲的“组织辞令”“斧藻群言”。
《原道篇》的上古文学史在论及商周文学时,称“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这是伟大的《诗经》时代,这是辉煌的风雅颂时代。商周始祖的“英华”纪录在《雅》《颂》文字之中。商的始祖是契,契建国于商;周的始祖是后稷,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再往上追问:契乃谁生?姜嫄如何生后稷?幸好,我们有《诗经》的文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生民》说“(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玄鸟生商(契),姜嫄履帝之足迹而生后稷,这是《诗经》的文字所记录的商周历史。就史学的真实而言,玄鸟不可能生商(契),姜嫄亦不可能履帝迹而生后稷;就文学(神话与传说)的真实而论,“玄鸟生商”“姜嫄履帝迹生后稷”则不仅是“真”的,更是“美”和“善”的。而关于商周始祖的真善美的历史,与其说是《诗经》的文字所记录,还不如说是《诗经》的文字所创造。关于“字生文学”的例证,除了“玄鸟生商”和“履帝武敏歆”,还可以举出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皇英嫔虞、伏羲画卦、苍颉造字……中国文学史上这些动天地泣鬼神的壮美故事,这些孳文明乳文化的伟大事件,无一不是我们的方块字所创造出来的。字生文学是也。
“文字”和“文学”的“文”,被许慎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12)。东汉的许慎虽读过《庄子》却未见过殷商卜辞,故不知道这个“文”就是《庄子·逍遥游》的“越人断发文身”之“文”。甲骨文中的“文”,从武丁时期到帝辛时期,均有“文身”之义:“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13)纹身所具有的符号性、象征性、修饰性、结构性和文本化,使得“文”这个独体象形的汉字成为人类最早的文学艺术作品之一,亦成为汉语言“字生文学”的最早例证之一。如果说,人在自己身体上的交文错画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创作行为,那么“以文身之纹为文”则是人类最早的文学鉴赏和批评行为,是人对“字生文学”的自觉鉴赏和批评。交文错画着形形色色之“文”的龟甲兽骨,虽然被掩埋在殷商帝辛的废墟之中,但“字生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的特征却生生不息,历经数千载而不朽。我们今天从文明、文化、文字、文辞、文献、文学、文章、文艺、文采、文雅等众多中国文论的关键词之中,从诗、词、歌、赋、曲、文、说、剧、碑、诔、铭、檄、章、奏、书、记等各体文学作品之中,不难窥见掩埋在殷墟小屯的“字生文学”之文化元素及文学景观。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文学”与“文字”都有一个“文”,“文”既是独体象形的上古汉字的典型代表,也是字生文学的典型例证。《文心雕龙》以“文”肇端(《原道篇》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以“文”终章(《序志篇》末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可谓始于“文”而终于“文”。《原道篇》追原“文学”之“元”(原本与源起),在很诗意也很哲理地阐释了“天文”和“地文”之后,水到渠成地引出“人文”即“文学”的定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天地之心)诞生了,“字”(语言文字)才会被发明被创立;语言文字创立之后,“文学”才会彰显、彰明、刚健、灿烂。作为天地之心的“人”,以自己所独创的“字”(“文”“名”“言”“辞”等),去彰明“自然之道”,这一彰显的过程、结果及其规律就是“文学”。如果说,《原道篇》“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章句篇》“人之立言,因字生句”、“振本末从,知一万毕”讲的都是文字对于文学之产生即历史起源的决定性价值,那么这里的“心生言立,言立文明”讲的则是文字对文学之生成即逻辑本原的规定性意义。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亦借刘勰“心生言立,言立文明”论汉语“文学”的本原、起源及流传,其首篇《自文字至文章》讲文字乃文章(即文学)之始:“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之人易之以书契”,“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14),连属文字而成文章,即刘熙《释名》所云“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字生文学是也。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讲人生在世须做三件事:活着,工作着,说(书写)着。(15)人的工作,制作出各种文化产品,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而只有当人类用文字“立言”之时,才真正创造出“人之文”。或者说,人类只有凭藉“立言”这种文化行为,才能创造出“言立”的文学。《左传》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德”和“功”的历史传承而言,前人如何垂后?后人如何识古?立言。何以立言?言寄形于字,因字而生句。故刘勰的“心生言立,言立文明”是对汉语“文学”字生性特征的高度概括。
汉语“文学”一词有文献可征者,始见于《论语·先进篇》:“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前551~前479)的这两位高足,既不创制诗歌更不杜撰小说,何来“文学”之名?杨伯峻(1909~1992)《论语译注》将此处的“文学”释为“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16)。中国古代,小学(文字学)是经学的根基(故十三经有《尔雅》),经学家首先是小学家(字乃经艺之本)。《世说新语》据《论语》孔门四科而列“文学”门,叙述的是马融(79~166)、郑玄(127~200)、何晏(?~249)、王弼(226~249)、向秀(约227~272)、郭象(252~312)这些学者注经的故事。精通小学和经学的大师们,统统被划归于“文学”之门。
夜梦仲尼以孔子为精神导师的刘勰本来是要去传注儒家经典的,但他觉得自己在经学领域很难超过马融、郑玄,就转而去撰写《文心雕龙》,其《序志篇》坦陈:“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可见以“敷赞圣旨”即弘扬孔儒文化为人生理想的青年刘勰,实际上是从经学(包括小学)切入文学研究,或者说是从经学(包括小学)与文章(即文学)之关系入手建构其文学本体论。以五经为标准来考察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刘勰很容易发现“(时文)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坚守儒家文化的经学立场和小学本位,青年刘勰敏锐地看出他的当代文学(时文)在“言”“辞”“文”(即语言文字)方面出了大问题,而问题之要害则是严重背离了儒家五经“辞尚体要”的传统:“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批判当代文学的“言贵浮诡”,回归儒家经典的“辞尚体要”,竟然成了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文化—心理动因。
如果说《序志篇》是在“文心(为文用心)”的深潜层次讲“辞尚体要”,那么《征圣篇》和《宗经篇》则是在“雕龙(创作技法)”的精微领域讨论如何以圣人和经典为师来“辞尚体要”。二者虽有巨细之别,但其经学立场和小学本位(即“字本位”)则是一致的。《征圣篇》连续四次讲到“辞尚体要”,要求文学家学习春秋经的“一字以褒贬”和礼经的“举轻以包重”,其文字方可“简言以达旨”;学习易经的“精义以曲隐”和左传的“微辞以婉晦”,其文字方可“隐义以藏用”;学习诗经的“联章以积句”和礼经的“缛说以繁辞”,其文字方可“博文以该情”……《宗经篇》则针对“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之时弊,大讲特讲儒家五经在“言”“辞”即文字上的优长:易经的“旨远辞文,言中事隐”,诗经的“藻辞谲喻,温柔在颂”,书经的“通乎尔雅,文意晓然”,礼经的“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经的“一字见义,详略成文”……“五经之含文也”,宗经征圣落到实处,是要学习五经的文字功夫即雕龙技法,这也是刘勰撰著《文心雕龙》的用心之所在,苦心之所在。
青年刘勰“征圣立言”的经学立场不仅铸就其文学本体观的“字本位”,同时也酿成其文学史观的“字本位”,即从“字”的特定层面来考察文学的历史嬗变。《章句篇》讲诗歌的演变,称“笔句无常,而字有条(常)数”,诗歌句子的变化似无常规,而(每一句)字数的多少则是有规律可循的:“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在刘勰的眼中,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演变史,落到实处,就是“字”数之多少的应变史:“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明诗篇》对诗歌史的描述,也是以“字有常数”为演变规律的:“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总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诗歌,彼一时代与此一时代的诗歌之异,或短或长,或密或疏,或促或缓,或多或寡,完全取决于字数的或增或减。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著一字而境界全出”,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增(或减)一字则格调迥别、境界迥异,“字”之多寡,岂能以轻心掉之?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周易·系辞上传》讲到《周易》的四大功用,首条便是“以言者尚其辞”(17)。《周易》的言说符号包括了两大系统:卦爻象系统与卦爻辞系统,借用王弼《周易略例》的话说,前者是“象者,出意者也”,“尽意莫若象”;后者是“言者,明象者也”,“尽象莫若言”(18)。但是,“象”之出意尽意,完全有赖于“言”之明象尽象,若无卦爻辞的文字阐释,《周易》那么多的卦爻象究为何意是谁也弄不清楚的。因此,《系辞下传》要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就是象征,象征就是通过模拟外物以喻晓内意,而拟物喻意离开了“辞”是根本无法进行也无法完成的。作为文学修辞手法,象征有两个端点:一头是物一头是意,物何以达意指意或明意?必须有“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套用《系辞下传》的话语模式:文学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艺术”何谓?用“语言”(辞)来拟物(人物、事物、景物等)出意(意义、价值、情志等)。文学生生不息的奥秘在于斯,文学动天地泣鬼神的感染力亦在于斯,故刘勰要借用《周易》的话来浩叹:“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在因“五经皆文”而征圣宗经的刘勰心目中,《周易》无疑是最好的文学之一,故《文心雕龙·原道篇》讲述上古文学史要以《周易》的原创与阐释为主线,所谓“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周易》的创卦者,观物而画卦,“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周易》的观卦者,尚辞而解卦,“观其象而玩其辞”,观察卦爻的象征意味而探究玩味其文辞,或者反过来说,通过品味卦爻辞而领悟其象征及修辞。“辞”对于《周易》的意义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无“辞”何以识训诂?无“辞”何以明象征?无“辞”何以成易道?无“辞”何以定乾坤?
《周易》是象思维和象言说,而《周易》的象思维和象言说,是靠“辞”(小学之训诂加上文学之修辞)来完成的。受《周易》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亦有“尚辞”之传统,笼统而言是讲究“语言的艺术”,具体而论是注重象征、隐喻、比兴、夸饰等文学修辞。《文心雕龙》创作论二十多篇,有超过一半的篇幅是专门谈“字”说“辞”的:属于谈“字”(即讨论语言文字)的篇目有《声律》《章句》《俪辞》《练字》等,属于说“辞”(即讨论文学修辞)的有《比兴》《夸饰》《事类》《隐秀》等,属于通论二者的有如何《通变》与《定势》,如何《指瑕》与《附会》,如何《熔裁》与《总术》。广而论之,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本,数量最巨的是历朝历代的诗话、诗式、诗格、诗法等。明清以降,继海量的“规范诗学”或“修辞诗学”后,又出现热衷于作法和读法的小说戏曲评点。金圣叹《第五才子书》讲《水浒传》的创作是“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19),故“因文生事”是在叙事层面对“字生文学”的经典表述。
《周易》讲“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许慎讲“文字乃经艺之本”,刘勰讲“言立而文明”,金圣叹讲“因文生事”,一直到鲁迅讲“自文字至文章”,均可视为从不同层面阐释汉语“文学”的字生性特征。汉语的方块字孳生了文学,也哺乳了文学,字是文学之母。就“文字”创制与“文学”创造之关系而言,汉字的六书作为“字”的构造规律,深情地也是深度地哺乳了“文学”,并成为“文学”的创作规律。刘歆、班固将“象形”置于六书之首,并将六书前四项表述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20),无意中触到字乳文学之要害。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亦论及“六书”尤其是“象形”与文学的关系:“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21)汉字六书对汉语文学的孳乳,若概而言之,则是鲁迅所言“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22)。若分而言之,其“象形”之“画成其物,随物诘诎”既是汉字区别于拉丁文的标志性特征,也是文学的标志性特征,方块字的象形孳乳了文学的形象性和意境化,此其一。如果说“指事”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养育了文学之“赋”的直书其事,体物写志;那么,“比类合谊,以见指撝”之“会意”,与“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假借”,则分别孳乳了文学的“比显”与“兴隐”,此其二。此外,“转注”的“同意相受”启迪了文学的互文性,而“形声”的“取譬相成”成就了文学的谐音之趣与声韵之美,此其三。至于具体的创作过程之中,文学家如何推敲,如何炼字,如何捶字坚而难移,如何语不惊人死不休,亦可见出“字”对于文学的特殊意义。
本文绪论曾谈到索绪尔视“文字”为“语言”之表现或工具;与此同时索绪尔又不得不承认:“书写的词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23)把书写的词即文字看得比口说的词即言语更加重要,这在表音体系(如拉丁语)中或许不太正常,但在表意体系(如汉语)中却是非常正常也是非常真实的。或许是看到了表意体系的这种独特性,宣称“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24)的索绪尔,却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专门讨论表意体系中“文字的威望”及其形成原因:“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其次,“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第三,“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辞典,自己的语法”,并最终形成自己的“正字法”,“因此,文字成了头等重要的”;“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因为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25)我们看索绪尔从逻格斯中心主义立场出发对“文字威望”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恰好是对汉字这种典型的表意体系的表扬。书写形象的永恒和稳固,视觉形象的明晰和持久,文字威望对语言统一性的塑造和维护,尤其是文学语言如何以“头等重要”的身份来解决文字与语言的矛盾等等,表意体系的这些特征及优长,构成了“字生文学”的文字学根基。
德里达《论文字学》在批评索绪尔对文字与言语作内外之分时指出:“外在/内在,印象/现实,再现/在场,这都是人们在勾画一门科学的范围时依靠的陈旧框架。”(26)而汉语的“文学”从来就不属于某一个科学的框架,即便是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中,文学也并不专属于哪一部;或者这样说:哪一部里面都有文学。就汉语“文学”的源头先秦文学而言,以经艺为代表的文学,用一个一个的方块字(关键词),建构起轴心期华夏文明的意义世界。同为轴心期文明,拉丁语的最小单位(字母)是无意义的,而汉语的最小单位(包括部首在内的字)则能显现独立甚至全息的意义,一字一世界,一字一意境。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方块字既没有被梵化,也没有被拉丁化,中国文学因之亘古亘今,中国文化因之分久必合,故汉语文学是字孳字乳的文学,华夏文化是字孳字乳的文化。汉语的“文学”,其源起是“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其元典是或“一字以褒贬”或“联章以集句”的经艺,其楷模是情见文字、采溢格言、辞尚体要、辞动天下的圣贤文章,其种类是肇于经艺、著于竹帛的所有文体。
字生文学,汉语的字从起源与本原处孳乳了汉语的文学,铸成“文学”的汉语定义。追问并验明文字与文学的血缘关系,揭示汉语“文学”的字生性特征,可为“文学”的释名彰义,为文学批评的选文定篇,为文学理论的敷理举统,乃至为文学史的原始表末,提供新的路径并开辟新的场域。
①本文所引《文心雕龙》,均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不另注。
②(23)(24)(25)[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7、48、51、50页。
③④(26)[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3、70~71、45页。
⑤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⑥⑧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49~50页。
⑦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5页。
⑨(11)(12)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3、743、425页。
⑩民间将作家的文学创作戏称为“码字”,将读者的文学解读戏称为“测字”,亦可见对文学活动中“字”元素的高度重视。
(13)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6页。
(14)《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345页。
(15)[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7页。
(1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17)本文所引《周易·系辞传》,均据[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5~92页,下不另注。
(18)王弼注,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19)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20)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册第1720页。
(21)(22)《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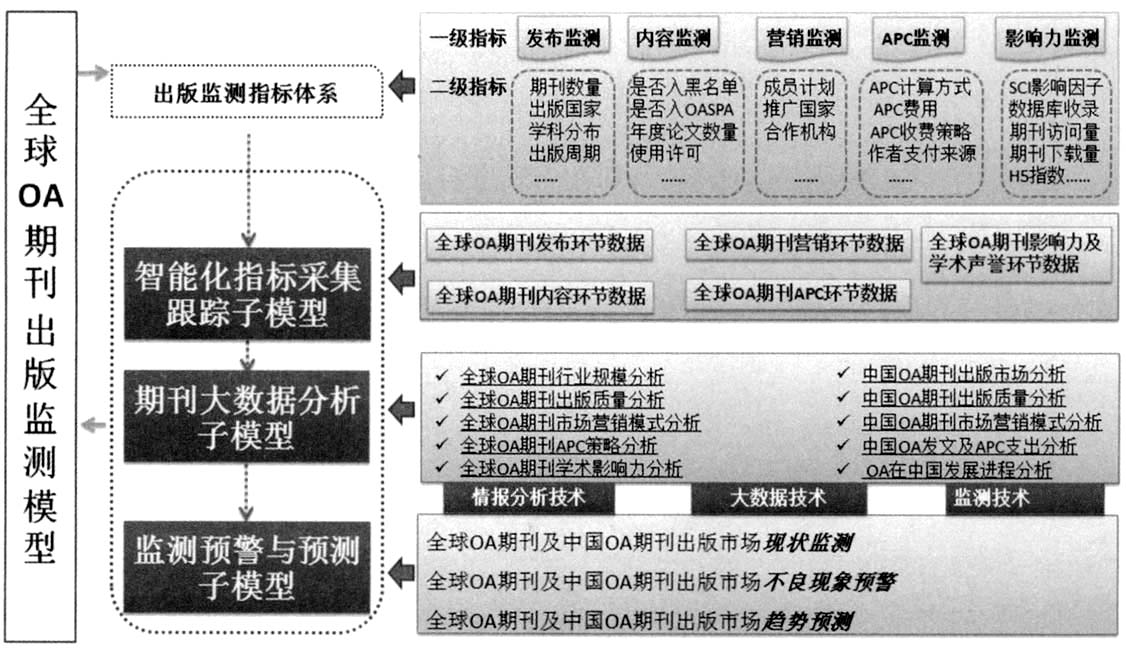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