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宁波 315000
摘要:玛莎·诺曼是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作品聚焦父权社会中边缘女性压抑、无力的生存空间和心理感受。代表作《晚安,母亲》在传统家庭结构中探索母亲客体化、他者化身份,通过重构新型母女关系模式言说母亲的欲望,构建母亲的主体地位和独立身份。理解和重构母亲身份成为诺曼探索现代女性身份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晚安,母亲》;母亲身份;母女关系
引言
玛莎·诺曼是美国剧坛著名作家,代表作《晚安,母亲》1983年荣获普利策戏剧奖,并获托尼奖四项提名和专门颁发给杰出女性剧作家的苏珊·史密斯·布兰科波恩奖,该剧于2004年成为百老汇的经典保留剧目。当代戏剧评论家布朗声称诺曼“是当今美国从事严肃女性主义戏剧创作最为成功的作家”,并认为她的剧作“从明确反映女性心理学和女性主义道德伦理的视角抓住了深奥的主题”。(1991:60-77 )诺曼的系列作品聚焦父权社会中边缘女性压抑、无力的生存空间和心理感受,从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性别分工审视现代美国女性的身份构建,而母亲身份是诺曼作品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易卜生、奥尼尔、品特等西方男性剧作家表现母亲身份相比,诺曼笔下的母亲是另一种观照。(刘岩,2004: 288)尽管她们依然生活在传统父权体制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比较成功地颠覆了传统母性角色,部分地建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和独立身份。本文运用女性主义相关理论分析诺曼在《晚安,母亲》一剧中对现代母亲身份的探索。
一、女性主义母亲身份理论
母亲在人类文明中一直是个文化象征,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母亲的身份特征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首先指出女性对于男性来说是“他者”,必须“根据本者(男性)选择的行为方式来定义自己”。(1972:279)本杰明沿用“他者”概念,“正是这一客体化,以及力争维持绝对差异和占据控制地位的思想,使主体(男性)的行为产生偏差。”(1988:77)像其他女性一样,母亲的价值体现在被交换的过程中,她的身份由男性参照她同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而定。在父权社会,母亲被认为是所有女性的最终命运。伊里佳蕾、克里斯提娃从结构主义出发,相继指出,女性被排除在知识和权力之外,女性的价值主要依赖于她的生殖能力,母亲身份被认为是父权制度下“女性唯一有价值的命运”。(Irigaray,1994:99)无论女性承担怎样的家庭角色,她都几乎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作用是保证繁殖,维系种族的繁衍。(Kristeva,1986:140)
与波伏娃一样,美国当代心理分析学家乔多罗也认为性属是蕴含文化和心理因素,每个人的性属概念都融合了个人意义和文化意义。乔多罗最核心的观点是:“女性承担母职是性别劳动分工的中枢。这一角色对于女性的生活、对于有关女性的观念、对于男性角色不平等的择生、对于劳动力的某种形式的再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身为母亲的女性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因素。”(1978:11)
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也改变了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女性母亲身份的看法,但是母亲身份依然是很多女性角色的最终命运。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努力在理论上重新构建母亲身份。波伏娃坚持认为,沦为“他者”的女性如果诚实面对自我和处境,勇敢地做出抉择,女性仍然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存在,实现自我超越。(1998:25)美国诗人里奇虽然认为在父权体制下,母职是一种制度和规定,但是她也同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母亲身份对女性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女性通过生儿育女,感知生活,实现自我的价值。(1995: 13)在探讨母职的社会、文化、心理意义不考虑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是不可能的。女性身体上的本质主义的确存在,不同的生理构造是女性承担母亲角色的基本前提,是自然的产物。但是性属的产别“逐渐获得的”是后天形成,是文化的产物。(Chodoraw,1978:108)既然生理差别是内在,那么通过消除性别差异实现性别平等是不可理喻的,因此从心理、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考察母亲的身份就格外重要。
二.塞尔玛与杰茜他者化的母亲身份
在以父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女性的生理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生活主要局限在家庭领域,随着年龄增长,母亲身份成为绝大部分女性的最终命运。这样的命运也发生在《晚安,母亲》中的两位女性身上。母亲塞尔玛是一位传统家庭主妇,但婚姻不幸。丈夫拒绝与塞尔玛讲话,甚至将这种冷漠带到临死之前的病榻上。在丈夫的世界里,塞尔玛不过是欲望的对象,丈夫用自己的喜好、传统观念定义塞尔玛,当塞尔玛不能满足丈夫的惊奇感后,丈夫便用沉默加以对抗,从而直接剥夺塞尔玛表达的权利。剧中,塞尔玛说话很快,甚至滔滔不绝,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自说自话,因为说话(speak)和表达(talk)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女性总是在说话,不停地说,唠唠叨叨,口腔充溢这声音,从嘴里发出的声音。但她们实际上并没有表达,因为她们没有什么可表达的。”(Cixous,1981:49)塞尔玛虽然拥有自己名字,但主要重复着女性“从夫从子”的传统命运,处理生活琐事。根据西克苏的区别,说话只是一种行为,并不能表达一个人的主体思想。它是被动的、直觉的,不需要主体。相比之下,表达却是述说思想的能力。它是主动的、独立的、是需要主体的。事实上,住在“乡间路旁的一幢房子里”的塞尔玛除了生活琐事也确实没有什么好表达的。(P.91)
寄居在母亲房子里的杰茜的处境并不比母亲好。杰茜从小身患重疾,四十多年来饱受癫痫病的折磨,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而被客体化、边缘化的母亲也无法给杰茜在精神上树立正面积极的形象, “母亲自身独立身份的丧失导致女儿生存困境更加困难。”(贺安芳,2009: 35)无法言说自己欲望的母亲把欲望和希望寄托在小孩身上,因为杰茜的疾病,塞尔玛对杰茜的保护也格外强烈。她不仅用谎言和虚构掩盖女儿疾病的真相,并一手安排女儿的婚姻。尽管杰茜爱自己的丈夫塞西尔,但塞西尔却不满杰茜抽烟,也不高兴她随他离开那个地方,进而出轨,然后把杰茜当“垃圾”一样抛掉。杰茜没有工作、收入、账户和朋友,每日工作就是处理日常家务。作为母亲和妻子,杰茜与塞尔玛的处境非常相似,家庭是她们活动的主要地方,在那里她们主要扮演欲望的对象。
三.重构母亲身份
母亲塞尔玛面对自己他者化的境遇并非无察觉,潜意识里对自己被丈夫当作“替罪羊”的角色心存不满。塞尔玛没有刻意改变自己逢迎丈夫的期待,而且“从来也没喜欢过做饭”。尽管如此,塞尔玛大部分时间还是选择了逆来顺受,被动等待。与母亲得过且过不同,杰茜选择行动。
杰茜是一位与塞尔玛不一样的母亲。杰茜明白女性要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母亲,她首先得是一个独立的人。抽烟是阳性的象征,通常女性是不能参与的。但杰茜却喜欢抽烟,当丈夫让她在抽烟和他之间做选择,杰茜坚持表达自己的欲望,选择抽烟。抽烟既是杰茜对自己他者身份的抗议,也是对男性权威的挑战。杰茜的男性化衣着同样表现她的反抗。杰茜身着长裤,黑色长毛绒衫,口袋挺深,里头装着些纸片,她耳后可能还插着一支铅笔,或在毛绒衫的一个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P.91)无论是抽烟还是穿着都体现杰茜对平等的渴望,而铅笔、钢笔更是暗示杰茜渴望拥有话语权和独立思想。面对一直关心自己的哥哥,杰茜也非常不满。无论是哥哥送的拖鞋还是对她的昵称,在杰茜看来都透着哥哥居高临下的自我优越感,令她反感。与母亲浑浑噩噩的生活相比,杰茜目标更明确,意志更坚定。
在母亲身份的认知上,杰茜与塞尔玛也很不同。传统的母亲以儿子为中心,塞尔玛也不例外。丈夫去世后,塞尔玛没了主见,家里大小事都让儿子做主。另外,从传统的母亲角色看,杰茜和塞尔玛都比较失败。塞尔玛女儿要自杀,杰茜儿子吸毒成瘾,沦为小偷,但两个母亲面对孩子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当塞尔玛听到杰茜要自杀,她很自责,觉得自己失责毁了杰茜的一生。但杰茜却不把儿子的犯罪与自己绑架在一起。杰茜将儿子视为独立个体,儿子犯罪是他自作自受,他得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杰茜比塞尔玛更有身份的疆界意识,明白母亲与孩子之间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
基于这样的认知,重构她与母亲的关系是杰茜重获自主性的重要一环。杰茜深知,只有冲破与母亲原始的共生关系,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母亲塞尔玛从小就对杰茜严加控制,从隐瞒病情到一手包办她的婚姻,再到杰茜婚姻失败收留她甚至规划女儿的生活,无一不体现出母亲对杰茜自我边界的侵犯。塞尔玛对杰茜的“吞噬”进一步加深了杰茜无我感。面对杰茜的自杀,母亲苦苦相劝,一再强调杰茜是她的孩子,而杰茜却不停反驳她不是母亲的“私有财产”,而是一个独立的成人。“如果自杀是我永远摆脱您的唯一办法那又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又怎么样?我照样能自杀。”(P.110)塞尔玛终于明白,孩子虽来源于母亲,与母亲血脉相连,但孩子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于母亲,孩子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思想。
四.结语
母亲角色一直是西方戏剧创作传统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从古希腊悲剧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剧。长期以来,母亲角色常常以家庭成员的欲望对象而存在,但这一形象在诺曼的作品中遭到挑战。女儿杰茜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重构母女关系、重塑自我的过程给母亲塞尔玛塑造了另一种母亲的形象,不仅将母亲从自责、悔恨中解放出来,也给予母亲重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实现精神上的蜕变。
注释:玛莎·诺曼. 《晚安,母亲》黄宗江 张全全译 《中央戏剧学院剧本选》第51册。(以上引文皆来自此译文)
参考文献:
[1]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M].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5.
[2] Brown, Janet. “Getting Out/night Mother.”In Taking Center Stage: Feminism in Contemporary U. S. Drama[M]. Metuchen, NJ: Scarecrow, 1991.
[3] Hélène Cixous.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trans., Annette Kuhn[J],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7.1, 1981.
[4] Jessica Benjamin, The Bond of Lo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M].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5] Julia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trans., Seán Hand,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Luce Irigaray, Thinking the Difference, trans., Karin Montin [M]. London: The Athlone, 1994.
[7] Nancy Chodorow,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M].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8]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9] 贺安芳. 试论《晚安,母亲》中的自杀主题[J]. 学术交流. 2009(08).
[10] 贺安芳. 母女关系视角玛莎·诺曼的作品研究[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3(03).
[11] 刘岩. 《西方现代戏剧中的母亲身份研究》[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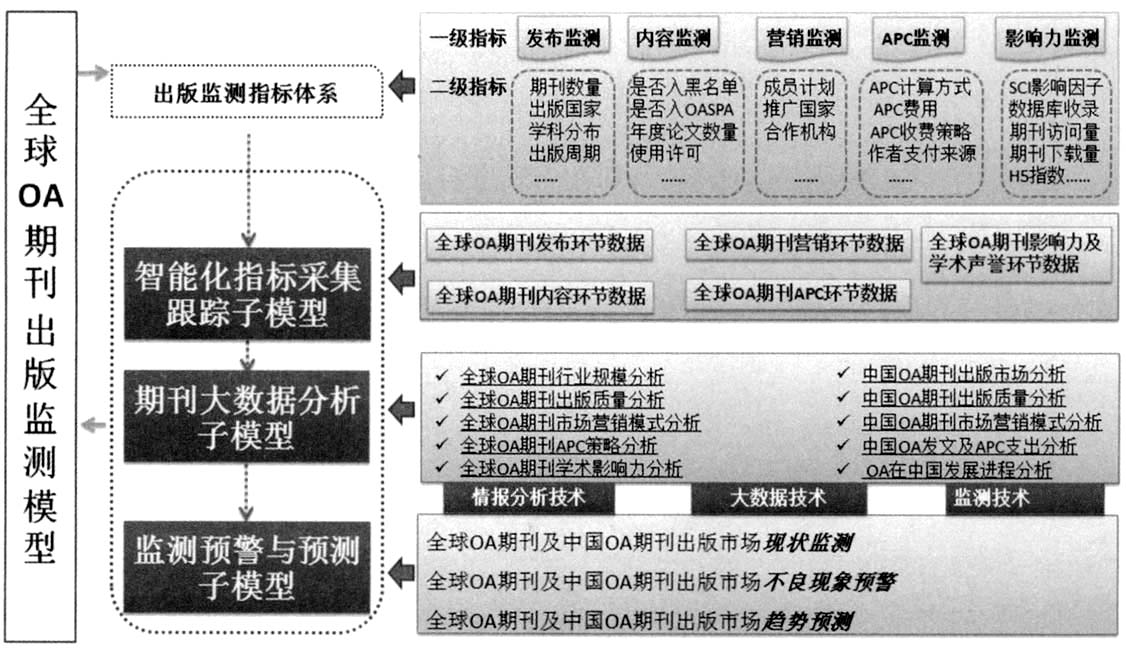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