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的巨大破坏性给了历代统治者深刻的教训。汉代太平教发动的黄巾军起义、元末白莲教起事、清朝嘉庆年间川陕楚五省白莲教起义及天理教暴动等以邪教为组织形式发动的颠覆政权的活动,无不让统治者伤透了脑筋,以致历代统治者时时以黄巾、白莲之祸为鉴戒,从行政、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采取严厉措施,对邪教犯罪进行全方位的预防和惩治,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重演。本文拟从法律角度探讨我国古代对邪教犯罪的预防惩治方法及对现实反邪教工作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古代惩治邪教犯罪的主要罪刑规定
1、谋反大逆罪。我国古代邪教组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入世”色彩,往往进行以危害现存社会秩序为对象的谋反、谋大逆、谋叛等性质严重的犯罪。因此,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谋反大逆”罪始终是惩治邪教进行政治性犯罪的重要法律规定。比如,明代《大明律》用最为严厉的“谋反大逆”律对邪教犯罪加以惩治,“凡谋反及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在清代,由于许多邪教成为“反清复明”的工具,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因此,清朝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把“兴立邪教”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比照“谋反大逆”罪进行惩罚。《大清律例》明文规定:“其有人本愚妄,书词狂悖,或希图诓骗财物,兴立邪教名目,……比照反、逆定罪之案”。这里,为满足个人私欲而创建邪教组织,及借助邪教从事反政府活动,这两类行为均被归为“谋反大逆”罪而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
2、造妖书妖言罪。“妖书妖言”是指借鬼神之口制造和散布对现存秩序不满以煽动民众的异端邪说、思想、言论及文字宣传。邪教组织宣扬的谶纬之学、“末世”、“劫变”等邪说异端思想、教义,极具有诱惑性和煽动性,能够将平时各自为阵的分散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种严密的组织,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引发叛乱活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此种邪教犯罪行为的惩罚,其中“造妖书妖言”罪是惩治此类邪教犯罪的重要法律条款。“造妖书妖言”罪始设于秦代,以后几经存废。唐宋时期,此罪名被进一步细化,分为制造妖书妖言、传用妖书妖言和私存妖书三种类型。如《唐律疏议》规定,“诸造袄书及祆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明清继承了唐宋的法律制度,《大明律》把“造妖书妖言”罪放入其中,规定:“凡造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大清律例》也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由此可见,“妖书妖言”罪惩禁的主要是邪教组织利用怪诞邪说、异端思想蛊惑民众的行为,是防范邪教组织“惑众”、制造社会混乱的重要法律依据。
3、禁止师巫邪术罪。“禁止师巫邪术”罪首创于明代。朱元璋鉴于元末白莲教起义颠覆政权的历史教训,专门在《大明律》中增加了“禁止师巫邪术”法律条款,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百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从以上律文来看,首次以法律条款的方式,明确把有组织的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当作邪教列为政府惩治的对象,重点打击这些邪教组织以祭祀为手段而追求不同于官方的神灵崇拜,夜聚晓散的活动方式,以及煽惑、聚集民众的师巫邪术行为。清承明制,在《大清律例》中专门列出“师巫邪术”条,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百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明清中央政府专门制定法律条款,对邪教组织夜聚晓散、煽惑聚集民众等活动进行治罪,使得地方官员在执法过程中更容易辨别邪教犯罪行为,同时更方便定罪量刑,对邪教的惩治也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我国古代惩治邪教犯罪立法的主要特点
1、法律规范日益明晰、具体。首先,对邪教组织的称谓和内涵日益固定、明晰。在清代以前,官方对邪教组织多冠以其它称谓,如宋朝称“吃菜事魔”,元代称“左道乱政之术”,明代称“妖术”、“左道乱政之术”,直到清代,“邪教”这一术语才正式刊载在官方文书中,成为内涵相对固定的政治概念。《大清律例》将白阳教、白莲教、八卦教等教派统称为邪教,明文规定“兴立邪教”和传习白阳、白莲等邪教的治罪条款,使邪教在法律上有了专门所指和固定内涵。其次,法律将邪教犯罪的形式和行为特征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比如,明代按照传习邪教行为的严重程度、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罪名和刑罚,使法律规范更为缜密和具体;清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传习邪教行为细分为习练荒诞不经咒语、无传习咒语传徒、收藏经卷、讽念佛经等四种类型,并分别治罪。这样,司法官员在处理邪教案件时,可以依据邪教组织和成员的具体犯罪事实,采取相应的定罪处罚措施,从而对邪教犯罪起到了很好的规控作用。
2、实施从严从重打击邪教犯罪的政策。由于认识到邪教组织对现存政权的严重威胁,历代统治者在对待邪教犯罪问题上均采取铁腕打击政策。如明代永乐年间,山东白莲教教首唐赛儿发动叛乱,遭到官军镇压后逃匿,“当是时索(唐)赛儿急,尽逮山东、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为了一个唐赛儿,受诛连人数竟达几万人之多,明代惩治邪教严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惩治邪教的刑罚也非常严厉,对于教首、教内骨干分子和一些情节较为严重者,除判处死刑(包括凌迟刑、斩刑、绞刑)和流刑等法定五刑外,还单独附加挖墓鞭尸、挫骨扬灰、刺字、枷号等刑罚。此外,还有撤除邪教犯罪者某种身份或降低其政治社会地位的身份刑,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1)邪教犯罪被判处流刑者,发往黑龙江、新疆给“披甲人”(军人)或回民为奴。(2)旗人传习邪教,拆销旗籍,不再享受旗人特权。(3)受徒、流以上刑罚的邪教罪犯,其后代三代不许参加科举考试。
3、实施自首从宽与分化政策。由于邪教组织人数众多,官府难以一一进行有效的管制和惩罚,加上邪教教徒大多数都是被诱骗入教的,对于邪教组织并不是真正了解,其立场也不坚定,如果一味严禁、不许自首,很可能会激发逆反心理,导致更加不利的后果。因此,历代统治者对邪教犯罪者多采取鼓励自首的政策,对一般胁从者也予以减罪或免罪,借此分化瓦解邪教组织。比如,《大明律》规定:“今后官、吏、军、民、僧、道人等,但有收藏妖书、勘合等项,榜文到日,限一月以里,尽行烧毁,与免本罪”,对于一般邪教信徒,给予了其限期烧毁“妖书勘合”、“与免本罪”的机会。应该说,允许邪教犯罪者自首,是明代防治邪教的有效措施之一。清代在处理邪教犯罪时,实行区分首、从的原则,对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骨干分子坚决严惩,凡触犯“禁止师巫邪术”者,“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清律例·禁止师巫邪术条》),而对受邪教组织蒙骗的普通民众则不予追究或从轻治罪。
三、我国古代惩治邪教犯罪的启示和借鉴
1、严禁邪教非法活动,将其禁绝于萌芽状态。如北宋宣和元年,浙江绍兴有奸猾者“结集社会,或名白衣礼佛会,及假天兵,号迎神会,千百成群,男女杂处,传习妖教”,宋徽宗“诏令浙东帅宪司温台州守臣疾速措置,收捉为首鼓众之人,依条断遣”(《宋史·刑法志》)。清代顺治帝敕令内外官员对邪教严加禁止,“如遇各色教门,即行拿问,依律重处,以为杜渐防微之计”(《清通鉴》)。
2、广泛发动舆论宣传,强化法制教育,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和能力。如宋代针对“吃菜事魔”、“聚众烧香”等事件,“令刑部遍下诸路州军,多出文榜于州县城郭乡村要会处分明晓谕”(《宋史·刑法志》)。对于“传习妖教”者,明代“诏令州县以断罪告赏全条于会处晓示,监司每季举行”(《大明律》),清代“令守令检举见行条法镂板,于乡村道店关津渡口晓谕,许诸色人告捉,依条施行”(《大清律例》)。可见,历代统治者在惩治邪教过程中,非常重视舆论教育的作用,要求各级地方官员以文榜、告示等方式对邪教的谬误加以反驳,并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使人们自觉接受遵从社会主流规范,从而在遇到邪教蛊惑时能够增强免疫力,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
3、实行奖励告发政策,充分调动群众举报邪教犯罪的积极性。如宋代规定:“夜聚晓散传习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州县首令能悉心措置,许本路监司审核以闻,除推赏外,量加奖擢”。清代规定:对于能捕获邪教罪犯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仍将犯人财产全给充赏”。可见,历代统治者对于能够悉心处置邪教的各级官员,以及积极举报邪教犯罪的百姓,都不吝给予物质奖赏和提拔重用,借此强化官民惩治、告发邪教犯罪的义务和责任。
4、打击邪教犯罪要坚持综合治理原则。梳理我国古代邪教蔓延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政治的明暗、经济的兴衰、救济制度的效能、社会的转型等,都是诱发邪教蔓延的重要因素。因而,要更加有效地防控和打击邪教犯罪,紧靠单一的举措和做法,哪怕是最为严酷的法律也很难奏效。比如,清代虽然制定了我国古代最为完善的反邪教法律法规和最严苛的刑罚,但依然接连爆发了川陕楚五省白莲教起义、天理教暴动等恶性邪教事件。可见,在不断完善法律规范,从严从重打击邪教犯罪的同时,还需要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保障等多个渠道、全方位着手,综合施策,方能最大限度地铲除邪教滋生的土壤,从而有效地预防邪教的蔓延坐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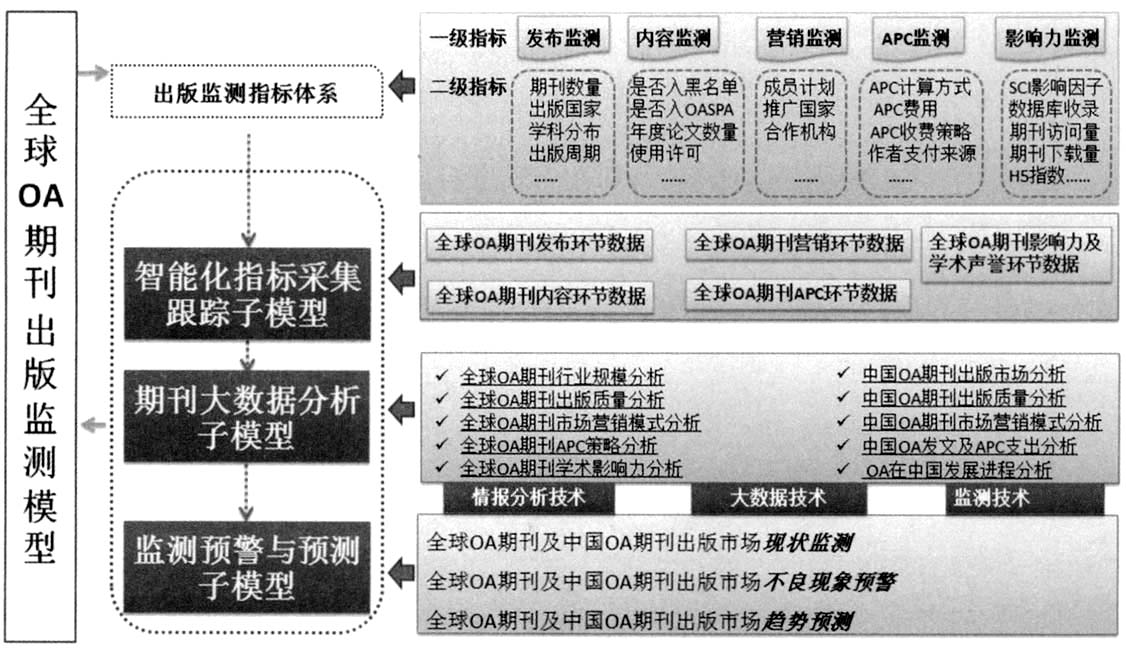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