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乔叶以散文写作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很快便凭借大量散文精品成为著名的“青春美文作家”。而以在《十月》1998年第1期上发表短篇小说《一个下午的延伸》为标志,奠定其此后在一个阶段内小说创作的艺术基调为标志,乔叶开始了从散文家到小说家的转型。二十多年来,小说家乔叶在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领域均有不俗的创作成绩,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70后”小说家代表人物之一。从“非虚构小说”《拆楼记》到反思历史及人性、“取向偏重”的《认罪书》,再到包裹着穿越的故事外壳、有些“偏轻”的《藏珠记》,直至刚刚出版的具有强烈女性意识、“有回归意味”的小说集《她》,乔叶的小说创作不断地在题材主题、叙事范式等方面进行开拓,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5月28日,乔叶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就与其文学创作相关的诸多话题展开深入对话。
一、我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践行者
江磊:乔叶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我想从您近年来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开始谈起。您的《象鼻》《随机而动》《进去》等近作试图发掘当今都市人坚硬外壳下柔软、空虚、彷徨的内心世界,捕捉其复杂、幽微的情感体验和人性呢喃,仍然延续着您一贯的人性书写。但与您的早期作品较多通过情感婚恋危机等“非常态”的人生处境探寻人物的心灵隐秘不同,这几篇小说写的是都市里的芸芸众生几无波澜的日常生活,意欲在人们已经见惯不惊、习焉不察的生活之流中揭示国人普遍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我认为这些作品非常贴近当今中国现实,时代气息鲜明,具有很强的“当下性”,也拓展了当代都市小说的叙事模式,构成了您在小说创作上新的爆发力。您怎么看自己的这些近作?
乔叶:学界喜欢说创作转变、创作转向、创作转型之类的话,也常常用来描述我从写散文到写小说再到“非虚构”写作的创作历程。这些“转”都是一种习惯性的常规叙述,我个人不太喜欢,对此也是存疑的:哪有那么转来转去的呢?就整体的内在性而言,我可能只有一条大的创作路径,也许有时候会岔开,走到这边或者走向那边,但我在这条路上不会有突然调头往东、突然调头往西的变化。我个人认为这条创作路径还是比较有一致性的,那就是往前走。
我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践行者,这也是我们河南文学的大传统。以前我不太认同自己是一个河南作家,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总想在写作时尽量抹去自己的地域痕迹。当然,当时我还很年轻,才20岁出头,来到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时也还不到30岁。那时候,我就是不太喜欢“河南作家”这个地域标签,一心想要当一个存在性更广泛的作家。但是后来这些年,写着写着,我发现自己骨子里就是个河南作家。我的根在河南,创作的根基在河南,文化的血脉在河南,那我当然也就是河南作家了,这是命中注定的,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挺认命的,心甘情愿。总的来说,我就是在现实主义大道上一直前行的一个人,没有太多的本质转变,只不过有时候对于某个方向兴趣更浓一点、延伸得更细致一些、探索得更深广一些。其实也都还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有时候往“大拇指”方向走一点,有时候往“中指”方向走一点。
你说的“非常态”特征在2004年左右我刚开始写小说时比较明显。我是写散文出身的,后来写小说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一定要特别像个小说家。散文的叙事是很缓慢的、偏日常的,所以当时我对小说的理解主要集中于故事化、悬念化抑或是传奇性等诸多方面,在这些方面下的功夫多一点。但写了几年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散文创作经验还是不能弃之不用,所以另外一些小说,如《最后的爆米花》《取暖》《最慢的是活着》等,都是明显的散文化小说。我其实没有特意去拓展你所说的当代都市小说叙事模式,不像评论界所认为的具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和路径。客观上可能会产生你说的那样的效果,比如表现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精神困惑等。所谓的都市小说叙事,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作家、小说家试图表达的内容,是一个“大篮子”,谁都可以往里面装东西。它也可以容纳任何人,凡是具有现代性视野的小说家都可以装进去。
我总结自己的小说创作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是让传奇的故事具有日常性;二是让日常性的生活具有一点传奇性。这两个方向都可以走,我认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就是在这两个方向上展开的。
江磊:优秀的小说家在某些方面的思考真的是相通的,您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张爱玲在其小说集《传奇》的扉页上写下的文字:“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我深感有异曲同工之妙。
乔叶:是的。比方说吧,像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写出身于上海弄堂的中学生王琦瑶非常偶然地被选为“上海小姐”第三名,成为“三小姐”,由此展开其传奇的人生经历。故事本身很有传奇性,但小说倾尽笔力描写其日常生活:写的更多的是她“选秀”之后怎样恋爱、怎么被人抛弃、如何一个人生活一直到老,等等。这篇小说在大的题材框架上是传奇的,但描写的却是极具日常性的生活细节。那么另一方面,我的许多小说又是试图让日常性的生活具有一点传奇性,比如《送别》是写“我”的大学同学突然跳楼自杀了,“我们”一帮同学去奔丧,为其送别,然后大家在与他的家人交谈、回忆他的往事时捋出了这个中年男人的点点滴滴。所谓送别,其实也是与“我们”自身的一部分送别。小说所涉及的都是些日常性的生活,但因为这个男人自杀了,所以好像又有一点点传奇性。
江磊:您的小说总体上包括城市题材和农村题材两大类,您觉得哪一类更接近您的内心?
乔叶:其实我本身对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所质疑的,选择面对面访谈的原因也在于此。什么是农村题材?什么是城市题材?如果一个人在农村生活了很久,来城市打工,你说写这样的人物是属于农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如何去辨别这个人身上带有的这种交杂的身份呢?他带有那么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农村生活习性,他来到了城市,其实依然是个农村人。可他到底属于农村,还是属于城市呢?我不太喜欢在小说人物身上打上各种标签,然后确立自己的写作,我觉得还是要以人为本。
倘若一定要辨析乡村经验或者农村经验,我觉得我们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大的乡村,尤其是河南在这方面最为典型。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的乡土经验、乡土伦理,虽然到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但它依然存在,“乡土中国”的说法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比如你应该也有在乡村的亲人,我们都有乡村背景,清明节依然要回乡上坟,过年过节也要回老家。我觉得乡村在以前具有一个明确的骨骼,也许现在这个骨骼破碎了,可骨架依然在,甚至还是我们的支撑。人们普遍认为它已经没有力量了,但它在一定的时候依然会显示出自身的力量来,而且非常坚实。我觉得这种影响、这种力量是深入骨髓的。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基础有着很大的区别,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的乡村伦理、宗族观念、道德体系,这些都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所以即使当下的现代化进程如此迅猛,大家都说乡村崩塌了,但是我觉得崩塌的只是表面,它内在的精神性的东西尽管也被破坏了,但哪怕发生了“粉碎性骨折”,它依然是强有力的硬性存在。
江磊:沿着刚才的话题说下去。您的创作与河南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如果具体到河南省省会郑州这座城市呢?您长期生活在郑州,而且您的大多数小说都是在郑州工作期间创作完成的,作品中的很多故事场景也有这座城市的影子。您觉得自己的小说创作与郑州的城市性格、城市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您认为郑州有着怎样的城市性格与城市文化?
乔叶:我觉得还是用地域性格来回答这个问题更加准确,因为现在谈论城市文化、城市性格还不够成熟。郑州在河南,李佩甫老师在《羊的门》里说过,我们所在的中原大地是块“绵羊地”。这块中原大地经受过非常深重的苦难,有着充满灾难和战乱的历史,长期被战争杀伐,在历朝历代每隔一段时间可能就要被狠狠地蹂躏。正所谓八面来风,四战之地,谁也饶不了我们。所以这是一块很温和,但又充满力量的土地。而这个力量也应该就是李佩甫老师说的,人活一口气,这口气你看不见,但是它在一定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刚硬。
因为经受了太多的苦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代一代地繁衍下来,可能会显得很中庸、很温和,就像中原饮食文化。我写《藏珠记》的时候采访了很多大厨、饮食专家,他们告诉我,中国的饮食总体上是“南甜、北咸、东酸、西辣”,而中原就是五味调和、知味适中,这就是中原饮食文化的特色。我想,这真的就像我们这儿的人,像我们这儿的地域性格:我们不是没脾气,或者说看着像是没脾气,但有时候会发大脾气。我觉得我的作品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特点。这一方面我倒是没有认真捋过,可能作品里会有这种看起来显得温和、冷静,但是也会突然爆发的人物。如果要找我的小说和地域性格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方面是可以找到线索的。
江磊:关于郑州的文化性格,我之前看过您的《双城记:郑州与北京》这篇文章,我注意到您在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话说回来,再大的城,与过日子休戚相关的,也都是些‘小’,不然怎么会有‘小日子’的叫法?”您对城市的观察,注重的还是其生活化的一面,关注的还是城市中的日常生活。是这样吗?
乔叶:观察城市还是应该落实到人:公交车上的人、地铁上的人、街道上的人,他们才是构成城市灵魂的基石。
二、我相信的是更加普遍的、概率更高的诚实
江磊: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散文写作的三个关键词是诚实、自我、虚构。在我看来,这三个词不仅仅是散文写作的关键词,应该也是包括小说创作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的关键词。您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乔叶:对,是这样的。我现在经常出去跟其他的写作者交流,给青年作家讲课,有时候也会具体分析某一部小说,但是在跟某些作家尤其是基层作者交流的时候,我发现技术层面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其实还谈不着,他们存在的主要是创作意识、创作观念方面的问题,而他们自己可能还意识不到。我认为,一个写作者的创作意识中是否具有自省能力决定着其“创作大脑”的质量,也决定着作品的质量。如果没有这种自省能力,写出来的作品往往会四肢非常发达,头脑却不健全:细节再丰富、语言再华丽,都不管用,因为这些都是次要的,大脑才最关键。
我自己人到中年,也依然在不断地成长,这是写作带给我的财富和馈赠,是一种巨大的精神福利,所以我非常愿意把自己在成长中的收获同大家分享。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创作意识、创作观念问题,这里就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诚实。诚实就是说真话,但好多写作者都在习惯性地撒谎,在写作时会端起架子来,自我装饰,自我欺骗,甚至于自己都没有丝毫察觉。有些话,写作者本身就通不过、就不相信,但是他(或她)仍然把这些话写了出来。那些明知是谎话还要说的人,在愚弄别人的同时,肯定愚弄了自己;那些不知道自己说的是谎话的人,在愚弄别人之前,首先愚弄了自己。对于这些,他们也许还不知道。写作是最不藏人的,读者群中藏龙卧虎,他们非常敏锐。
卡夫卡曾说:“说真话是最难的,因为它无可替代。”这句话深得我心。散文、诗歌要诚实,写小说当然也要诚实,虽然小说有着虚构的外壳,但却讲着最真的话。因此,如果有人写这些:一个已婚女人受到魅力男人诱惑,她的内心稳若磐石;一个男人身为绝版好丈夫忠贞不贰,对妻子之外的任何女人都没有动过心……作为一个人,他(或她)从不曾在滚滚红尘的欲望中挣扎过,动摇过,煎熬过——我不相信,我觉得这种情况只存在于质量不高的偶像剧中。当然,生活中真的可能有特别完美的人,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那样写,但那样写的作者无异于把自己立在了刀尖上,是否能够平稳地走完写作过程是很危险的,往往都会掉下来,甚至刚上去就掉下来。但是这个写作者可能自己都没有察觉,甚至会觉得自己走得特好。那没办法,我也不能说这样的写作者不诚实,但这样的诚实是非常有限的、非常狭窄的。我相信的是更加普遍的、概率更高的诚实。
江磊:其实您刚才说的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我下面想谈的这个问题。您的小说处女作是发表在《十月》1998年第1期上的短篇作品《一个下午的延伸》,这篇作品实际上奠定了您此后在一个阶段内小说创作的艺术基调。小说讲述一个女下属与她的已婚男上司之间并未真正发生的婚外恋情,重点表现了二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内心波澜。很明显,婚外恋、精神出轨等情感婚恋危机实际上是您洞察人心、洞悉人性的一个窗口,您的独特之处在于把人物从社会层面的伦理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宽容。您如何看待笔下的男男女女们在情感、欲望面前的矛盾与困惑?这是否代表了您对现实及人性的某种认知和理解?
乔叶:对啊。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为什么那么动人?就是因为曹雪芹在描写他们的时候,不仅写了“纯洁”,还表现了“丰富”。好多写作者写“纯洁”的时候会失去“丰富”,但其实,“纯洁”并不妨碍“丰富”“复杂”“深沉”。我们都知道,贾宝玉看到林妹妹就忘了宝姐姐,看到宝姐姐就忘了林妹妹,貌似有些小花心,可这就是贾宝玉可爱却又矛盾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并不会遮蔽人物的光芒,反而构成了他的光芒。就像油画,油画中的白是需要由其他色彩衬托出来的一种坚实的、可信任的白,而不是说什么其他色彩都没有,只剩下了白。伟大的作家是要用丰满、繁复的人性来告诉我们有一种可以信服的美好。许多写作者自认为写得很纯洁,其实是写的简单,甚至简陋。这可以延伸出很多话题。我觉得,如果是10多岁的孩子,你可以简单、单纯,但当你40多岁时,如果还认为自己很简单、单纯,那其实就不是简单了,而是简陋,这和你的经历、阅历、人生经验等都不相配。如果是以这个样子写小说,还认为自己很单纯、纯洁、美好,那就是自欺欺人,就是不诚实。其实,也是没有能力诚实。
我曾经在《散文选刊》工作过几年,那时经常看到歌颂父母的“好爹好娘稿”。我们都有父母,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父母很好,这无可厚非,可以理解。在生活中,我很相信也很尊重这种真挚的情感,但是把它放在文学文本里去表达的时候,简单的歌颂和表扬可能就成了问题。比如歌颂母亲的时候,有的写作者很清楚自己在写作,文章可能要发表,就觉得一定要表扬母亲,要树立形象,任何不利于这些的内容都不能在文章中表现,所以最终在文章里呈现的,其实是经过自己内心过滤了许多遍的母亲的光辉形象。这真实吗?我觉得充其量只是某个层面上的、某种狭窄角度的真实,当然不是优秀的文本。端起架子来写作是很可怕的,有的写作者在写作时明明是自欺欺人,却对此毫不自知。
创作优秀的、诚实的文本,需要把读者当成自家人。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有时候会做错事、会有各种矛盾、会有牢骚、会有埋怨、甚至会痛哭流涕,但只有拥有了最真实的泪、最复杂的痛和最清晰的认知,真正把读者当成了自家人,写出来的文字才会更被认同。这涉及到复杂的写作伦理:写作的基本伦理就是至少该在写作中探究真实的生命感受,表达真实的生命经验。同样是歌颂母亲,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特别感人,许多人看了都会流泪,这就是优秀的、诚实的作品。许多写作者很容易陷入一种表扬和自我表扬,不太敢自我批判。进行真正的自我批判其实是很残酷的事情,神经娇弱的人挺多,他们读那些真正具有批判性的作品可能也受不了。
江磊:近年来,创作界、理论界对“现实主义”等相关问题有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比如说去年,《长篇小说选刊》开展了“新时代与现实主义”大讨论,您在自己的专稿《柳青的现实主义》中写道:“现实不是描摹的纪实,不是愚蠢的顸实,而是最深的真实,和最高的诚实。”能不能请您进一步谈谈自己的观点?
乔叶:文学是关于现实的表达,而非现实本身,同时,现实也不是写实。我们现在谈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一种主题性的论述,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现实感”。现实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创作观念,如果具备这种很好的创作观念,即使写唐朝的事情,也会有现实感,那么这未尝不是现实主义,我认为可以更宽泛地去理解它。而“现实感”则涉及到一系列因素,比如作家的学养积累、作家如何去观照历史及当下的生活、作家的认知能力,等等。我特别不同意“照相机似的现实主义”,那是不够高级的现实主义,对现实的理解和表达还是要有纵深度。
江磊:您曾表示:“我不从性别来考虑人物,男性和女性,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有性嘛。我虽然是女作家,但我也写男性人物,他们也不一定就比我的女性人物更不可信。”但是在不久前的一次关于中国作家性别观的问卷调查中,您似乎推翻了自己多年以来的观点。在调查问卷的回复中,您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您的许多短篇小说都运用了女性叙事视角,但很多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没有姓名,叙述者皆为“她”。我想,这大概也是您的短篇小说集《她》的书名的一个由来吧?
乔叶:张莉老师的这次问卷调查就发生在不久之前。回想起来,在某些问题上,我似乎总是在不断地推翻自己。比方说我刚刚谈到的河南作家的身份问题,我以前老觉得自己不是河南作家,或者说比较拒绝自己的河南作家身份,但后来我又很认同这个身份。其实性别意识和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之前我自认为没有性别立场,但后来我发现自己还是有性别立场的。生而为女人,作为女性活了这么多年,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写作,也必定在这个命里面。没办法,我还是要认同,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甚至开始觉得号称“不从性别来考虑人物”也是自欺欺人。
江磊:世界是中性的,但不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其小说中的世界其实都是带有主观性的个人化的世界。在我看来,您是从自己独特的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出发去写作的,所以您刚刚虽然说自己是有性别立场的,您的小说也确实具有明显的女性特质和强烈的女性意识,但您在表达时较少偏颇。比如我注意到,您的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大都不是所谓女权主义者,她们与男性人物的关系也大都是平行的。
乔叶:努力吧!我当然也可能会偏颇。偏颇难免,因为人人都有立场。我试图在自己的局限性中做到最好,尽量不去偏颇,但在这个尽量之后,可能也还有偏颇,那我也认了。毕竟作为一个文学样本来说,也应该会有它的独特色彩和价值可能。我以前喜欢刻意清洗贴在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比如河南作家、女性作家什么的,但现在有时候觉得自己的这种清洗很愚蠢。其实完全可以把这些标签当作一种提醒,我可以深化它们,往更深处、更细微处继续探索,也会有新发现。
三、“非虚构写作”就是深度地、诚实地、鲜活地书写生活
江磊:既然刚刚聊到了现实主义问题,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谈您的“非虚构写作”,因为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实主义的艺术品质和写作伦理,在非虚构写作中得到了凸显。您在《人民文学》2011年第6期、第9期上先后发表了两篇“非虚构小说”——《盖楼记》《拆楼记》,很快就引起了广泛关注。“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文学界掀起的热度已持续多年,作为国内较早创作“非虚构小说”的探索者,您如何看待非虚构写作的发展?您还会写“非虚构小说”吗?
乔叶:《人民文学》杂志的“非虚构”专栏应该是在2010年初开设的,后来又发起了一个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它鼓励作家走出书斋,贴近生活现场,在此基础上去感受、去表达。一批好作品随之出现,如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我很受触动,就申报了《盖楼记》《拆楼记》,也列入了这个写作计划。作品发表后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还获得了当年度的“人民文学奖”,单行本初版时将这“双记”定名为《拆楼记》。
《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专栏现在仍在继续开办,其实我觉得,这个栏目本身在或不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非虚构”这面旗帜下出现了一批好作品。这么多年来,“非虚构写作”仍是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我也接受过多次与之相关的访谈,我想这足以表明非虚构写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它依然是极有意义的课题。至于非虚构写作的发表平台,我觉得它可能被转化了,或者说被分散了,它不再集中于一个刊物上展现。比如我常年订阅的《三联生活周刊》《人物周刊》等杂志上刊登的一些文章,还有我们在微信上读到的那些有深度的报道、人物特写等等,其实都属于非虚构写作的领域,而且都属于从我们最初的“非虚构写作计划”那时候延续下来的创作精髓和实质,我认为可以归为非虚构写作的脉流。在我看来,“非虚构写作”就是深度地、诚实地、鲜活地书写生活,我期待今后能够继续看到好的非虚构作品。至于我自己,如果发现了适合的素材,我也会再写的。
江磊:您的《盖楼记》《拆楼记》被称为“非虚构小说”,而且我注意到,您在以前的一次访谈中也提出了“小说化的非虚构”这个概念。怎么理解您所说的“小说化的非虚构”?或者说,您认为到底该如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理解“写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的关系?
乔叶:这个问题很难讲。我在之前的一次访谈中说:“将‘非虚构’小说化,是想用小说化的技巧来优化我想传达出的那种真实感,使我想传达出的真实感能够以一种更集中更有趣也更富有细节和温度的方式来展现在读者面前。”我要写的东西,如果需要小说的技法才能实现我想要的表达效果,那就可以使用,所以我所说的“小说化的非虚构”主要是指创作非虚构作品时的小说笔法。小说的笔法特别讲究细节,尤其体现在人物心理、对话等方面。
我认为合理的虚构在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比如之前提到散文创作的三个关键词,其中有一个就是虚构。举个例子吧。《拆楼记》里的事件基本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真实性我怎么拿出来证明呢?我想要在作品里表达更真实的效果,或者说让读者得到真实的阅读感受,我可以适当地修改情节,比方说把三天的情节并作两天,但它仍然包括事件的所有内容,我是不是就造假了呢?对于读者来说,这个事件是在两天内还是三天内发生的,有必要像破案一样来确认一下吗?难道就可以由此判断我的写作是虚假的吗?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思考,也都可以构成问题。所以我认为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小说化的非虚构”,我在写作的时候,不论我的认知能力如何,都尽量保持最诚实最素朴的写作态度,以最真挚的情感去写。作品里的细节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亲耳听到的,把这些表达出来,尽力去记述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只能这样做。
江磊: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您曾有过一个“要让飞机找个好机场”的说法,这让我突然想到一个关于真实与虚构的比喻:真实就像“机场”,它是文学创作的落脚点,所以要贴近大地上的现场实情,要脚踏实地;虚构则是起飞的升力,让文学作品最终像飞机一样展开艺术飞翔的翅膀。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是否可以形容您所理解的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乔叶:没有,我觉得你的这个形容不适用于“非虚构写作”。飞机和飞机场的比喻适用于“虚构小说”:我有个想法,要用小说把这个想法给落实了,要让它落地,所以得找个好机场。它更适用于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话题,即让传奇性的故事具备令人信服的日常性,因为飞机飞得再高,也是要落地的。《藏珠记》就是这样:小说有一个传奇性的开头,主人公唐珠吞下宝珠得以长生不老穿越千年,但她这一千多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得让她落地落得踏实、扎实,所以要找到合适的机场。你的说法不适用于非虚构,我觉得非虚构本身就在大地上,它也不太适合起飞,稍微起来一点、低空飞翔是可以的,可它还是在大地之中。
但是,我认为作家在创作“非虚构作品”的时候也有适当的权力:适当地对现有的素材进行组合、拼装、修剪的权力,而非篡改的权力。作家有必要让自己写的“非虚构作品”更好看,更具现场感和真实感。我不喜欢各种成规旧套,各种僵硬的条条框框,写作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冒犯,也就是去试探原有的各种条条框框的边界。试探边界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以前走得还不够远;看到边界才知道,原来它在这儿呢,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江磊:聊聊《认罪书》吧,这部小说无疑是一部厚重的作品,涉及对历史的反思、对人的灵魂的追问等主题,同时也融入了您对很多社会现象的思考和判断,体现出您在拓宽创作空间和艺术视野方面的努力。您曾说这部作品想要探讨的是“平庸之恶”,我也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比肢体的残疾可怕的是心灵上的残疾,比心灵的残疾更可怕的,则是那个年代群体性的精神残疾。”其实世上一切的恶,归根结底都是人之恶,鲁迅先生曾经说的“欺与瞒”也就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残疾”,而上述这些,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我觉得您的这篇小说就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您创作这部作品是否有这方面的思考?
乔叶:对,应该有这方面的考量。其实当时写这个小说是源于对雾霾问题的关注:2013年的时候,雾霾问题非常严重,大家在讨论引起雾霾问题的“罪魁祸首”时有很多种说法,比如汽车尾气、秸秆燃烧、甚至炒菜的油烟。可是,涉及的这些“当事方”都认为自己的问题不大,都认为问题的源头出在别人那儿。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另外,我之前也关注过“文革”问题:几乎全民都参与了“文革”,到最后就只是“四人帮”的问题?那下边的人都干嘛去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于是想:其实任何当下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历史成为历史问题,而任何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也都会延续到当下成为当下问题。所以当时思考到了这个层面上,就很努力地写了这部小说。大概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作家的功能在于做一个病理切片,让大家都来看看这个切片,看清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应该是先说出来,让人看到,如果大家都看不到或者假装没看到,当然不可能引起注意,更不可能解决。
江磊: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期待见到您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乔叶:谢谢!
作者简介:
江磊,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乔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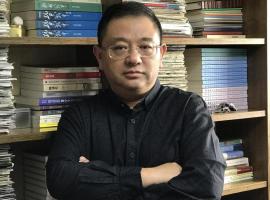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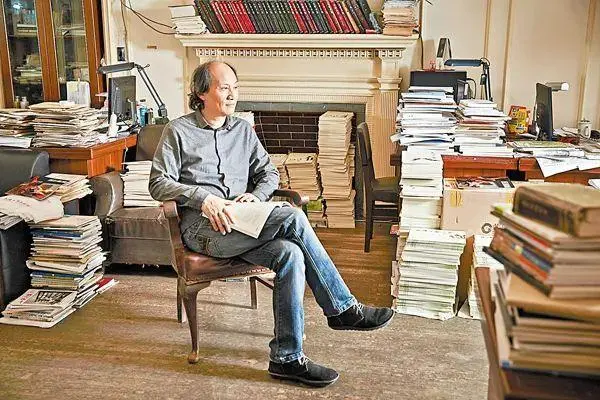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