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本外国文学作品《独居的一年》和《葡萄牙的高山》已入围第二届京东文学奖。
2017年,第一届京东文学奖成功创办,成为国内奖金最高的文学类评奖,其中最受关注的为国内作家作品和国外作家作品,获奖者将得到1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在评选流程上,京东文学奖也采用了专业评委研讨和全民投票结合的方式。
2018年,京东集团继续支持“京东文学奖”项目的开展,评委阵容更加壮大。通过奖励优秀的文学创作者,来激励广大作者的创作动力。
露丝·科尔在她4岁的时候,看到了16岁的埃迪与她39岁的母亲玛丽恩在床上鬼混,《独居的一年》便从一场偷情开始了故事。如此开场,呈现的是矛盾重重的家庭危机,也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欲望、阴郁、与麻烦不断的主人公。
讲述故事的人是美国作家约翰·欧文,他是畅销书作家,被称为“狄更斯再世”。库尔特·冯内古特称其为美国最重要的幽默作家,还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文学偶像。 后者曾于1984年在美国旅行时拜访过约翰?欧文,并且声称深受其影响。
无论如何,约翰·欧文怎么看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但若你走近他的世界,便知道他的人生其实并不完美……
约翰·欧文(John Irving,1942年3月2日-),美国小说家,作品有《盖普眼中的世界》《新罕布什尔旅馆》等,很多作品都十分畅销。他亲自执笔将作品《苹果酒屋法则》(又译《心尘往事》)改编为剧本,并因此在2000年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有病”的畅销书作家
约翰·欧文1942年3月2日出生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艾克赛特,父亲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家里唯一和文学沾边的是他的母亲,当时她是新英格兰一家剧场的提词员。欧文两岁时,父母离婚,六岁时母亲改嫁科林·欧文,约翰从此随了继父的姓,成为了约翰·欧文。
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在上床睡觉之前,花上数个小时为他朗读文学。白天的时光,他会在母亲就职的剧院后台度过,长年观看的大量戏剧演出,对他影响颇深。他曾说过,从戏剧舞台上,学到了更古老的故事情节,而这一点,发生在他能够一个人读懂小说之前。
到了入学的年龄,约翰·欧文入读埃克塞特学院,却得了一种伴随他一生的病:阅读拼写障碍症,以至于不得不去看精神科医生。后来在他开始文学创作时,也多次提到阅读拼写障碍症对他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似乎是正面的。他坦承由于阅读拼写障碍的原因,往往会对手稿修改多次,以确保故事中不会有拼写的错误。为此他重写了许多遍小说内容,又养成了不断重写的写作习惯。当然,这种习惯的直接后果,就是一部又一部小说。
后来,约翰·欧文进入爱荷华作家班,他的老师是著名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纳尔逊·艾格林,前者写出了著名的《五号屠宰场》,后者凭《金臂人》成为美国首届国家图书奖的小说奖得主。
学成之后,信心满满的约翰·欧文于1968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将熊释放》,满期待能够获得世人注目,却像往大海里扔了一块小石子,连个小水花都没有激起来。随后创作的《水疗》《158磅的婚姻》等,也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
直至1978年出版《盖普眼中的世界》,记者们找上门来,报刊上到处是约翰·欧文的报道,他才意识到他成为了一个畅销书作家。自此,他的作品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中就包括直接影响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生活的不完美
在《独居的一年》中,约翰·欧文设置的情节可谓超出想象:16岁的埃迪爱上了39岁玛丽恩,而这一切,正是露丝的父亲特德精心安排的,只为得到女儿的抚养权。这还不算完,埃迪后来发现自己又爱上了玛丽恩的女儿露丝·科尔,正是她在4岁那年,亲眼目睹了埃迪与其母亲的一场偷情。
情节曲折,恰是村上春树受其影响最深所在。村上春树认为情节是一个好故事的基础,在他本人的作品中,这些元素常常出现。不同之处在于,约翰·欧文的主人公,很大一部分是社会的边缘人。
比如说,在《独居的一年》中,作者将视角放在了荷兰红灯区的妓女身上。露丝为了给新书中的故事搜集素材,走进了阿姆斯特丹妓女的房间,于是欧文的笔触呈现了一幅光怪陆离的景象,常人难以窥探的都市边缘人的生活呈现在读者眼前。
事实上,《独居的一年》涉及到相当多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作生活中的边缘人。他们并不占据社会主流,甚至他们的生活除了自己,并没有其他人会过多关注。他们的生活混乱,无助、偷情、背叛、以至于婚姻走到破裂的边缘,这些人物情节的设定,映射的恰是社会现实一幕:尽管焦头烂额,却是必须面对的日常生活。
作家关注现实,对于边缘人群体给予人道主义关怀,说起来容易,但如何呈现是一个特别难以掌控的创作难题。对于尺度的把握如同一盘菜里搁多少盐,搁得多了难以入口,放得少了又寡淡无味。而欧文呈现的方式,是在边缘人为活着而经受磨难之时,又给予人物寻求积极向上的一面,由此甚至让这道菜苦涩中有些甜丝丝的味道了。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生活,甚至是不完美的生存状态。但是,约翰·欧文就是有本事将这些在现代语境中明显道德有瑕疵的人写得不那么让人憎恨。并且让我们意识到,世间的生活,不正是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不完美中,去追求完美的存在?
重复的魅力
如同生活的鸡零狗碎,并不会随着太阳从西边沉没而消失不见,第二天睁开眼,露丝·科尔还是得面对困扰她的一切。重复,成为不完美生活的佐证。
在约翰·欧文的小说中,重复描述发生的情节,显然成为了作品的艺术特色。在《独居的一年》中,最为明显的重复是那句话:“不就是埃迪和我嘛。”这句话第一次出现在开篇,当同样的话再次出现的时候,约翰·欧文为我们讲述的奇情故事已经到了结尾。
两次不同的场景,同样的话语,在重复中的恰是消解及构建文本的同时发生。不仅是在《独居的一年》,在约翰·欧文的其他作品中,重复的情节、场景同样大量存在。比如说在《新罕布什尔旅馆》中多次出现的话:“哀愁会浮起来。”《盖普眼中的世界》更是将“伏流蛙子”重复到令人几乎厌倦的地步。
重复描述,这一文学创作手法见之于古今中外大量作品中,《水浒传》中有一武松打虎,偏又有一李逵杀虎,有江州城劫法场,又有一大名府劫法场,却毫不相犯,以显作者笔力惊人,呈现世情命运之磅礴难测。而在现代小说中,重复的手法往往出现于或首尾相衔、或同景同情,以凸显人物命运之奇崛吊诡。两种不同的创作理念,带来的则是不同的文本效果,并无孰高孰低之分。
严肃文学创作与畅销作家之间能否划上等号,是极难之事。阅读约翰·欧文的作品,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他讲述故事的方式,包括其文风语言等,介于严肃文学与大众流行通俗小说之间。事实上,我认为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约翰·欧文式的作家。最起码,在与电视、手机等媒体的受众争夺战中,读者会因此而选择阅读,这终归是一件好事了。
或许,这也是一种不完美中的完美吧。
Saudade,葡萄牙语,有思念、怀旧之意。它出现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扬·马特尔使用了这个词,来缅怀一只古老的伊比利亚犀牛,而最后,在黑猩猩的带领下,消失许久的犀牛才重新出现。这个曾经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带给我们困惑的作者,又一次带来了新动物的意象,他是在单纯强化自己的风格标识,还是想通过人与动物的故事,解放新的思考?
扬·马特尔(Yann Martel),1963年出生于西班牙,著有畅销全球的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赢得2002年度布克奖,并由导演李安拍成电影,获得奥斯卡奖。代表作:《赫尔辛基罗氏家族的幕后真相》(荣获加拿大“旅程奖”),长篇小说《自我》和《标本师的魔幻剧本》,以及非虚构作品《给总理的一百零一封信》。
难以驯服的小说
对中国读者来说,扬·马特尔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然而我们知晓他的方式却有些不公平。几年前,电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热映,无数人都热衷于解读它的深邃意味,在故事间分析推断。部分观众借此接触到扬·马特尔的风格,仿佛它只是一件电影的衍生品;正如去年《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之后,随电影一同被热议的本·方登。这正是这个“读图时代”的现状,现代人的耳膜、舌头、鼻子、想象中枢纷纷退化,肉眼成为接受所有刺激的入口,人们都在使用肉眼——而非眼睛生活。不过,电影终归是电影,李安120帧的效果并不能挪用到本·方登的小说里,扬·马特尔也是如此。人们或许忽视了,那部电影的成功正是因为李安驯服了一本“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作为原著,作品理应比电影先行一步,只是在电影院外,这个过程被反调了。
总有这么一种说法,在电影改编中,一流的文学作品难以改编成一流的电影——想想一部不如一部的《战争与和平》和《古都》。关于小说和电影剧本的转化,是导演应该考虑的问题。至于小说家本身,他的任务就只有创作。《葡萄牙的高山》再一次用文字创造了一座怪医杜立德式的居所,人和动物在故事里相互交错。
《葡萄牙的高山》和少年pi的故事一样,拥有丰富的视觉潜力。小说开头的节奏就非常快,在一句话的长度里,托马斯就失去了所有的至亲。我们能用眼睛想象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场面,例如托马斯一直倒着走路,他开着一辆像高卢玩具的大汽车;医生欧塞比奥在解剖中从尸体里取出榔头、苹果、鸡蛋、蜡烛、蜂蜜;彼得带着黑猩猩进入人类群落,并在全书的落幕时刻见到一只光彩熠熠的犀牛。
这同时彰显着一种文本的尊严性——它仿佛在抗拒改编。小说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在三个叙事中自由穿梭,无视轴线;但这三个部分如何归顺到一根时间轴上,从而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想,这不仅是未来导演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读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扬·马特尔的小说是一匹烈马,抗拒着蒙太奇效果的驯服,同时也抗拒着读者的诠释。
逆行的动物寓言
少年pi里的动物主角是一只孟加拉虎,而在《葡萄牙的高山》里,主角变成了黑猩猩和犀牛。对于二者,我们不应该去创建“老虎-野性”,“黑猩猩-人性”的对应关系。路易斯·博尔赫斯曾经将世界上的所有动物划分为三大种类,包括陪我们一起看电视的动物、食用的动物、害怕的动物。过度泛滥的人文关怀主义逐渐把所有动物都聚拢到“能陪我们一起看电视”的分类。语言及意义,正是完成这一驯服的优良工具。
《伊索寓言》可能是这项工程的开创者。这本古希腊故事集里充满了大量的动物,但这些动物说白了不过是人类品性的化身。狐狸成为狡猾商人的图腾,鸟总是虚荣的,乌龟勤勤恳恳。扬·马特尔小说中出现的动物则充满不可预知性,谁也无法预料它们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举动。同时,扬·马特尔站在人类中心的外缘,缓缓打开了“寓言动物园”的大门,让被驯服太久的动物横冲直撞地跑出来。
黑猩猩、伊比利亚犀牛、豚鼠、狗……跑出来的动物都挣断了身上的意义锁链。“福音书里说,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扬·马特尔在进行反福音书的信仰书写。恢复自由的动物不再是人类精神的化身,尽管它们依然存在广阔的意味。比如反复出现的黑猩猩像是结合了人性与野性,人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能从中看到荒野的残留。这种质疑也通向人类自身:作为地球上的一员,主导我们内心的,究竟是人性还是野性?
这是一个没有中间道路的思考。因为假如在开始思考时就考虑中间道路,那思考的结果必然疲软无力。动物是扬·马特尔用来将思考过程具象化的产物。他在生态破坏中看到文明的屠戮,于是缅怀那温馨的犀牛;他在人类的历史中看到荒谬与丑恶,于是把黑猩猩摆上圣十字架,来反思意识形态。采用这样的思考方式,是因为在扬·马特尔的内心,信仰与爱永远是破解文明表象、直面生命与死亡的钥匙,只是它不能像寓言那样驯服。它们以无法言说的方式贯穿始终。
《葡萄牙的高山》外文版插图
绝望后浮现的爱
动物是扬·马特尔呈现思想的关键,因此在了解动物的特性后,才能回到《葡萄牙的高山》,去看那三篇名为“无家可归”、“归途”、“家园”的故事。小说中散点分布的文本,才有可能回归到同一条轴线上。
《葡萄牙的高山》里有五个主要人物。第一位少年托马斯是个用奇特方式倒行的人,他在残卷中发现了一个神父关于圣多美岛的记载,看到了黑暗的贩奴史,并得悉神父在神秘的高山区留下了一座神像。这座圣像有可能是破解文明黑暗的关键,于是他告别了伯父,离开家乡。
接下来登场的是欧塞比奥·洛佐拉医生,他和妻子玛利亚·洛佐拉一同生活在悲观的诊所里,夫妻两人都意识到文明的悲伤面,在小说中进行了漫长的对话。医生“自认为在寻找悲伤的起因方面是个行家,但是对于悲伤本身,以及如何面对它,那既非他的医学专业,也非他的天赋所在。所以他才选择了病理学”,一个类似于思想评论的工作,避世、不见人、只和纯粹的理论打交道。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尸检。
而他的妻子认为黑暗的人性裂缝是永存的,并且就是“我们”本身。玛利亚谈起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和耶稣之死一样,我们很容易忘记凶手是谁,只记得被害者的名字。但其实,真正的凶手永远是“神的缺席”,是“无名氏”,如“犹太人-民众-我们所有人”杀害了耶稣一样,也是我们所有人在创造一战、黑奴贸易,以及所有黑暗的历史。唯一不同的是,侦探可以找到破解的方法,但历史不行。谋杀无法停止,黑暗也不会中断。悲观的玛利亚在故事结束时,带着阿加莎的侦探小说神秘死去。
至于先前的少年托马斯,也没有找到答案。尽管他在葡萄牙高山区找到了遗留的圣像,整个旅程却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他只能看到十字架上的猿猴,看不到任何信仰的存在。两部过后,整个故事看似就此沦陷于虚无。这时,黑猩猩作为人性与自然的结合体再次出现,把小说的氛围带向了另一种基调。
回到医生欧塞比奥的解剖室里,走进来第四位人物玛利亚·卡斯特罗。这位玛利亚和医生谈论自己死去的丈夫,谈论与死亡相对的性爱。“爱以一种我最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它伪装成一个男人的模样”,既然爱可以伪装成一个男人的模样,那么人性自然也能伪装成动物的模样。医生解剖的时候,丈夫的尸体仿佛变成了朱塞佩·阿尔钦博托的油画,里面出现镜子、扑克牌、黑猩猩。最后,玛利亚选择躺在丈夫的胸膛里,就像躺进棺材里一样,让医生将她缝进日常生活的躯体,从而“回归于爱”。
虽然出现了一丝光亮,但这依然是私人化的爱,它无法扩张,无法浸染给更多的他者。直到最后一部分《家园》,彼得和黑猩猩奥多的故事才真正释放了“爱”这个词语的全部潜力。人与动物,文明和未知之间达成了和解,生命之间不再彼此心存畏惧,灵魂不再有隔阂——就像曾经的少年与老虎一样。对此,我们没有办法阐释更多,扬·马特尔在全文最后才缓缓抬出的犀牛承载了太多意味,黑猩猩奔向了它,人类也紧随其后,而它却恍如一个亘古的守候者,在草地上原地不动。这头犀牛还会消失吗,我们和体内的黑猩猩在追逐什么,又想要抵达哪里——这是需要重新回到“爱”的空白状态去探寻的旅程。在这个理解爱与人类的过程中,想象永远大于诠释,体验也无可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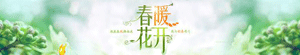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