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族古代有着丰富的文艺美学著述,这些文艺美学著述具有双重性的特点:从思想资源上来看,是印度文化和藏民族文化的结合;从内容上来看,它具有鲜明的佛教美学理想,又贯穿着强烈的身体意识;从形式上来看,它以诗歌的形式阐释艺术理论,是诗性言说和理性逻辑的结合。
关键词:藏族;文艺美学;双重性
在藏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藏学大小五明是其核心的构成部分。它包含了藏族古代在诗歌、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的文艺美学思想。这些文艺美学的理论著述自成体系,内容丰富,全面地反映了藏族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对藏族的文学艺术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藏族文化形成的特殊因素,这些文艺美学思想在来源、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来源:印度与西藏
从来源上来说,藏族古代的文艺美学著述大都译介自印度梵语文艺理论著作,深受印度古代文化的影响。“藏文发源于古印度梵文”“藏文字母从文字结构到书写形式,以至到读音几乎完全是仿造古印度梵文字母”“藏文的文法规则、行文写作格式都是仿照梵文语法结构和写作格式加以融化推行的。”[1]藏语“不仅在词汇方面忠实地以梵文为楷模,而且在文体句法中也是亦步亦趋。”随着藏文的规范化及其与印度文化交流的发展,印度古代医学、数学、天文学、声明学、工巧明、因明学等传入西藏,藏族古代的文献《甘珠尔》和《丹珠尔》,包括文艺理论著作等“几乎完全是自梵语(文)译来”[2](P299)。
传统藏学的大小五明的基础理论部分均源于古印度梵语文化,藏族有关文艺美学思想的著述都是大小五明的组成部分。《画像量度经》《十搩手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和《十搩手造像量度经疏》,即所谓的“三经一疏”,是藏族古代绘画和雕塑的依据和仪规,属传统藏学中“大五明”中的工巧明;《诗镜》是指导藏族古典文学创作的经典著作,是藏族学习“小五明”学科之一——诗学时依据的基本理论。《乐论》是藏族古代的音乐理论著作,属于藏学中“大五明”中的工巧明。这些文艺美学理论无一不是以古代印度的相应著作为蓝本,由藏族译师以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创造了富于藏族特点的艺术理论。《画像量度经》《十搩手造像量度经》和《造像量度经》的作者相传为埃哲布(意为大仙人埃哲之子)。《造像量度经》赞语中“向遍知一切之佛祖顶礼!埃哲山里将佛门”(1)句,埃哲山,是印度一山名,因大仙人埃哲隐居于此而得名,说明这三部造型艺术理论的经典均来自印度。由藏族的堪布达玛达热和译师扎巴江参翻译成藏文,并对《十搩手造像量度经》做了详细的注解,形成《十搩手造像量度经疏》。《诗镜》的作者是印度的檀丁,在西藏萨迦王朝时期,由藏族译师匈·多吉坚赞和印度学者拉卡弥迦罗译为藏文。这些来自印度的文艺美学著作,奠定了藏族文艺美学的思想基础,并被历代藏族学者反复阐释形成藏族自己的文艺美学思想。所以藏族文艺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畴,审美理想和美学标准都来自印度。如《诗镜》说各类成功的文学作品,“处处充满情和味”“一切修饰上,均已赋予了意味”,而“情”和“味”“就像蜜蜂贪花蜜、它使智者得陶醉”。《诗镜》把“情”和“味”看作诗歌美学的理想和标准。“情”和“味”却是印度美学基本范畴,“‘情’。这个词源出于‘存在’,变为名词又可以出于‘使存在’。《舞论》第七章解释说:因为这些‘情’把具有语言、形体和内心表演的诗的意义去影响,感染,注入观众、听众,所以叫做‘情’(使存在)。”而“味”出于“情”,是指渗透一切的对象。印度的《奥义书》赋予了它哲学内容,《舞论》最初赋予它以艺术理论的重要意义[3]。
《诗镜》全篇所举诗例共355首,而描写女子容颜、男女之情的一百七十八首,占全部诗例一半以上。如“进入水中沐浴的女郎,你的笑颜、美目、俊秀的脸庞,必是从夜莲、优婆罗、日莲中,窃取来的吧!美丽的女郎!”“女友!未蔫儿的花!你乳房的表面上,留下新的指痕印,请用上衣快盖上!”“情人被爱欲折磨,女子欲给以宽慰,做出莲花合拢状,示意今宵来相会。”这些诗句以女性的容颜、男女之情为描写的中心,反映了《诗镜》受到印度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具有艳情主义的思想特点。“印度传统美学思想认为,艳情泛指欢乐、美好的情感,主要指男女爱恋的欢快美妙的情感,也指万物有情的青春生命给人美妙的感受。这是由自古以来印度审美理想以生命为美、以青春健康为美的观念发展而成的审美范畴。艳情在两性爱恋的情感中,表现为性爱的美妙、相思的甜蜜和惆怅等。”[4](P150)
藏族古代的文艺美学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美学。无论是诗学理论、音乐理论还是绘画与雕塑的造型艺术理论,都特别注重艺术形象的形式创造,对艺术形象所表现的内容有意忽略。在诗学理论方面,《诗镜》指出:“修饰完美的诗篇,永远流传到劫尽”,论述文学修辞的必要性。而《诗镜》关于修饰及其分类的论述,占《诗镜》全书的百分之八十四。在音乐理论方面,《乐论》正文三章,“论音”、“论词”和“音乐应用”(2),主要表达了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思想,注重形式和技巧。“三经一疏”通篇论述的是画像和造像的量度、尺寸和比例,突出神佛形象完美的形式特征。这些艺术理论著作都不涉及艺术形象的表现内容,更没有哲学升华,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这一点受到了印度美学思想特点的影响。在古代印度“哲学和美学长期不相合,讲艺术的着重形式和技巧,讲哲学的不论美本身,以致在一千年以前,从公元初的《舞论》到8、9世纪的《韵光》,尽管已有美学思想体系,却没有得到哲学的发挥。”[3]西藏早期学者以印度经典为师,他们对艺术形式的强调,显然是受到印度艺术理论重形式传统的影响。
虽然藏族古代文艺美学思想来源于古代印度,受到印度文艺和美学理论的影响,但是藏族古代的文艺美学思想和著作仍然具有鲜明的藏族特点和西藏社会生活内容。“古代藏族的翻译多为译述,而非全译,一向是译中有述,论中有译,译介和论述紧密结合,‘合我实际者译,融我独见于译’,并常常假托于译文而实行著述,以便托名‘传真佛语’。”[5](P373)《造像量度经》文末翻译者堪布达玛达热、译师扎巴江参自述“音译和意译相结合,堪称译著之佳作。”在把印度梵文的佛教文献翻译成藏语的过程,翻译者把古代西藏社会生活内容融入其中,比如在画像和造像度量经中,讲述人体形象各部位的量度,则常以“青稞粒”之长为单位。来自印度的文艺理论,在西藏传播的过程中,被藏族历代学者反复注疏和阐释,这些学者们以“我注六经”的形式,把具有藏族特点的个人的独特见解融入其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注疏和阐释就是一种再创造活动。因而,这些注疏和阐释的文本也就成为藏族和译者个人的理论著述。如《诗镜释难》就是由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著作的,一部为了帮助读者在学习《诗镜》时排除理解上的困难而写的注释。既阐释了《诗镜》的主要内容,又结合藏族的社会生活及语言特点,并举藏族诗歌作为印证,使诗例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很高的艺术造诣,成为藏族文艺美学的新经典。
《乐论》作为藏族的音乐艺术理论著述,全面地反映了13世纪藏族音乐实践。从历史上看,“据藏文史籍《拉达克王统世系》记载,远自吐蕃王国之前第十代首领德晓勒(赞普)时期(约公元前425-385年)‘鲁’(泛指徒歌)和‘卓’已经十分丰富。”[6](P1)萨迦派寺院乐舞形成较早。据《萨迦世系年鉴》记载,萨迦派创始人贡却杰布在举行大法会时前去观光,各种技艺中,“表演本母者按鼓点狂舞,最引人注目”。萨迦派寺院的宗教乐舞和遍布西藏各地的丰富的民间音乐实践,为贡噶坚赞写作《乐论》提供了直接的感性材料。根据藏语的发音特点,《乐论》对印度音乐理论做了修改,使之更符合藏语的特点。《乐论》说:“由于语言、声调的特殊,在藏语中难以使用,因此从六生等演唱法,在此文中不再说明。还要知道按摩喉咙等方法,凡是佛陀所说,与藏语一致的,已经包括在此文中。”《乐论》把音调划分为“扬升”、“转折”、“变化”和“低旋”四种表现形式,依据藏语的读音,分别以(aā)、(la lo)、(a yi)和(a a)来表示。“扬升以平直、上升、收拢、褒扬和贬抑的声调发声”,藏文注释中用藏文五元音表示:a表示平直,e表示上升,i表示收拢,o表示褒扬,u表示贬抑。音乐的发音的基本规律用藏文的读音表现,贴近藏族实际,融入了民族独特的情感体验,显得通俗易懂。《乐论》重点论述俱生乐即声乐,而对各种缘起乐即器乐的演奏与合奏的方法略去不谈。这其实反映了贡噶坚赞生活的13世纪的时代,藏族音乐实践的特点。虽然《乐论》中已经谈及“竖笛、比旺和腰鼓,铜锣、圆鼓和大鼓,小鼓、钹和伽纳智,海螺和多弦琴等等”,而直到17世纪甘丹颇章政权时期,第悉·桑杰嘉措才在《意、耳、目之喜宴》音乐著作中对藏族乐器进行了分类。18世纪,多仁·丹增班觉从内地学习中原戏剧和乐器演奏归来,带回来内地的乐器,组建乐队,用器乐合奏伴奏民间小调的演唱,至此,西藏世俗音乐中开始出现了器乐合奏的形式。此前,原始宗教乐舞和藏传佛教寺院乐舞,虽然已有以鼓、筒钦、比汪等乐器伴奏或合奏,但是一方面乐器简单,另一方面也从属于原始祭祀和供奉酬神的宗教需要,具有神圣性的宗教品格,乐器的演奏技术只是掌握在少数神职人员的手中,仅仅在盛大的宗教节庆才得以展现,所以乐器的演奏和合奏的技巧在那时候并不普及。因此,《乐论》中略去器乐演奏和合奏技法,正是针对藏族当时的音乐实践的实际情况。
二、内容:宗教与身体
藏族古代文艺美学的著作和思想是由于宗教思想传播的需要,作为卷帙浩瀚的佛教经典一部分,由藏传佛教的僧侣自印度佛教典籍翻译、注疏和阐释与撰写而形成的。所以藏族传统的文艺美学著述在内容和形式都以藏传佛教的思想为指导,具有鲜明的宗教特点。
自7世纪起,佛教传入西藏,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信仰,成为西藏社会的意识形态主体,深刻地影响了藏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等。“佛教教义源于释迦牟尼的四谛说”“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人生最苦,致苦有因、涅槃常乐、解脱循道。”[7]所以佛教把通晓“五明”,学习各种知识,获得智慧视为从烦恼的此岸渡到觉悟的彼岸的六种方法即六度之一。《乐论》中贡噶坚赞说能“为助友人之兴而著此文”是“靠前世通晓此学艺的业力,此生方才获得纯洁的智慧。”劝诫人们要学习:“自己若无心思学习一切知识,想成为遍知像天涯一般遥远,这般考虑之后,胜者和诸佛子谆谆嘱咐要把知识钻研。”学习知识是利乐众生,超度苦海的法门。“想做指引众生走向未来的明灯,或是想成为天神和凡人的上师,就是那已经被列为圣贤的佛子,也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学习。”在古代西藏社会,教育仅仅为宗教人士所享受,为宗教垄断。对他们来说,学习知识就是为了成为“明灯”、“上师”或“佛子”。《乐论》于此就体现了明显的宗教目的和动机。《乐论》开头部分“向上师和文殊菩萨合掌致敬!向从诸胜者之法言神变中,生成的金刚妙音躬身致敬!”的赞颂语,就是依照宗教的仪轨,发愿传真佛语。
藏传佛教以为人性就包含着佛性,宇宙本体和佛法佛性就存在于现实事物的形象之中。藏传佛教僧侣的修持方法从根本来说,就是通过现实事相直觉地体认世界本体,证悟万法皆空。佛法佛性与具体形象的结合,就是圆满和完善。“南阳忠国师作圆相以示道妙,沩仰宗风至有九十七种圆相。”[8](P111)佛教思想是藏族古代艺术理论的总根源,艺术形象的塑造是为了思想教化、普度众生的目的。所以圆满就是这些艺术理论的最基本的美学理想。在音乐理论著作《乐论》中,贡噶坚赞说“如果一切皆圆满完善,智者为增长安乐当取之”。把圆满完善视为音乐美的理想。这种美学理想表现在其造像艺术理论中,体现为佛教神佛与人物的形象圆满为主要特点。《十搩手造像量度经》的序文中,佛陀给舍利弗讲说造像法度时说:“如来身量纵广相称,犹如尼拘卢陀树,纵广皆等自身一庹”。在经文中,佛陀各部位和各器官之和,高与宽恰好是一百二十指,即一庹,构成了纵横相等的圆满之相。在《十搩手造像量度经疏》中藏族学者更把这一点发挥为七处圆满的“七高”,“所谓七高,是言佛身七处平满,此七处即两足、两手、两肩头和颈项。”《造像量度经》中的罗汉、佛母的造像身高和宽各108指,护法神形象纵横各96指,将军形象纵横各84指,而侏儒的造像身高与宽也各72指,无论在佛教的品位,亦无论神佛和凡间俗众,身体均呈圆满之相。当然这种美学理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佛祖的造像中,可以说,正是由于圆满的美学理想深深地渗透在佛教的造像艺术中,才构成了佛教神佛尤其佛陀庄严妙好之相。《画像量度经》的主要内容是讲述造像的“量度”,作为佛教的艺术,量度最能体现佛教的教义和思想。《画像量度经》对具体画法提出了明确要求:“直长、滚圆、歪斜状,三角形等诸怪形,不能用在神像上”,应该做到“五官肢体要完整”,“他的身体要圆满”,“面部四角要方形,丰满光泽具美像。”只有这样,“才能圆满得吉祥”。注重完整、统一、和谐,是对圆满的追求,这既符合佛教教义思想,也符合长期形成的藏民族审美趣味。佛陀是佛教崇拜体系的中心,人们把一切美的特征和善良的品性都赋予佛陀的形象上。佛教经典说,佛陀具有“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突出佛陀不同寻常的形式特点,这些形式的特点成为佛陀造像的指导思想,无论“三十二相”还是“八十种好”最突出的形式要求就是圆形,即以圆形为美。
马克思说,人的第一对象是人类自身。从历史逻辑的角度来看,身体是人的存在的直接现实,是世俗生活的基本形象,也是人的文化构建的起点和原型。胡塞尔说“身体是所有感知的媒介”,“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9](P12)艺术是以感知觉为媒介,表现情感的人类活动方式,感知觉是艺术创造和欣赏的核心。在佛教观念中,人之所以在生死轮回的苦海中流转,就是由于六根不净造成的罪业,眼根贪色,耳根贪声,鼻根贪香,舌根贪味,身根贪细滑,意根贪乐境。身体的自然欲望是涅槃成佛的障碍,解脱之道在于禅定修心和持戒修身,其中持戒是基础,就是守护六根的大门,戒除身体的欲望。但另一方面,佛教修炼者进入禅定之中,要诀之一就是“观想念佛”,就是心专注一念,思维集中想念佛陀庄严、美妙的形象。《佛说观无量寿经》中说“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所以“在佛教艺术更为成熟的阶段里,这种强烈的感官性并没有被抛弃,而且也不与精神性相对抗,这两者反而是和谐一致的。”[10](P26)完美的肉体形式和圆融美妙的精神得到高度的统一,身体成为佛性的载体与象征。
“三经一疏”中,众神的形象描绘都是以人的身体为原型,并赋予人的身体因大小、比例、姿势差异而不同的象征意味。更重要的是,画师对众神形象的艺术描绘也是以人物形象的身体为尺度的。《画像量度经》在身体比例和尺度的论述中,表现出以身体特点表征佛教理念,以不同身体尺度显示在佛教世界不同心智成就的意识。首先,《画像量度经》在量度的基础上,突出了天神的奇异性的身体特点,如“与神有关诸人像,嘴上毛须均不长。身上又无汗毛生,像十六岁少年样。人间国王和天神,发长还有旋纹状。颜色绀青异常美,众生一见喜心上。身色如溶黄金液,好似红莲正开放。也如金色瞻波迦,这是转轮圣王相。”还有他的步法、仪态、肤色、装饰以及面、发、鼻、牙、耳、眉、颈项、胸膛,乃至肚脐、腰身、骨节、阴茎、腿部、脚趾、指甲等都各具特点,总而言之,以转轮王为代表的天神,在身体造像的每个细节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特征性,正是宗教理念的形象体现。其次,按照《画像量度经》中的量度,转轮王的身高是108指,依次是贤者106指,玛拉帕吉104指,能明100指,兔王98指。这些神佛形象在身高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呈现出等级性特点,它代表着在佛教世界中,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的品位或成果。人的身高的差异表征着佛教理想世界中差异性的修行成果。佛教艺术中人物形象的创造,无疑反映了佛教的理念。身体的特征和差异,在《画像量度经》中被赋予了独特的宗教内涵。身体是文化塑造的对象,也是文化表征的基础。
《造像量度经》中最主要内容的就是,规定了不同神佛形象塑造应遵循的量度,并视这些量度为神佛形象能否实现其宗教价值的标准。根据在佛教中果位的高低,造像时使用的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十搩手身像之量度,是专讲佛陀、菩萨形象的尺度和技法;九搩手身像之量度,是专讲塑造佛陀、菩萨以下大圣、罗汉、佛母等神祗形象的尺度和技法;八搩手身像之量度,是专讲以威怒为特征的各种护法神形象的尺度和技法;七搩手身像之量度,是专讲塑造金刚力士等威仪形象的尺度和技法;六搩手身像之量度,专讲塑造侏儒及诸矮身像的尺度和技法。佛教造像经典相信,每一类型的神佛或人物造像的头部都是十二指,十搩手之身像总高为一百二十指,头部为身像总高的十分之一,九搩手是指头部为身像总高的九分之一,其身高一百零八指;其余依次类推。从宗教美学的观点来看,雕塑形象塑造的合乎量度,就是美的形象;违反造像量度的规定,任意增量或减量,塑造的形象就是丑的形象。可以说,量度规范鲜明地体现了佛教关于形象创造的美学主张。从美学的角度来说,造像理论在艺术形象的个性化特点的塑造中,凸显了形象结构的比率和尺度的变化会改变形象的意义和审美效果的审美创造规律。按照不同比率创造出来的形象,既具有不同的宗教内涵和象征意蕴,也具有鲜明的视觉特点,形成或影响了人的美感效果。从佛陀形象塑造的比率和尺度来看,佛像的臂部饱满、圆浑,手臂圆润、修长,遵循着佛之手“手过膝”的造像要求。佛像的五官在面部分布比较饱满,面轮短阔、圆浑,面部骨骼结构不明显,眼眶饱满,眼形细长。神态含蓄、安详、慈悲。这些特征正好遵循了八十随形好中“面如秋满月”“目相修广、如青莲花”“颜貌舒泰”等绘塑佛像的标准。它体现着独特的宗教意义的理想美,与现实中的人体比例有一定区别。
在《造像量度经》中对“佛像量度增和减”的功德和危害做了集中阐述:合乎量度的造像,具有无上的功德“纵横长宽皆具量,保佑地方得安然。”详细来讲,“头部适意如宝盖,五谷丰登财宝添。”“额头、眉毛行善美,将能经常赐吉祥。”“口唇塑成鹦鹉唇,众生安乐且得胜”……其他如脖颈、身像、手、大腿、腿肚、足等塑造的合乎量度,都能取得相应的宗教功德。而不合量度,则会产生巨大的危害,“身像若不具量度,地方、财宝均毁灭。长、宽量度若削减,灾荒连年地方毁。”详细地说,“身躯减量成驼背,鼻若减量成怒容,眼睛偏左富贵尽,眼睛过高将折财,眼睛过小则闭合,歪斜、过高或过低,过长、过短均不宜。”……腹部、大腿、鼻子、眼睛、手指、喉头、下颌、胫骨等等不合尺度,就会“五谷减产造饥荒”“罪非轻”“罪孽大”。可见,身体是佛教艺术的审美理想建构的基础和表现的对象。
三、形式:诗性与哲学
藏族古代文艺美学著作,在形式上采用藏语诗歌的形式表达深刻的艺术理论,体现了诗性言说和理性逻辑相结合的特点。
这些古代的文艺美学著作文体都为“颂体”,即格律诗。藏族格律诗形式多样,有七言、九言体,还有五言、六言,也有十言以上乃至二十言为一句等。无论哪种形式,每句字数都是整齐的,如《乐论》“全文共计460个诗句,文中除了有24个诗句为9字句外,其余全为7字句。”[11]《诗镜》“共656首,绝大多数为七字句,共占623首,其余的六字句的1首,九字句的12首,十一字句的18首,十三字句的1首,十五字句的1首。”[12](P247)藏族民间诗歌虽然也有九言、八言、七言或三言等形式,但一般长短句错杂成章。藏族格律诗不但每句字数是一定的,而且每首诗的诗组都是四句,这种形式与佛经四句为一颂的形式相同。
如前所述,藏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著述都是出自印度佛教的经典,从印度的文艺美学著述中译介而来,所以,一方面,深受印度佛教经典四句为一颂的论说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了印度用诗歌写作艺术理论的传统。《乐论》作者萨迦派学者贡噶坚赞是藏族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印度的写作传统,又开启了藏族学者用藏语诗歌写作理论著作的先河。从总体上看,用诗歌形式写作艺术理论,是东方古典艺术理论的基本特点和创作规范。从西藏文化的特殊性来看,《诗镜》说“如果称做词的光,不去照亮轮回界,那么这全部三世间,就将变得黑黢黢。”它把用诗的形式写作,视为照亮世界的方法。这里,把“词”的语言形式与“光”类比,赋予诗歌形式以本体论的意味。从语言特点上来看,用诗歌的形式写作艺术理论,具有明显的诗意性特点。如果考虑到早期宗教和艺术的血肉相融的整体关系,那么用诗歌形式写作就能更加契合佛教梵天传音的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凸显神圣性的宗教意味。
藏族的文艺美学著述善于运用比喻,进行形象化修饰,富于诗情。如音乐理论著作《乐论》:“扬升好像是如意树,转折就像是开花的藤,中低音似流水潺潺,变化如海水中的月影。在集会上歌声像是狮吼,在僻静处像飞舞的蜜蜂,在智者的面前声如鹦鹉,在愚者面前似孔雀开屏。忧伤时的歌声如引升信念,唱情歌似被爱神花箭射中,唱祭祀歌曲如喜人之花朵,净恶似被盐碱河水洗冲。赞颂己方时声音如神鼓,贬抑对方时似慑服仆从,美妙动听如乾达婆之音,混合犹如成串的花鬘。”这里用比喻的修辞说明音调运用的方法。这些文艺美学著述一方面因为丰富的比喻而形成了繁复的形象,富于磅礴的诗情。另一方面把比喻提升为一种方法论。“对于会应用这些音调的人,还要举喻说给他们听,可用箭、弓、铁钩、犁杖、伞、犀角、金刚杵、青稞、波浪和圆轮来做比喻,在任何能发出来的音上,我都看到具有这些物喻。”意思是说:发平直的音似箭,转折音似弓,上转折似铁钩,下转折音似犁杖,上部增大似伞,下部增大似犀牛角,中部细小似金刚杵,中部粗大似青稞,某低音(如人的脚部)与另一高音(如人的头部)相联结似波浪,粗略和细致相混似轮子。由于受印度诗学理论的影响,藏语写作注重“庄严修辞”,把丰富的比喻、形象化修饰视为写作的生命。《诗镜》篇幅最大的内容是讲修饰,依据表现内容和形式,把比喻修饰即明喻分有三十三小类,形象修饰即暗喻分有二十小类,近乎烦琐的比喻类别划分,显示了藏族格律诗对于比喻修辞手法的重视。比喻方法在藏族古代文艺美学著作中的大量运用,使这些理论阐释充满了丰富而具体的形象,在形象的连缀中揭示文艺观点,富有诗性思维的特性。
更特别的是,在叙述的过程中运用比喻的方法,是藏族比量思维逻辑推论的要求。量识理论把量识分为现量和比量两种,“现量也叫亲听量,是使所了解之境悉现于前,为心识亲自验证的正确认识,亦即不经过逻辑推理而直接得到的感性认识。比量也称势所量,是所量之境不在眼前,根据经验知识和正确比喻而认识的真理,也就是通过一定的逻辑推理而产生的知识。”[7]比量是藏传因明学即逻辑学中量识理论提出的推论方法。比量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思维,它运用宗、因、喻三支的固定模式进行思维。宗是观点主张或大前提,是逻辑推理之本,因是理由或原因,喻是比喻,三者结合推出结论。这种逻辑推理的方法,是僧侣的辩经和理论著述中基本原则。可见,运用比喻是比量推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作为一种艺术理论,运用比喻的方法,就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要求。
运用大量的具体事物比喻,使藏族古代文艺美学著述中充满了生动而丰富的形象,这种运用具体形象说明抽象理论的方法,赋予具体形象以特殊意味的文艺创造原则,从深层来说体现了藏传佛教具象思维的特点。藏传佛教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清净的,具有佛性,由欲望而生的烦恼,迷失了本性,可以通过对现实的观想,体悟缘起性空之理,觉悟成佛。所以,通过对具体事相的体认来证悟佛性,是佛教修持的基本方法。这种证悟成佛的方便法门,从思维方式来看,就是“从具象直达本体,从直觉进入体验,用感官直接去诱发心灵顿悟把握佛性的思维方式”[7],具有具象思维特点。具象思维也称形象思维,就是仅仅依靠感官直观,而不是经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过程,直接地把握本质和规律的思维方法,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运用具体形象或符号去反映抽象的意义。在艺术创造中,形象思维的方法就是通过对物象的加工,使具体的形象和符号赋予象征的意味,所以佛教艺术就是以象征性手法去表现佛教的观念、情感和精神。藏传佛教是藏族传统社会的普遍信仰,它的具象思维的方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宗教艺术创造,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藏族人的思维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藏族古代文艺美学著述中以比喻为主的形象化方法,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藏族古代文艺美学著述在结构上有着严谨的逻辑,具有鲜明的哲学品格。如《乐论》从整体上看,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绪论说明写作的主旨,正文第一部分“论音”、第二部分“论词”第三部分“音、词结合运用的规则”,最后是结束语,总结全文。既讲音、词创作理论,又讲音词结合的表演方法和技巧,把音乐创作理论与表演实践相互结合,以严谨的逻辑结构全文,富有鲜明的理性特征。其次在论述的过程中处处贯穿着辩证的思想,讲各种音调的综合运用,“像弓和箭要搭配在一起”,又反过来讲“单一方式唱不出优美的歌声”;讲作词的原则,对“有功德者”“智慧者”“有教养的人”等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敬重,而对“妄自尊大”“一味骄横”“废弛教规戒律”的人等要呵斥;再如在“音、词结合运用的规则”中,先正面阐述音词正确运用的方法,又从反面阐述音词运用的弊病和缺点,正反结合、逻辑严密。再次在叙述的方法上,先总说,次分说,再讲各部分的综合运用,然后再总结。其他文艺美学著作如《诗镜》包含三个部分,即诗体、修辞和诗病。论述时先对诗歌进行分类(论及各类关系);再依次穷举类项目;再对各项目加以定义;最后是各项目诗例。这样的论述方式在思维上层层推进,不仅给阅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使《诗镜》多年来成为诗歌创作者们速查的诗歌创作指南和手册。再如《画像量度经》正文包括“求画”、“供画”和“量度”三个部分依次交代了佛教绘画的缘起,宗教功能和各类形象的尺度与比例,遵循着事理的逻辑。这些文艺美学著作有着严谨的逻辑结构,体现了著述者们深层的理性思维的特点。可以说,由比喻呈现的形象表层结构内隐深层逻辑思维的特点,是藏族古代文艺美学在形式上的突出特点。
综上所述,藏族古代的文艺美学著述具有鲜明的双重性特点:从思想资源上来看,是印度文化和藏民族文化的结合;从内容上来看,它具有鲜明的佛教美学理想,又贯穿着强烈的身体意识;从形式上来看,它以诗歌的形式阐释艺术理论,是诗性言说和理性逻辑的结合。这种双重性特点的形成,从其根源来说,是由于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一方面形成了粮食农业和饲养牧畜并存的双重生产方式,“西藏经济主要由粮食农业和饲养牧畜的结构派生而来的。”;另一方面形成了定居生活和迁徙生活并存的双重社会形态。“事实上,居住地的自然环境本身就迫使西藏人的生活具有双重形态”[2](P123)。这种具有双重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对其思想意识和文化创造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桑德.略论古印度梵语文化对西藏传统文化的影响[J].中国藏学,2005(4).
[2]石泰安著,耿昇译.西藏的文明[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
[3]金克木.略论印度美学思想[J].哲学研究,1983(7).
[4]邱紫华.印度古典美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于乃昌.附记[A].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资料初编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6]嘉雍群培.藏族文化艺术[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7]彭英全,乔根锁.藏族传统思维方式管窥[J].中国藏学,1993(2).
[8]钱钟书.说圆[A].谈艺录[C]北京:中华书局,1984.
[9]理查德·舒斯特曼著,程相占译.身体意识和身体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0]劳伦斯·比恩尼著,孙乃修译.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1]萨班·贡噶坚赞著,赵康译.乐论[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4).
[12]赵康译.旦志·诗镜[A].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资料初编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注释
1文中所引《画像量度经》《十搩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诗镜》引文资料均出自《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2文中《乐论》引文如无特殊注明,则均引自萨班·贡噶坚赞著,赵康译《乐论》[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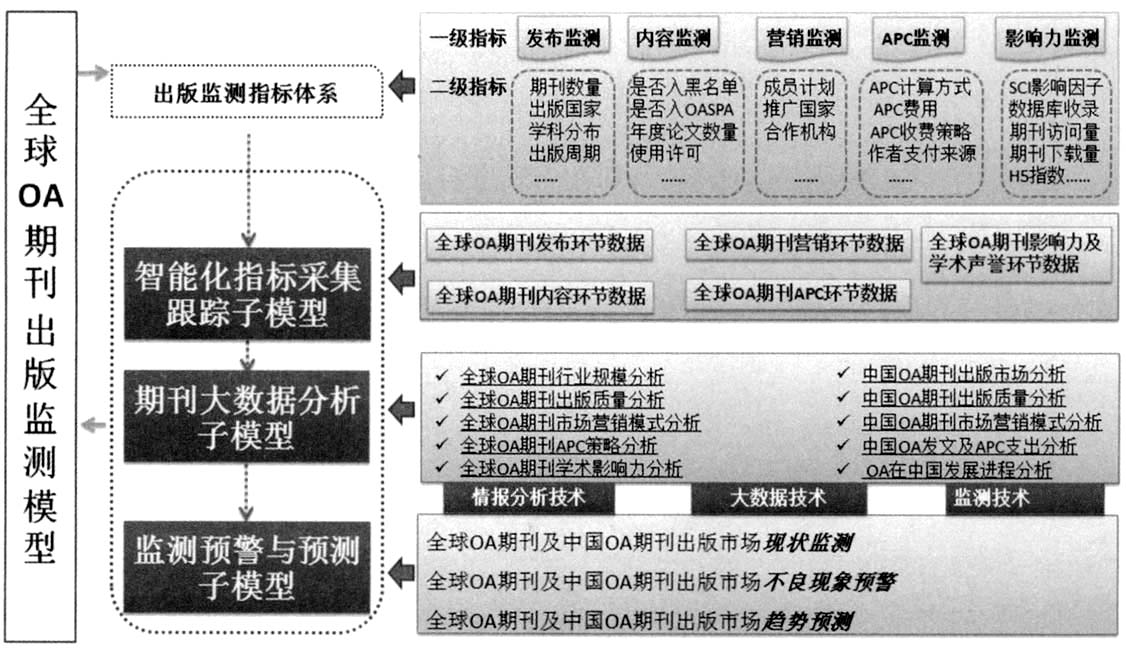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