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路藏在一片闹市中,路口浅灰色拱形石牌坊掩在树荫下,稍不留意就能走过头。
东起四川北路,向西折北再与四川北路交汇,“L”型的多伦路像一只老电话的传声筒,挂在四方市井里。“叮咚”“叮咚”,踩着三轮单车的老伯摇着铃铛穿过。繁华都市里听见此声,竟有时空错乱的感觉。抬头看多伦路的石牌坊,“海上旧里”四个大字跃入眼帘,往里走,人文故居和文博店铺接踵而来,青鼓鼓的弹格路凝成一个个记忆的落点,摁进脚掌。路上,能够寻觅1930年代中国“左联”作家的音容,能够找到华洋交织的文化形态、经世致用的文化性情。
从印着“窦乐安路”的老路牌开始,多伦路将它的传声筒贴近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
叩开名宅公寓,穿梭先生们搏击暗夜的旧时光
多伦路从头走到尾,只消十分钟。然而如果沿着历史的脉络细细品味,花上大半天也不为过。马路过去叫窦乐安路,为1911年英国传教士窦乐安填河建造而成。窦乐安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亲手所造的马路,将填满一个时代的中国的伟大故事。
靠近那些中西合璧的文化旧里,透过神秘魅人的窗格向里窥探。一时间,景象翻飞如走马灯。
首先看见的是一位蓄着胡须、着长衫的人。他径直来到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底层一间小教室,冯乃超、冯雪峰、钱杏邨、夏衍、柔石、殷夫等四十多位作家或站或坐,有人趴在窗台朝里看,有人堵着门。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 ‘韧’……”鲁迅先生站在讲台上。那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这支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作家队伍和其他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者们,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战斗中发出振耳惊雷。
鲁迅回到景云里的家,夜已朦胧。先生抽开椅子,桌上堆着杂文、书信和讲稿。1927年 10月,鲁迅许广平夫妇入住景云里。在景云里的两年多时日,与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冯雪峰、周建人、柔石等人为邻。那时,茅盾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冯雪峰编《萌芽月刊》;叶圣陶编《小说月报》,扶掖丁玲、巴金、戴望舒、沈从文、朱自清等大批文学新人;柔石与鲁迅共同创办朝花社,写出《二月》《为奴隶的母亲》……
作家们总去多伦路四川北路路口的公啡咖啡馆聚会。鲁迅在《革命咖啡店》一文中写道:“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躲开巡捕房“包打听”,幽静的公啡咖啡馆见证了 “左联”的酝酿、中国新文学的涌动。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左联存在的六年间不断遭到残忍镇压: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一批革命作家被害;大批左翼和进步书刊、书店被查禁、捣毁……然而,屠刀下的左联作家都是勇士。他们存在一日,壮大一日,以文化、科学之锋芒搏击暗夜,照亮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天空。
岁月更迭,作为公共租界的多伦路不断涌入各方力量,明暗交织。左联完成了历史使命,抗日战争爆发,马路一度被日军海军陆战队占领;抗战胜利后,住进了汤恩伯、白崇禧、孔祥熙等国民党大员。人们说,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数尽风雨沧桑的多伦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成为住宅区。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多伦路在市井营生中褪去光芒,成了一条热闹拥挤的“马路菜场”——小贩摆摊,鸡鸭齐鸣。道路失修,夜晚人不留神,摔一跟头是常有的。盛夏忽然一场暴雨,坑坑洼洼的小马路便寸步难行。
人们发觉,曾响彻文人跫音的多伦路正蒙上风尘,为人淡忘。为了让记忆留下来,多伦路在一轮轮城市更新中,发出人文的呼唤。
老店铺里流连忘返,在这里找回岁月与初心
上世纪90年代初,虹口文化人率先提出以鲁迅公园为轴心,以多伦路一带名人故居、文化遗址为内涵的“雅文化圈”构想。1998年,虹口区政府对多伦路名人寓所、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保护和开发。提出的愿景,是建设集名人故居、海上旧里、文博街市、休闲社区为一体的文化名人街。
1997至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副校长的郑时龄主持团队为多伦路进行改造设计。童年居住于此,他熟悉多伦路的肌理。他说,“建筑是一个创造人性的场所,融入文脉,而不破坏城市空间的和谐。”
1999年10月,路过四川北路的人纷纷停下脚步。透过树荫,上海市老领导汪道涵题写的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牌楼跃然眼前。往深处走,以中国传统建筑造型铸造的鸿德堂安宁伫立,法兰西新古典主义情调的汤公馆、阿拉伯风格的孔公馆等名人公馆焕发神采。老建筑松动神经,纷纷苏醒。
慢慢走,风景旧曾谙。鲁迅、叶圣陶、茅盾、郭沫若、丁玲……如果你忘了他们的样子,可以在屋檐下、树荫里见到他们活灵活现的铜像。他们无意用纪念碑式的架势横在路中间,更不会干扰视线。“L”型道路的分割点上,郑时龄团队设计的“夕拾钟楼”朗然而立。钟楼的气息,对所有追寻历史的人有着神奇的功效。人们从日常思考中解放出来,绕着多样建筑兜兜转转,无意停息。
步入“L”型道路的另一截,将看到一些有趣的店铺,比如旧书店、私人博物馆。有家专收老物件的博物馆,白色雕花石库门门楣朝向马路。人们难以列出在这儿买得到的所有老物件:月份牌、老路牌、黄铜台灯、蝴蝶缝纫机、马灯、搪瓷杯和别些种类的旧家什;人们不知应该瞻仰那堆到天花板的“三五牌”座钟,还是应该拍下那些仔细用塑料纸包着的《申报》《新闻报》《小星报》——据说那儿有三万多种、总重量超过一吨的旧报纸。让人流连的并不是物件的本身,而是那些物件所代表的历史。它们让城市的记忆一齐觉醒而把你包围起来。彩色弹珠是一代人的童年,“三大件”里有小康家庭的变迁……不只是个人往事,还有这个城市过去、现在与未来。
博物馆不远处有一家旧书店,爱书的人只要来过,都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住在附近的青年,要是晚上睡不着觉出门闲逛,也许会碰见它仍亮着灯。也有专门赶来找书的学者,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翻着泛黄的书页。如果听见书店里传来“啊!”的一声,没准是有人发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宝贝书。守着16平方米书店的老店主看着来客从少年长成壮年,早已打定了主意,要陪着这些爱书人走下去。
世纪之交,多伦路上涌现的民间博物馆多达十余家:筷子馆、瓷器馆、钟表馆、石头馆……如今,那些时光筛后而留存的店铺,怀着不忘过去的初心,成为人们乐此不疲谈论的马路地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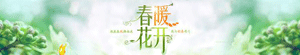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