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的文学史不可能拿我的见解去做主流,甚至我的很多看法和主流文学界是相反的,但我的心态就是去做个补充。”
毕飞宇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以来,以一个作家的趣味选择了许多经典名著进行讲授,他的课颇受学生们欢迎,还陆续被邀请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讲课,这次毕飞宇干脆把课堂公开给了所有的读者与听众,推出了首部音频节目《毕飞宇和你一起读经典》,这是目前国内首档由作家推出的音频节目。这档节目将会在蜻蜓FM和喜马拉雅FM同步首发,随后陆续登陆豆瓣、知乎等国内知名音频平台,而毕飞宇也将从一个小说家艺术家的视角,对13部中外经典小说等进行解读,内容依据他在大学里所讲的课程为基础,包括《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故乡》(鲁迅)、《项链》(莫泊桑)、《杀手》(海明威)、《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等多部名家名作的解读。郭采洁、郝蕾、江一燕、林海、路内、梅婷、王宁、王雪纯、祖峰、周一围等众多名人都参与录制了名著的原文朗读。
《书香周刊》在毕飞宇这次从南京来北京录制课程音频的空当与他聊了聊讲课那些事儿,采访过毕飞宇多次,纯聊“教学”不提写作还是头一回,他也乐得从一个受关注的作家暂时变为一个有个性的教师。毕飞宇算是作家走上讲台最受关注的一位了,这和他课堂上充满着有趣见解分不开,他对于大众知名的作家,往往有与众不同的解读,不过毕飞宇对此很轻松,他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学者,他把自己定位成文学课堂上“有趣的补充”,一个“教授后面捡稻穗的”。毕飞宇看来,阅读是写作的第一步:“如果真有写作的天才,他首先是一个阅读的天才。与众不同的阅读的才华,最终让你在输出的时候成为一个写作的高手。”
《书乡周刊》:多年来你作为一个作家,一直以文字与读者交流,这次是以声音与听众交流,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毕飞宇:任何一个人刚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对事情本身是不熟悉的,我刚进(录音)棚的时候,说实话也有压力。我是苏北人,有很重的苏北口音。如果我能像赵忠祥那样,每个字都读得很好,那当然好。但我是一个写作的人,也不做播音员,也不做演员,普通话不好。我觉得我普通话就不该好。在我比较累的时候,嘴瓢的时候,许多方言就出来了。内心我是想说普通话的,控制不住了。
《书乡周刊》:这次出的音频是大众的,可能绝大多数听众都不是文学专业出身,是文学爱好者,对他们讲课与对中文系的学生讲课有什么区别?
毕飞宇: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在大学里给中文系的学生们讲的时候有些纯理论的东西,有时候反而会讲多一点,这个音频的课程里面理论有好多处我全都拿掉了,估计很多人对这个没兴趣。其实我没上过课,一直都是讲座的形式,讲座和课程有区别,讲座我讲一个话题、一篇小说就可以,讲座和讲座之间可以没有逻辑性,但是课程要求教师拥有比较完整的学术能力,我不认为我有能力在大学里开一门系统的课程。
《书乡周刊》:在你的观察里,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的课程存在哪些问题?
毕飞宇:老师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某一个具体的作品上花很多时间去一字一句地分析,就是文本细读。小说家在高校里面讲课就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补充,这个补充是必须的。文本细读其实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但是我觉得有点遗憾地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跟西方比起来唯独有一点是有缺憾的就是文本细读。
《书乡周刊》:上次你推荐给我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就是文本细读的典范。
毕飞宇:这本书特别好,它里面的解读特别有意思,比如作者把《红楼梦》里但凡名字里有“玉”的,都跟贾宝玉做了一个分析,你注意到没有,不仅仅是林黛玉,还有妙玉、蒋玉菡等等。大部分人觉得文学批评要用一个高屋建瓴的方式去完成,但对于文本内部许多重要的点可能会遗漏。如果说文学教授是前面割麦子的那些人,那我就是在后面捡稻穗的。
《书乡周刊》:你在课程里也专门有一节课讲《红楼梦》,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可能我们都看过各种各样的分析,现在人教版初中的教材里也成为课文了,这个对于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是不是有点深了?
毕飞宇:《红楼梦》是个特例。它和鲁迅的东西还不一样,鲁迅的东西是“只深不浅”,但《红楼梦》是“可深可浅”。至少它里面的爱情故事是能读的,女孩子们之间的鸡零狗碎是能读的。在我看来,“可深可浅”的小说是最高境界,这样的作品就带有海洋的特点,可以到海滩捡贝壳,也可以去深海去。
《书乡周刊》:当然在中学的语文课堂上讲《红楼梦》也不是你在大学里讲《红楼梦》这种讲法,可能需要归纳总结中心思想什么的。
毕飞宇:在我看来,老师们有个硬任务要完成,那就是传授知识。但对于作家来讲,知识一定不是强项,作家的强项在于阅读的能力。作家走上讲台是个好事,可能会对学生阅读的能力上有所帮助。
《书乡周刊》:我还记得你说读到王熙凤在秦可卿死的前后的表现,“一步一行来欣赏”,看得你从床上忽然坐起来,吓出一股凉意,这是年少时候读不可能有的感觉。
毕飞宇:没错。我相信即便是我看了这么多遍,《红楼梦》里一定还有我没有发现的东西,这跟它的写法有关。要是《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或《战争与和平》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
《书乡周刊》:但其实在少年时代的阅读还是很重要的,虽然不一定能读明白,但还是要读。
毕飞宇:是的,都说“囫囵吞枣”不好,但我看来有个很大的遗憾却是我少年那个时代“吞枣”的机会不够多,我那时候阅读量还不够大。每次当我真正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其实是盲目的,许多东西我是通过自己的写作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如果我17岁之前阅读量能翻个几倍的话,我相信我写东西起手会更快。
《书乡周刊》:你在讲课的时候有很多与众不同的见解,比如你说张爱玲,要是你和她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正好要和她一起过马路,你会不太敢去搀扶她,因为可能她的身体没有温度,她的手也没有温度。
毕飞宇:我在讲课的时候也说,张爱玲是《红楼梦》的一个次生物嘛,次生物能有多大的价值?最了不起的作家一定是原创性的,哪怕有很多瑕疵,因为原创是最难的。如果我是以一个大学老师的身份去讲,说不定有的时候我会向主流的文学评价妥协,但我是一个作家,这就是我的个人看法,任何人都可以来批评我。未来的文学史不可能拿我的见解去做主流,甚至我的很多看法和主流文学界是相反的,但我的心态就是做一个补充。
《书乡周刊》:比如你第一节课就讲《聊斋志异》,把蒲松龄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把他跟屈原、李白、杜甫放在同一个高度。
毕飞宇:我特别渴望未来学者们在修订文学史的时候,能给予蒲松龄更高的文学地位,因为他是中国文学史最顶级的作家。我的依据很简单:屈原是第一个以私人身份写作的人,李白毫无疑问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曹雪芹用白话把长篇小说推到了巅峰,白话文短篇小说的喜马拉雅是鲁迅。那么用文言文写短篇的最高境界是谁呢?就是蒲松龄。我所说的这几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把自己的类型写到极致,所以他们应该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是我的逻辑。(陈梦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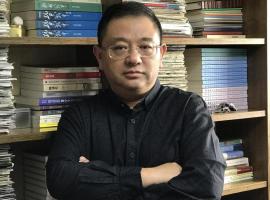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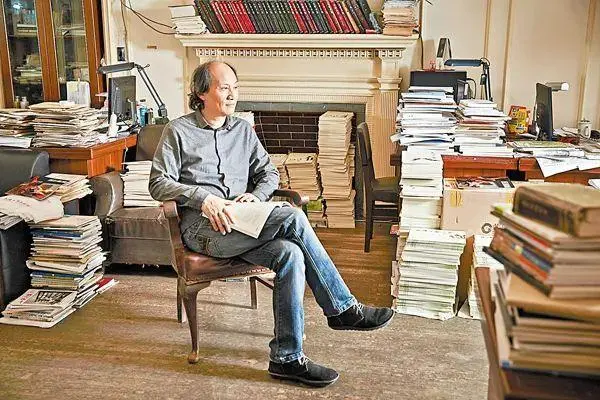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