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2月3日,90岁的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英国剑桥的家中去世。
出生于富庶犹太家庭,以德语、法语、英语为母语,文学批评家、翻译理论家斯坦纳自称“中欧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和欧洲文学语言如数家珍,会多门语言,博览群书。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涉及语言、文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的影响。英国小说家拜厄特(A.S.Byatt)曾把他描述为“一位来得太晚的文艺复兴巨人……一位欧洲玄学家,却有着了解我们时代主流思想的直觉”。
在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大背景之下,1944年,斯坦纳到了纽约,成为了美国公民,他一面反思大屠杀,一面观察现代生活中语言的退化,并以此为基础在1967年完成了代表作《语言与沉默》。身为“中欧人文主义者”的斯坦纳在纳粹军官身上看到,一个人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读歌德和里尔克,却不妨碍他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为什么会这样?他追问,文学和知识究竟应该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斯坦纳看到,语言是文化的代表。现代西方政治上的非人道(尤其是纳粹),伙同随之而来的技术化大社会,使得大众教育教出了“一种特殊的半文盲,只在非常有限和充满功利的范围内阅读和理解”,导致了语言文化的滥用与污染,使西方文学的创作陷入自杀性修辞“沉默”。
为《语言与沉默》作序的学者李欧梵认为,斯坦纳在书中展现出了“纵横四海”的批评方法。斯坦纳指出,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文学批评家,势必非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读西方的经典著作,与文盲相差无几,而局限于一国的文学,也是井底观天。所以他批评他的老师——牛津大学的名批评家利维斯(F.R.Leavis),说他只论英国文学,专捧劳伦斯(D.H.Lawrence),但是如果把劳伦斯的作品与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则显然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他最恨文学上的褊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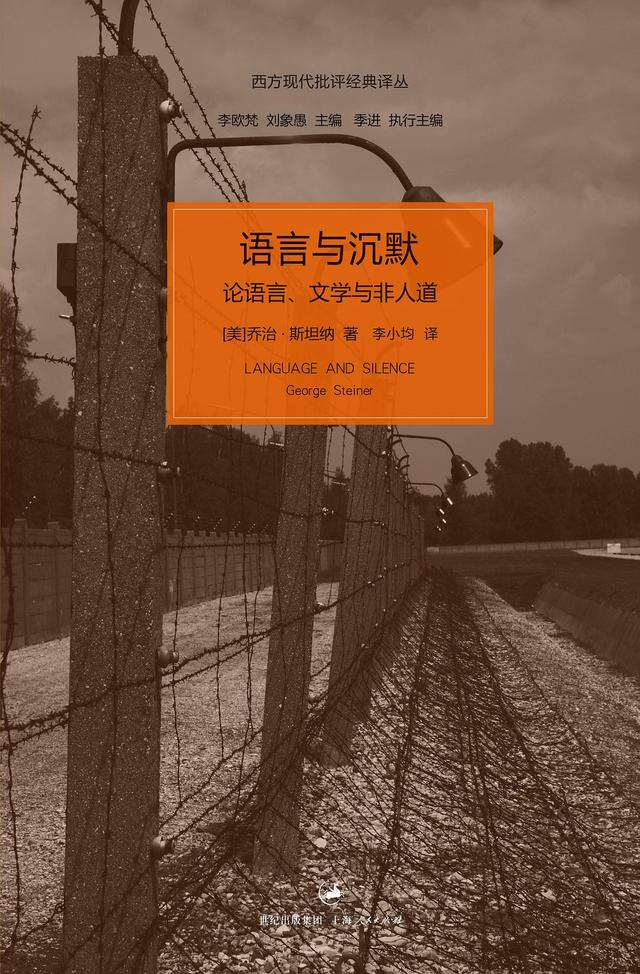
《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美] 乔治·斯坦纳 著 李小均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1
和2019年去世的哈罗德·布鲁姆一样,斯坦纳不是结构主义或精神分析这类“理论家”。他认为,理论是人类失去感知耐心的堕落表现,不仅简化了语词的丰富性,还剥夺了文学鉴赏和阐释功能的独特尊严。他说,理论在文学、历史、社会学等论述上的胜利,其实是自我欺骗,是因为科学占据上风,人文学科为了背水一战而发展出来的。
在《语言与沉默》当中,斯坦纳一直关注人文素养(humane literacy)这个概念。他指出,在阅读中,读者不是被动的角色,批评家对于同时代的艺术有特殊的责任。批评家“不但必须追问,是否代表了技巧的进步或升华,是否使风格更加繁复,是否巧妙地搔到了时代的痛处;还需要追问,对于日益枯竭的道德智慧,同时代艺术的贡献在哪里,或者它带来的耗损在哪里。作品主张怎样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人?”李欧梵称,“在此书中,他处处反思欧洲文化经历纳粹浩劫后的反响,令我深深感动。我再三咀嚼此书中的篇章,甚至学习斯坦纳的英文文体。”在文学评论中,斯坦纳正是这样显示出“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
在文学批评领域,斯坦纳让人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不是二传手,而是进行再创作。在翻译研究领域,斯坦纳也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当中,译者逐渐从边缘地位上升到文化传播者和历史参与者的中心地位。斯坦纳1975年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提出的阐释学有关理论成为了研究译者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在本书中,他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判断,并且指出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信任,就是译者相信在原文本中一定有能够可以理解的意义。侵入,则反映在译者的理解上,因为译者“无法不对他的时代和背景妥协”,而译者的侵入也可以让原作在译入语当中获得第二生命。吸收是译者侵入的目的和结果,译者应该引进并消化原文的核心信息。但译文必然会改变乃至重置原文的结构,在侵入和吸收之后,损失无可避免。因此第四步补偿,就是达成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平衡。这四个步骤无不与译者的主体性相连,在“茶杯、麦克风、译员”成为主流,译者常常拿来与机器翻译进行比较的今天,翻译家也不断地引用斯坦纳,来为自己存在的价值辩护。
随着哈罗德·布鲁姆、乔治·斯坦纳等当代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相继离开,我们或许正在迎来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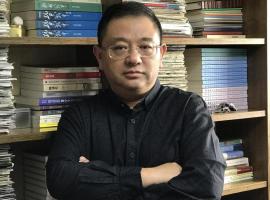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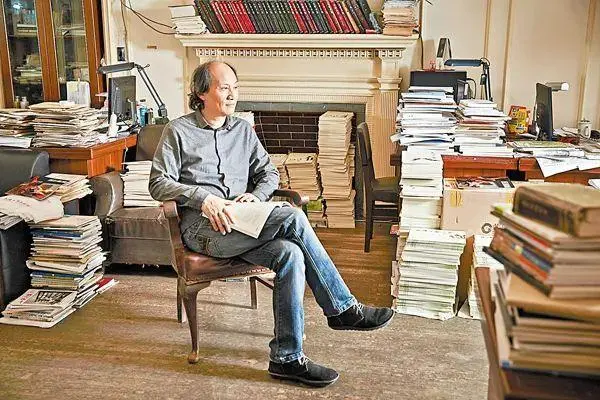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