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墩子,1992年生于陕西永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江南》等期刊发表小说多篇。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滇池文学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虎面》。
一个理工大学材料系的学生,对文学满怀热情,从大学时代写小说起,到现在他已经写了八年。
八年间,他发表了大量作品,也屡屡遭遇退稿的打击。但这个从偏远西北小镇走出来的青年人,身上似乎有着一股韧劲,他不害怕跌倒,一直在写作这条孤独的路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坐标。
继《我从未见过麻雀》后,今年他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虎面》。他就是90后青年作家范墩子。日前,范墩子获得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的“年度最佳小说奖”。应《中国青年作家报》之邀,笔者采访了范墩子。
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便是故乡
问:获奖对于创作而言,是一种肯定,尤其这是一次特殊时期的获奖,什么感觉?
范墩子:我没有想过自己会获得哪些奖,在这之前,只是埋头苦写。获奖有运气成分,谁也无法左右这些事情。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老老实实去写自己的作品,就足够了,经过这几年的历练,我深深感觉到,自己对小说有着一种纯粹的爱,我无比热爱虚构,热衷于在小说里创造各种人物,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也是高于获奖这件事的。
问: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你也数次通过网络直播,来和读者进行对话交流,分享新书《虎面》,这些体验,未来会写在小说里吗?
范墩子:我也不知道,可能会出现在小说的某个细节里,也或许不会。我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比如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几个人物,他们的形象格外清晰逼真,似乎他们每天都在对着我呐喊,希望我能将他们写出来。我的理解,写好人物,是小说的基本,但并非根本。而现在,我还处于要把人物写好的阶段。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几个人物写好,至于别的东西,我考虑不了那么多。小说本来就需要慢一点,和时代保持一点距离感,这样的话,才能看清楚一些东西,不至于迷失,也不至于找不见自己的坐标。
问:《虎面》是你在书写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小镇,你怎么看待故乡这样一个本体?在创作中,为什么会夹杂着如此复杂的情感?
范墩子:不得不承认,古老乡村的文化内核已经在消亡,甚至正在断裂,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变化的。如果把这种变化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知晓我们今天究竟丢失了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那种狭义的故乡概念了,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那些童年记忆,可能是关于城市的,可能是关于乡村的,甚至还可能会是关于县城和乡镇的。
问:故乡的生活经验,和你异地求学的经历形成了某种映照。你如何看待这种映照?
范墩子:在故乡时,渴望逃离故乡。不在故乡时,却常常怀念故乡。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无论我在咸阳,还是沈阳,或者别的地方,毫无疑问,我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故乡,我的心里也不再有以前那种狭隘的故乡概念。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故乡不再仅仅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它可能存在于我童年的记忆里,也可能存在于我的小说里。以前我憎恨故乡的村镇,但现在我对那个村镇充满了爱意,我不仅能看到它黑暗的地方,也能看到它光明的地方。
用小说表达我认识的现实
问:第一次读你的小说,是你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在你的创作上,巧妙之处就是规避了陕西已有的“三座大山”,另外选择了一条道路,用现代的手法来写乡土,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创作?
范墩子:我从写作开始,就没有想过将自己归在某个地域范围里,我对自己的定义是做一名汉语作家。用汉语表达我自己所想到的,所观察到的,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要去继承什么传统,我手里仅有的武器就是汉语。我也不知道我的小说究竟算现实主义文学,还是算先锋主义文学呢,我脑子里装不了这么多的东西。我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我所认识的现实。未来哪怕仅仅能够触及现实的一角,那我也觉得我的小说是有意义的。
问:反复书写童年记忆,带给你怎样的体验?
范墩子:现实本身就是沉重的,人们总会陷入悲伤或者虚无的情绪当中。快乐的时光毕竟是短暂的。我忘了我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一句话:你们的快乐吓坏了我。《虎面》就是一本充满着悲伤记忆的小说集,有的是写小镇上的青年,有的是想尝试一种别致的叙述,多少表明了自己的一点写作野心和理想。尽管这是本记忆之书,但我并不希望在书中
哀悼以往的生活,我更希望通过记忆之门,去窥视未来。很多人都在哀悼记忆,哀悼那些已经灰飞烟灭的东西,但往往越是被我们哀悼的东西,却往往叫我们感到安心。藏身在记忆里,是人的本能,只不过现实太叫人感到虚妄罢了。
用小说留住这些记忆
问:《虎面》 中,有描写乡村葬礼仪式上的杨喇叭,也有《鹧鸪》的主人公阿翔,带有着现代性的迷茫与无奈。对于人物的刻画,为何如此执迷?
范墩子:要说杨喇叭这个人物,就必须提到《火箭摩托》里的张火箭。是在写完张火箭这个人物后,我才想到要去写葬礼歌手这样一个角色。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群体,他们常年活跃在乡下最不起眼的舞台上,给人们带去或快乐或悲伤的歌曲。这也是一份精神层面的营养。他们也有欢乐,有梦想,有着想去大舞台表演的幻想,但现实中他们却只能守在让人们泪流不止的葬礼舞台上。他们是村镇的一部分,更是村镇记忆的一部分。写杨喇叭、张火箭等这些人物,其实也是在写那些正在坍塌的现实。记忆会随着肉身一同死亡,但却永远也不会消逝,用小说去留住这些记忆,也是我自己写作上的追求。
经常阅读我小说的朋友会发现,我热衷于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鹧鸪》就是描写了主人公那种恐惧的心理过程。但要谈这个小说具体表达了什么,我也谈不出来什么。我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在了小说里,解剖小说的内核是我的弱项。换句话说,我是在追求一种叙述上的现代性,这个过程包括人性上的现代性,也包括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问:你是怎么想到吸收文言笔记小说的经验来进行创作的?
范墩子:蒲松龄是我眼里的大师级作家,《聊斋志异》在我心目中的分量,超越了四大名著。《一个将来的夜晚》是想去写未来的爱情,但我却将时间定格在了久远的上古时代。一个猎人与三个狐狸精的故事。写法上的确是想致敬古代的笔记小说,不仅仅是 《聊斋志异》,也包括冯梦龙的小说。那段时间,我正着迷明清笔记小说,阅读了很多,于是也就试着去写了这样一篇。
河南的孙方友先生是写笔记小说的高手,他的《陈州笔记》我看过一些,非常老到,烟火气息浓郁,是不可多得的好小说,遗憾的是,他多年前就去世了。韩少功也写过一些。笔记小说算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 不拖沓,在很短的篇幅里,还要写出烟火味,写出奇特的想象来,这的确是不容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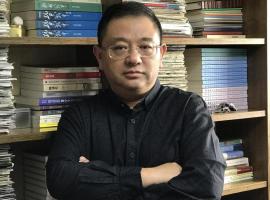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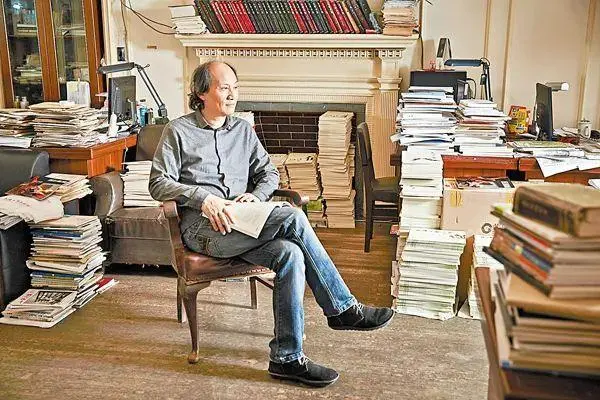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