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晓航是当下中国城市叙事的重要作家,作为一直生长于城市的“60后”,他无疑深谙城市内在的丘壑肌理,深切了解其间的种种生态、各色人物。也许恰恰因为太熟悉,他反而喜欢避实就虚,抛开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呈现,常以想象力搭建自己的城市空间,这个空间映照着现实城市,这里当然有世俗的生存经验,更有他看重的城市的存在与文化经验。
晓航的小说与他本人一样,充满了“异质与独特”的元素。作为理工科出生后又从事贸易的他,似乎游离在文坛之外。从他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 《师兄的透镜》中即可发现,写作于他而言更像是一场精神的思考与探讨游戏,他也不同于接受了中外文学系统教育的作家那样谙熟写作的种种门道,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结构自己的小说,也因而无所顾忌,别有新意。
新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长篇《游戏是不能忘记的》依然延续了晓航的城市叙事,在由环保、游戏、科幻、技术共同建构的城市里,他展开了自己对于城市存在的想象与描摹,借由一座城市的重建,呈现了对于城市生存之本的思考。
记者:问题从标题中的“游戏”二字开始,韦波创造的新离忧城,“游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游戏”。看上去你似乎强调的是“游戏”的意义,但事实上小说的内容却指向了它带来的种种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传统意义上的善来拯救。为什么设置的是“游戏”?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有让你选择它来成为新城规则的原因。
晓航:这个问题我从两个层面来回答,第一,接地气地说,选择离忧城的内容是游戏,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好玩,一个充满游戏、可以在游戏中生活的城市我没有见过,我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第二,相对一点说,游戏精神恐怕是人类具有的一种本质精神,人对于游戏的渴望来自灵魂深处,其实就是对自由与解放的渴望,也是对于打破人类自身局限性的渴望。这就是我选择游戏的原因。
记者:城市叙事,这是你小说的一个标签。这部小说依然如是,其间包含着城市生态、金钱利益、人工智能等等,我们当然可以从中找到现实城市的某种映照,但如你所说,你因为现实主义不如生活本身丰富而对于其有某种排斥。然而,作为一个生长于北京的人,你其实深谙城市的种种丘壑肌理,所以选择现代主义或者说超现实主义是某种意义上寻求更大的真实吗?更甚者,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的哲学思索?
晓航:我对现实主义的认识确实是有一个过程,年轻的时候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相当不以为然,因为现实的丰富性远远大于现实主义创作本身,这个难题是明摆着的,可以没什么人思考或者说大家都回避这个问题,更没什么人想办法解决,作为理科生我受不了这种自欺欺人。但是,从2012年起我开始写长篇,我对现实主义的看法有所转变,觉得现实主义创作当中的一些优点必须学习,比如对于人物的塑造与刻画,我原来写小说,从来不顾忌这些,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爱谁谁,什么这那的,我爽就行。
当然,我现在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批评性看法依然没有太多改变,我觉得人必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自己所运用的创作方法被一些朋友叫做“智性写作”,大致就是用现实的砖搭建一个非现实世界,但是这个非现实世界是直指现实世界的。我这么做从2001、2002年就开始了,主要就是为了对现实进行超越,就是想解决我上面提出的那个难题,这其实也应该是其他艺术门类的某种传统性做法,就是主观想尽办法超越客观,这样文学艺术才能发展,而不是被简单地局限住,如果甘于被客观局限,就干脆别干这行了。
至于我表达的城市确实与其他人完全不同,骨子里我觉得是我对城市的体验更深刻,认知更完整一些,因为我全部的生活经验都来自城市。不同于那些进城的、打工的、市民化的、民俗化的城市小说,我的小说既关注世俗的生存经验,更关注存在与文化经验,这也许就是你说的追寻更广泛的真实以及对城市的哲学思考。说白了,有些小说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短的产品,我的小说则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的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形的哲学基础的问题,光年头长肯定也不行,还得学会从哲学的角度看问题,得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记者: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城市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是焕新—游戏—恶的滋生—善的救赎,乍一看这不是一个新的设计。但我想你应该有自己的考量,为什么最后是凌驾于人之上的“超级计算机”系统产出的“好人”代表的善拯救了这个新城?“善”和“道德”在你这里仍然是城市的重要准则。
晓航:你描述的城市建构过程很对,实际上,我很少看小说,我这样结构小说,只是我自己逻辑思考的一个结果。至于为什么超级计算机会让系统产生好人对城市给予拯救,我的逻辑是这样,因为在最赚钱的“坑人游戏”系统中产生不了好人,“坑人游戏”是一个逐利的体系,它的所有兴趣就在于坑人,并且因此产生利润,这个系统运行下去的话,好人是要给团灭的,让这个系统自我抑制、自我拯救是不现实的,因为大家还是要挣钱的,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外部系统,给“坑人游戏”注入一个正面因子,由那些系统产生出来的“好人”,用善和道德去对抗那些坑人的、全然逐利的倾向,善与道德的重生是我对于离忧城最大的渴望。
记者:有评论认为你这样的设置其实是你的理想主义,佐证了你对于城市的情感。事实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城市书写与情感?确实有一种理想主义一直在影响着自己的创作吗?
晓航:毫无疑问,我一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既是我的自豪也是我的悲哀,理想主义当然影响着我的创作,我终生不会放弃它。
我和城市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我生活在城市中,所有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都在这里,我跟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看着它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也看着它越来越肮脏,越来越臭气熏天。我爱它、恨它,却永远无法离开它。我没有什么归隐情结,也不想出国,只想在我所在的城市终老,即使它有时不时空气不好,有化学食品,有难喝的水,但是我还会长久地待下去,直到和我的爱人垂垂老去。这个城市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一直向前,作为城市的表达者之一,我会在整个生命的历程中讴歌它,批判它,为之痛苦为之欢乐,为之汗颜也为之自豪!
记者:谈谈人物。韦波这个利益至上的野心家和商人,赵晓川这个边缘人一样的人物,他们二者的对应关系是这部小说里最重要的一种,他们各自代表、牵系了城市的不同人群,最终也是因为赵晓川认同超级系统的“善”,并由此影响了韦波。能不能阐述下这两个人物的意味?
晓航:这两个人的关系实际上体现了我对城市、对人的一部分理解。他们俩是发小,从小就是好朋友,但是他们的路完全不同,韦波利欲熏心,兢兢业业,最终功成名就,成为城市的创造者。赵晓川则是一个“loser”,他一味地逃避、奔跑,不愿意承担压力和责任,但是他对于城市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洞悉,他也很聪明,能想尽办法活下去,混个温饱,而且在浑浑噩噩之中竟然成为城市中自由的偶像。这两个人道路完全不同,个性也不同,想法也不一样,但是很奇妙的是,他们竟然是朋友,能互相倾听,互相接纳,互相帮助,关键时刻还能挺身而出。其实,这种关系的设置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广大、包容和善意,人与人之间可以完全不同,但是这不妨碍他们是朋友。我所在的城市,有一部分人是讲性情的,不那么功利的,他们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权,只在意你是不是跟他投脾气,是不是朋友。很多时候,有人会批评那个城市的人,你们看他们成天吊儿郎当的,也不那么努力,他们则会说,累不累啊你?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拥有一种相对豁达的生活态度。
记者:有评论认为你的这部长篇,以“纯文学”的标准来看,也存在语言泥沙俱下、叙事欠缺收敛和节制等问题,说你喜欢欧阳锋式的十八般武艺,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掠过一切,而不是在某个细微的角落流连忘返——与我们通常所在意的“深度”相比,你更在意“广度”。关于这个问题你是如何回应的?这其间应该有你的文学观。
晓航: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和行超探讨的这个问题,她的大致意思是,我小说中有很多点都比较有意思,只是我一般都会迅速滑过去,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她认为我应该在这些点上深挖一下。我当时的回答是,我喜欢《天龙八部》里慕容世家的武功,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有一次慕容复化装成一个西夏武士和段誉动手,瞬间使了六十四种门派的武功,那种形式化的东西是我极为向往的。我的打法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心中有很多武功招式,打起来的话不拘一格,随便挥洒,珍珠翡翠白玉汤一般用在一起。其实,那些东西我都是花很长时间研究过的,别人看到了可能非常感兴趣,想多了解,可是对我来说是用得比较熟了,就一带而过。总体来说,行超希望我深入一些,她说的是纵向,而我更喜欢像一只鸟一般掠过整个世界,我喜欢横向。
很有意思的是,我最近听到很多人的观点和行超很类似,我已经开始在想,也许大家的看法是对的,我应该注意一下,在该深入的时候认真深入一下,但是应该在哪里停留,在哪里深入呢?这个我现在还完全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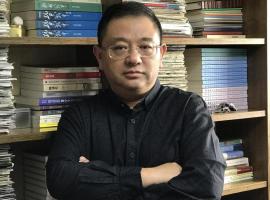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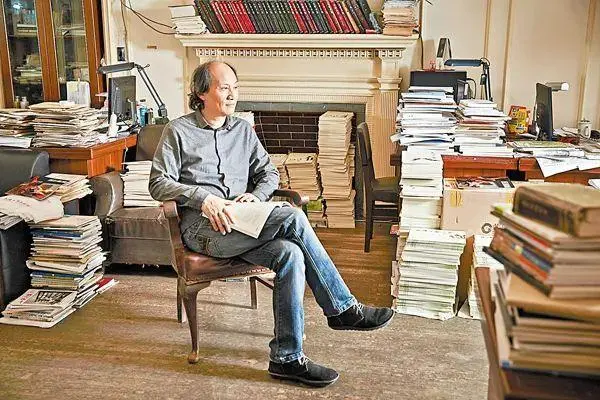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