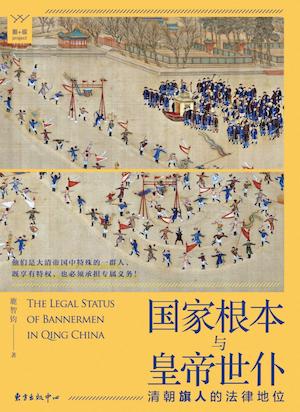
作为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的少数民族王朝,清朝皇帝如何以“征服者”之姿,在统辖广大的汉人臣民同时,又维持本民族的特色和统治地位,当属近三十年来清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
在欧立德(Mark C.Elliott)等学者看来,清朝成功统治中国的基础有二:一为树立起新儒家式的道统(Neo-Confucian legitimacy),二为保持满人身份的特殊性。而八旗制度的存在,则是清朝能够推行满洲本位政策,保护身为“国家根本”的旗人群体的利益,并形塑满人之族群身份认同(Ethnic identity)的重要条件。这种论述固然揭示出八旗制度的重要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特权联系在一起,实则是简化了旗、民关系的历史复杂性。
有鉴于此,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鹿智钧《国家根本与皇帝世仆: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一书,通过各种满、汉文的清代司法档案,动态地剖析了清朝针对八旗成员所作的刑法、民法和行政法设计,揭示出旗人群体在某些层面上享受到法律特权的同时,亦要在其他方面承担义务和身份束缚。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既能维护旗人的“国家根本”地位,亦将八旗嵌入帝国秩序之内,最终得以长期统治中国。
本书除第一章《绪论》和第六章《结论》外,内容计分为四章:
第二章《旗人的刑事规范与司法制度》共有三节,依次是“‘犯罪免发遣’律的制定与意义”“旗人刑罚中的‘新例’与‘发遣’”“旗人的中央司法审判与诉讼制度”。
入关以后,清朝在处理刑事案件时主要采用大明律,摒弃了大多数的关外旧俗,尽量让旗人与一般民人的刑罚趋于接近。然而,这一举措却存在两点例外:一为保留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的鞭刑,用以对等汉人的笞、杖刑;二为旗人若犯流罪,则免于流放。这就意味着清朝在采纳汉人的法律时,并未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而是“巧妙借由对旗人施以‘同罪异罚’之法化解”。但长此以往,旗人如果犯有徒、流罪均可豁免,势必使旗人不畏刑罚,导致犯罪问题日益严重,清朝无法继续透过部分关外旧俗的实施保证旗人的特殊性,便发明了折中的“枷号刑”,规定以枷号日数和徒、流之刑相抵,这就是旗人“犯罪免发遣”律的诞生过程。该条法律在解决旗、民的法律差异时,亦保证旗人不会被流放到各地,为皇帝保有一批巩固政权的力量。
“犯罪免发遣”律于雍正三年(1725)被正式修入清律后,其适用对象就随着皇帝的考虑而多次改变,包括汉军、旗下家奴、旗人中罪大恶极者等八旗成员,都在被调整的范围内,而这种调整实为约束旗人并维持旗、民身份界限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犯罪免发遣”律并非旗人所受刑罚的全貌,另外还有处理旗人命案时的“新例”和旗人的“发遣”刑等。所谓的“新例”,也被称作“满洲杀死满洲例”(在实践中亦将八旗蒙古、汉军纳入考量),出现于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规定旗人之间的命案均处重典立决,朝廷意图借此重整日趋败坏的旗人风俗。至于旗人的“发遣”刑,作者特意区分了其与“犯罪免发遣”律的区别。“发遣”刑是一种独立于徒、流刑的刑罚名称,即将犯有严重罪过的旗人发配到边地并承担劳役(发遣当差、为奴)。这两种特殊的刑罚表明,旗人在法律上并不单纯是法律特权的拥有者,皇帝有时反而会基于恢复旗人纯朴风气的考量,加大对旗人的法律惩处力度。
最后,对于与旗人有关的刑事案件,清朝会以何种审判和诉讼制度来应对呢?顺治初年,清朝一方面采取旗、民分治的政策,规定各级地方衙门无权直接惩治不法旗人,必须将其移交北京刑部处置,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弱化威胁皇权的八旗势力,允许旗人越过领旗贝勒、固山额真直接向刑部申诉案情,使得刑部以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之姿涉入旗人的司法案件。但是,这些案件给刑部带来繁重的工作量,朝廷被迫重新提起分层审级制度。例如,康熙时期就在逐渐赋予步军统领衙门、八旗都统等以部分初审权和司法权。但是,八旗都统的司法权始终处于被皇帝限制的状态之下,皇帝出于稳定政权的考虑,并不希望八旗的特殊性过度抵触于国家的司法体系。
第三章《旗人的民事规范与民事纠纷》共有三节,依次是“八旗田房政策与旗地纠纷的处理”“八旗俸饷制度与旗人的钱债纠纷”“八旗户婚制度与旗人的家庭纠纷”。
本章的核心问题是,清朝针对旗人的民事司法实践,是否存在特殊性,或者说有无将关外旧俗带入关内?作者分别从田土、钱债和户籍三个方面讨论了这一问题。
以田土为例。顺康时期,清朝沿用关外的“计丁授田”制,通过“圈地”将旗地统一分配给旗人;同时还将内城的民人驱逐到外城,空出旗房用来安置旗人。清朝虽然规定旗地、旗房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旗人只拥有使用权,但这些规定无法阻止旗人手中的不动产流入民人之手,且由于满人对产权手续的一窍不通以及清朝官方的疏忽,导致围绕旗产的法律纠纷时有发生。面对层出不穷的旗地、旗房的争讼案件,清朝特于户部设有“八旗司”、“现审处”等机构,并严禁旗人在地方州、县衙门递送呈词。
以钱债为例。清朝既视旗人为“国家根本”,便从多方面照料旗人生计。自康熙中叶起,由于八旗人口激增,很多旗人无法继续披甲当差并享受国家福利,再加上旗人生活的日益奢侈化、清朝严禁旗人从事其他行业等原因,旗人的生计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很多旗人都会向他人借贷,故而必然出现各种旗人之间、旗民之间的钱债纠纷。面对眼前的社会危机,清朝除了向发放给旗人更多的生活补助外,还积极地查缉向旗人放高利贷的不良分子,避免国家发给旗人的钱粮遭人鲸吞。清朝为此多次修订条例,试图以严刑峻法恫吓众人不得放债于旗人,似有防范于未然之意,但这种努力最终被证明为毫无成效。如果旗人生计不能得到根本改善,举债度日便在所难免,而相关纠纷只会层出不穷。
以户籍为例。清初民人若为旗人奴仆即可进入旗籍,但成为旗下家奴后想重返民籍则并非易事,多数旗下家奴都只能私自脱逃,这就是扰民甚深的“逃人法”的由来。康熙时期,“逃人法”被废止,清朝逐渐放宽政策,允许旗下家奴在八旗内开户乃至于赎身出旗为民。但由于旗下家奴的流动实与正身旗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也就会产生两者的户籍纠纷。其次,作者讨论了八旗的婚姻习俗,指出入关后的旗人婚俗直接继受汉制,传统的收继婚、一夫多妻制都宣告瓦解。最后,作者注意到旗人家庭的继承制度的变迁,入关后的家产诸子均分政策、户绝立嗣规范均无异于汉民,只是严格维护旗籍的纯粹性,严禁非八旗成员的民人和旗下家奴继承旗人的家产。
第四章《旗人的行政规范与行政制裁》共有三节,依次是“旗人的政治参与和官员处分制度”“旗人的披甲当差与兵丁相关约束”“旗人的人身与迁徙自由限制规范”。
本章聚焦于八旗官员规范、八旗兵丁规范与八旗人身自由限制规范三方面,以行政法的角度梳理旗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首先,作者梳理了旗人的政治参与情况。清朝通过官缺、科举、升转等方面的优待,谨慎地保障了八旗官员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八旗官员也会承受比汉官更重的行政制裁,包括解任、革职削爵和财产刑,这些都源于关外旧俗。顺治初年,汉官们发现八旗官员的行政制裁过于严苛,仅因小罪便被降革世职世爵,或者籍没家产,而汉官则只是简单的降革官职和罚俸,便唿吁朝廷予以改革。直到康熙年间,这些针对八旗官员的独树一格的惩罚才彻底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其次,作者注意到旗人在披甲当差时所承受的各种约束。例如,旗人一旦成为国家兵丁,就必须参与定期的武备稽查。朝廷既要检验兵丁的骑射能力,对未达与否要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亦要核查军事装备是否完整齐全,凡私自典卖兵器者均移送刑部法办。对于出征在外的兵丁,清朝对军律与军令极为重视,违反号令者轻则鞭刑、重则正法。总的来讲,旗人若以当兵为职业,结果似乎是利弊参半,难以断言为好处还是约束。
最后,作者以旗人的逃旗问题为线索,指出旗人缺乏迁徙自由的事实。逃旗,即旗人私自离开北京或各省的驻防地。清朝一方面认为旗人是“国家根本”,不能轻易散于众多汉民中;另一方面认为旗、民分隔,有助于避免旗人失去满洲本色,且能防止旗人侵扰地方。自干隆时期以来,清朝对旗人私逃者的处罚日趋严苛,最严重的惩处甚至包括“撤销旗档”。上至八旗出身的官员,下至普通的闲散,均处于这些法令的约束之下,可见旗人之于国家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
第五章《皇帝对旗人扰民事件的态度》共有二节,依次是“八旗军队扰民事件及其相关处理”和“日常生活的旗民冲突与官方对策”。
通过前三章的讨论,本书已展现出旗人的法律地位与普通民人之间的微妙差别,但这种“与众不同”却也蕴藏着某种潜在的危机。清朝皇帝要在追求八旗特殊性的同时,保障帝国各成员间能和谐相处,而若想在“满汉一体”与“旗民分治”的两端之间取得政治上的平衡,其实并非易事。本章通过八旗军队的扰民、旗民的日常冲突等问题,展现出这种政治努力的困难程度。
就八旗军队的扰民而言:在入关之初,八旗军队存在掠夺老百姓的财物、伤杀民人、奸淫民女等行径,这些都与关外时期的作战习惯密切相关。但清朝并未继续姑息上述恶行,反而对违法者严惩不贷。在康熙、干隆年间,清朝则在持续对边疆用兵的同时,继续管控查缉着出征的旗人。不仅如此,清朝皇帝在外出巡游时,亦会严格约束扈从的八旗兵丁的一举一动,防止出现扰民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盛清以降的八旗兵丁还会被移调到他地驻防,在迁徙的过程中若有扰民问题,朝廷往往会对涉事者从重制裁。由此可见,八旗兵丁身为“国家根本”,虽被皇帝所重视,但皇帝照顾旗人的同时,亦会重视地方秩序与民人感受,尽力消弭民人对于旗人的负面印象。
在日常生活中,清朝利用户籍使旗、民相互区隔,而当旗、民因冲突进入司法程序时,便象征着两种体系的相遇。在京畿地区,清朝通过五城御史、步军统领衙门与刑部的两级司法审判程序处理此类问题;但在八旗驻防地,旗、民冲突就会带来比较复杂的司法程序。因此,清朝特地设计出理事同知、通判的制度,专门负责会同地方民官审理旗、民交涉案件,并根据审转制度逐级上报。
除此以外,清朝皇帝对旗、民冲突的审理,往往会依照法律采取大公无私的态度,鲜有刻意偏私之举,旗人在这些冲突中并不占有过多优势。然而,清朝皇帝的终究目标并不在于宣传朝廷公正严明的形象,而在于彻底减少旗、民之间的冲突。皇帝认为这一目标的关键实存于驻防八旗官员的身上,如果八旗官员能够妥善地教化、管理旗人,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惜这些计划都在地方遭到抵制,基层的八旗官员经常包庇旗人的违法行为,导致旗、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清朝皇帝所希冀的旗、民和平共处的景象终究难以完全实现。
综上所述,本书从法律条文、司法实践两个角度,剖析了清朝对旗人的法律定位——作为国家存在之基础的“根本”所享受到的特权,以及作为皇帝之“世仆”所被迫承受的束缚——清朝借由这种特权、束缚的并存关系,在赋予旗人特殊地位和待遇的同时,尽全力调和因此衍生的满汉矛盾,最终得以将各族帝国臣民统辖于皇帝一身。
本书核心观点的初衷,在于修正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也译作魏复古)的“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理论。作者在《绪论》和《结论》章节指出,不宜将辽、金、元、清这四个人为定义的“征服王朝”简单地混为一谈,魏特夫的理论有“描绘‘征服王朝’一致性特征的企图”,进而存在“导引出北亚历史’一元性’发展”的嫌疑。因此,必须要通过比较征服王朝的“社会、文化的二元性”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谓社会的二元性,即王朝统治者给予“征服者集团”的特殊待遇,而文化的二元性是指“因俗而治”。作者在解读清代旗人的法律地位时,始终不忘在同页脚注中对比辽、金、元三朝的法律情况,以比较法学的视野阐释了“四个征服王朝不可一概而论”的理论关怀。
然而,作者的理解是否为魏特夫的本意呢?这其实是我对本书的最大疑问。
征服王朝论固然是一种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但这一理论的提出却与美国人类学在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博厄斯学派(Boas school)有直接关系。博厄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林顿(Ralph Linton)曾于1935和1936年提出假设,两个文化的触碰、交流会带来多种结果,某一方完全地被吸收(Absorption)或同化(Assimilation)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此外还可能会出现涵化(Acculturation)的过程。在林顿看来,“使涵化成为可能的接触类型,更可能是通过征服,以及征服集团在被征服者之间的定居过程产生的”(the type of contact which makes acculturation possible is more likely to arise through conquest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conquering groups among the vanquished)。魏特夫的研究其实是对林顿和博厄斯学派长久以来观点的唿应,并提供历史上非西方世界的涵化案例——“在征服和政治隔离的条件下,汉人是否吸收了他们的征服者”(Did the Chinese ever absorb their conquerors as long as the conditions of conquest and political separation persisted)——这在《中国辽代社会史》的书中都有明确的学术史梳理。魏特夫在书中对金、元、清三朝的简要介绍,本意或许并非是有构建北亚民族历史发展的单向序列的野心,而是将其处理为情况类似但细节不同(作者在第23页的注释①中也如此承认)的历史人类学案例。
作者还引用了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研究,说明征服王朝在入主中原前夕,已“兼有农、牧两种生产形态”、“具备多民族国家的特征”,意指魏特夫过于强调“北亚族群自成系统的历史进程”。但这一判断的问题在于,魏特夫也持相同观点:“满人进入中原时已经具有类似汉人的想法……祭祀时虽然仍用牛马,但在……征服华北的十九年前,已经引进了汉人的农业礼仪。”(the Manchus entered China already imbued with quasi-Chinese ideas……Horses and oxen were still offered in sacrifice,but the great Chinese agricultural rites had been introduced……nineteen years before the conquest of North China.)更为重要的是,魏特夫在论证时亦和作者一样引用了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且征服王朝论的诞生过程恰与魏特夫和拉铁摩尔的学术交往分不开。如果作者以拉铁摩尔的研究佐证自己对魏特夫的批评,显然需要更为详细的说明。
另外,基于清朝入关前文化的多元性,确如本书“绪论”所言,涉及如何界定“征服者”、“征服集团”、“被征服者”的问题。但是,征服者的组成是否一成不变呢?八旗汉军一度无法适用“犯罪免发遣”律,被清朝待之如汉民,随后又调整回适用的状态,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跨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界限的行为?就此而言,作者没有给出直接回答,且未能在书中与研究汉军与征服者身份问题的柯娇燕(Pamela K.Crossley)《晦昧之鉴》(A Translucent Mirror)有所对话,殊为一件憾事。
纵观全书,作者对魏特夫的超越主要在于以法律史的视角,系统而全面地指出八旗制度并不单是要保障特权,更有使旗人承担义务的作用。魏特夫则认为,“汉人被征服后,满人采取许多手段保护他们的权力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特权”(Once the Chinese were subjugated.the Manchus took many measures so safeguard their power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ivileges arising from it),但特权并非清朝透过八旗制度形塑满人特殊性的唯一取向,而作者从法律史的视角挑战了这一传统研究中的疏漏,使我们对清代的族群政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实为本书学术价值的体现。因此,尽管在宏观的理论构架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本书不失为一本清代八旗研究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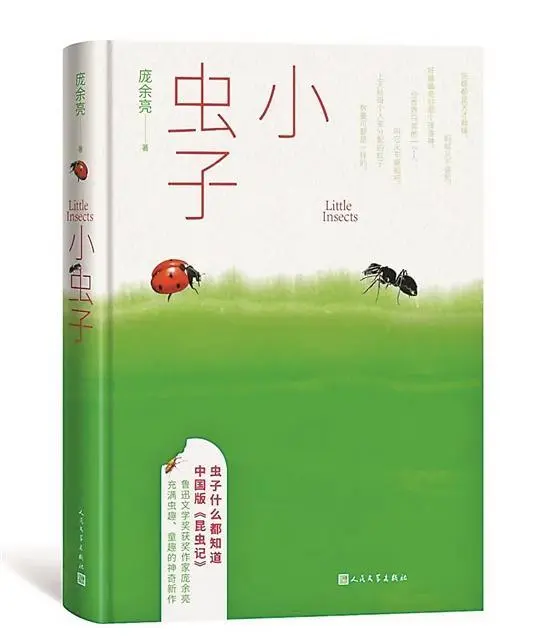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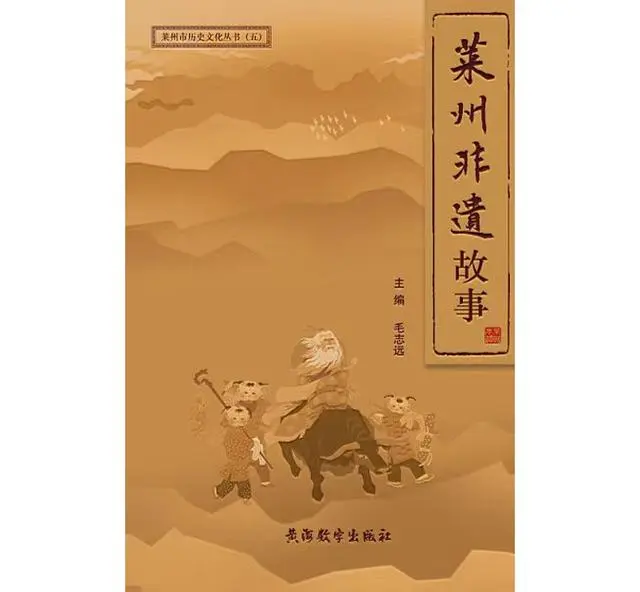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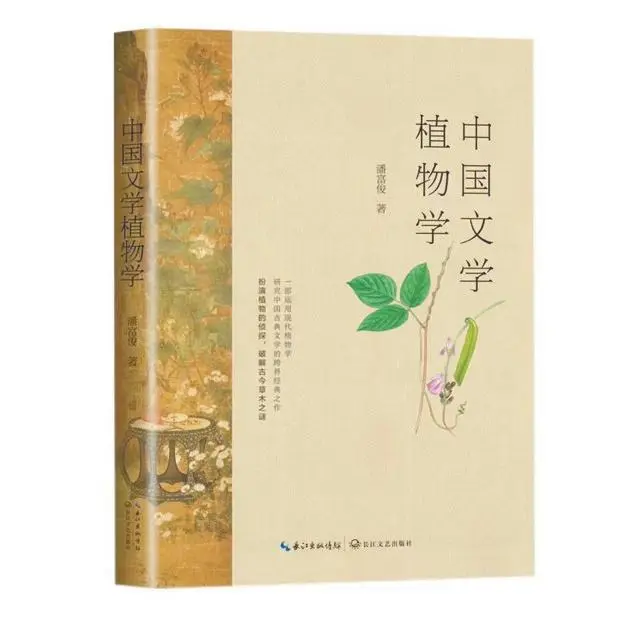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