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作家裴洪正首部短篇小说集《这个世界,别的夜晚》由五个故事组成,故事的主人公生活在小乡镇上,有校园霸凌中绝望的自杀少年,有亲手终结家族疯癫的母亲,有频繁遭遇家暴渴望逃亡的女人,有在土地变迁中彷徨迷茫的农民,有遭受非议与攻击的小镇画家。他们在生活的泥潭中奋力挣扎,谱出让人印象深刻的生存之歌。
裴洪正其短篇小说风格沉郁,笔锋凌厉又饱含悲悯。在论者看来,他的小说,通过“我”与主角的自救、互救,将人性置于光与影的交界处加以审问,进而在天真与世故、丑恶与善良、理想与现实留下审问的空白。
文/王江泽
近年来,伴随着双雪涛、班宇等东北作家的崛起,新东北文学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界的焦点所在——它以新潮的书写样态呈现了对东北城市的描绘,以多彩的艺术范式对过去三十年来的东北文艺景观进行了解构、重建。特定社会时代背景下平凡人的奋斗与自救,成为东北文学的叙事锚点。裴洪正小说集《这个世界,别的夜晚》接力泛东北化叙事,着眼于描绘生活日常中的平庸之恶,审问人性的弱点,他的作品是对于新东北文学的一次开拓,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苦难母题的一次突围。
作为“95后”作家,裴洪正出生于辽宁辽阳,曾经做过车间工人。早年的经历使得他的笔下充满了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与自救,质朴的文风饱含情感的泪水,读来尤为感人。与典型的新东北作家不同,裴洪正的文字略过了对宏大历史的刻画,而是借助独到的文学笔触,游走在过去与当下、青春与失败、虚构与真实之间。在个人史和社会史的交织中,裴洪正的笔触锁定那些平凡而又悲怆的现实,通过关注当下,关注习焉不察的日常,来绘制他所认知的苦难与人性。
小说集《这个世界,别的夜晚》由五个故事组成。《溺亡少年往事》聚焦农村校园暴力,《疯掉的塔达与失落的废墟》刻画不幸的家庭,《逃亡》关注家暴,《坐落无声》探索城市开发和农民失去的土地,《一个艺术家的故事》讲述画家秦怿坚持理想主义而遭遇的悲剧。除了《逃亡》,其余四个故事都巧妙地以“我”的角色将故事的叙述者和主要人物结合起来,通过我的叙述引导情节的发展,解剖人性的矛盾,揭示笼罩在平庸之恶里的黑暗现实。《溺亡少年往事》里,裴洪正采用一个“傻子”的视角,讲述了我与同学王芗伦深陷校园暴力漩涡,王芗伦最终承受不住打击投水自杀的悲剧,一句“傻子的话,谁会相信呢?”振聋发聩,揭开了现实中被霸凌者们所处的失语困境。除了“我”的视野,《逃亡》一篇诉说家暴的故事,裴洪正的笔调更加凝练,以第三人称速写的方式,刻画了在家暴阴影下女性渴求逃亡的生活悲剧。
自我的叙事无疑是有挑战性的,裴洪正恰恰利用“我”的视角将故事文本与思想表达,实现表里契合。“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一场场悲剧的见证者:《疯掉的塔达与失落的废墟》中“我”目睹疯癫的塔达兄弟消失在大雨中,他们因一场意外的悲剧家庭破碎,沦为他人的谈资而内心逐渐崩塌;《坐落无声》里人人都为化石博物馆的建立欢欣鼓舞,只有“我”感知到了丁伯心中那种田园故土被现代生活摧毁的哀恸;《一个艺术家的故事》里年少的“我”陪伴着画家秦怿,但他的理想却被村子里的人否定、诬陷、中伤,乃至最后被迫焚烧画作。“不一样”或者“不对劲”是这五个故事里主人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人群中的另类他者,他们或许先天不足,或许横遭飞祸,但是最终使得他们湮灭于黑暗的,是人性的冷漠推力,这些设计让小说内涵更为深广。
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强调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经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裴洪正故事里的人物正是被他人的平庸之恶所驱使着,在孤立无援之中丧失了希望,如断线风筝一般坠入黑暗之中。我以为,这也是《这个世界,别的夜晚》的超然之处,它打破了歌颂苦难的范式,通过诠释悲剧孕育的过程来诠释苦难本身,将对“平庸之恶”的理解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从而使文字爆发出了震撼灵魂的力量。
近年来文艺作品出现“向外转”的趋势,作家更加关心现实、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个写作者写下每一行字不仅追求小说技巧和语言,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忧虑和犹疑。裴洪正的小说,通过“我”与主角的自救、互救,将人性置于光与影的交界处加以审问,进而在天真与世故、丑恶与善良、理想与现实留下审问的空白。在裴洪正那里,小说创作不是在“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私密空间中打转,而是如哈里森所言,为了“共同培养的、或者说多方培养的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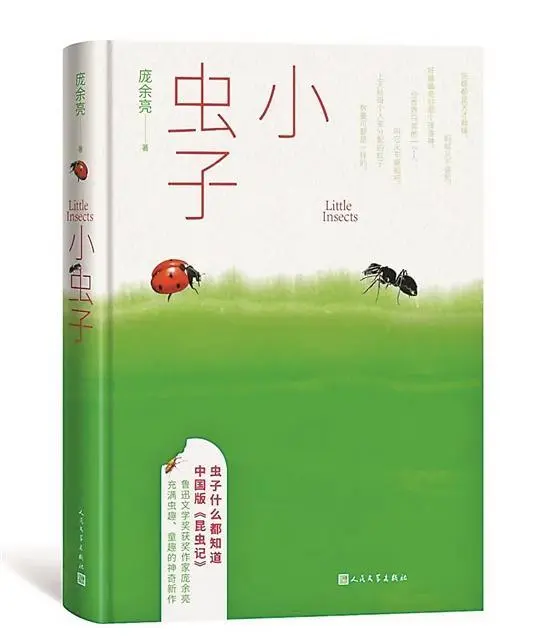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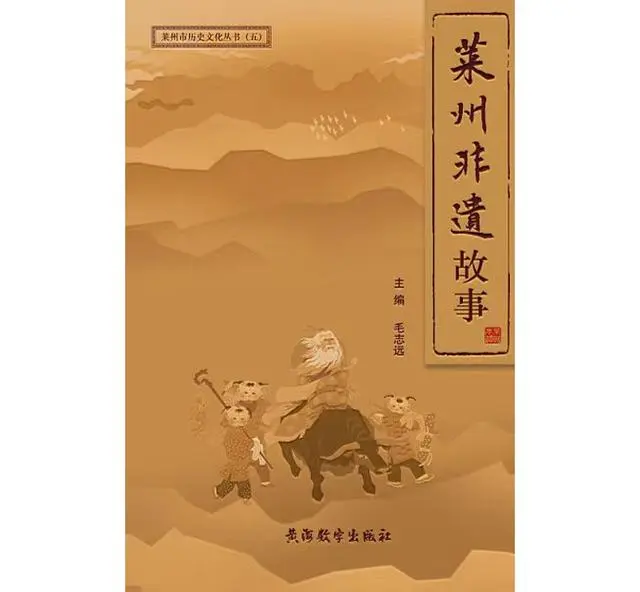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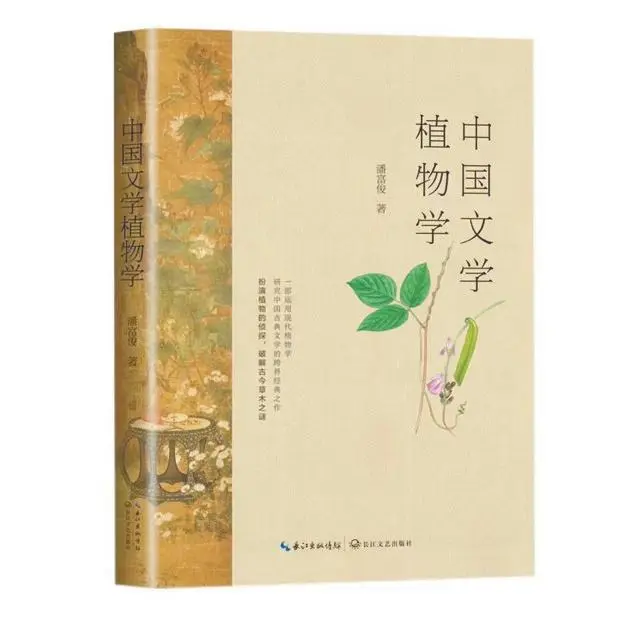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