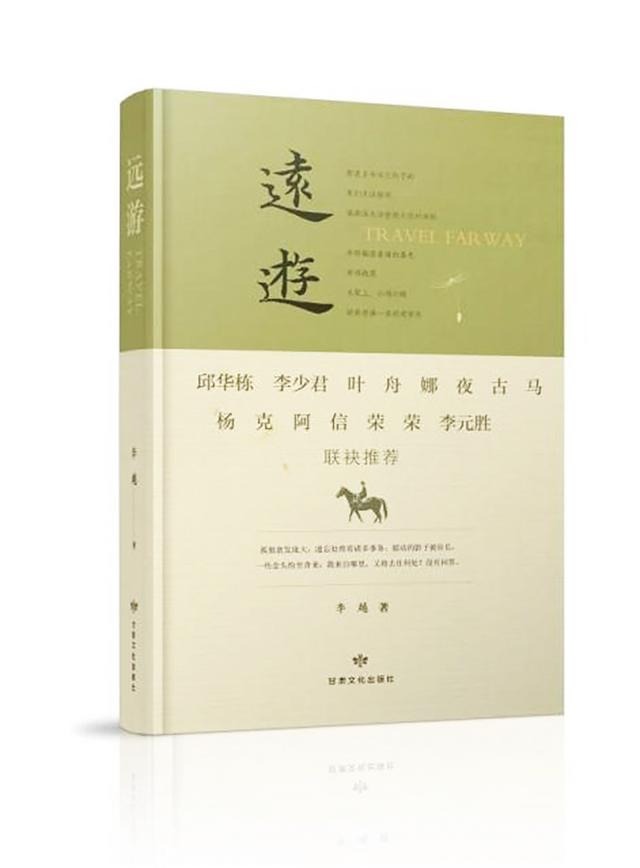
《远游》是青年诗人李越的最新长诗力作,共分六卷:往观、远游、天运、言归、击壤、回响。它像西域的细密画,诗人将身体的感觉做成了语言精巧的袍子,上面镶有中原的星辰卦象、西域的羊脂玉,内里铺陈古代的农令节气,又有现代都市的种种烟火与景观。
“往观”卷选《离骚》中“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之句,主题是缅怀童年,往观有回溯的意味。诗人从中年反观童年:身形开始变化,在时间中矮小下来,喉结消失,随着时光机奔跑,退回到往日记忆。童年的散光碎片开始充满活力,勾手格斗、抟泥巴、看守瓜田、玻璃弹珠、游泳、翻麦、放风筝、骑车……诗人努力剥离成年人的意识,像钻进一个时间之圆,随着螺旋而推进纵深。不仅如此,诗人还从童年洞观成长与生死。他写道“青春发育如激变物种入侵”“身体整夜燃烧,火舌翻卷”,表现出成长中的孤独与恐慌。
“远游”卷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为引,诗人沿着时间寻找河流的第三条岸。这一卷很突出的一点是关于声音的记忆,写了跫音、节拍、磁带、白噪音、喧嚣声、飘忽不定的车声、轻声吁叹的仙气、声控的尾音等。诗人进而由声音入梦,进入另一个明亮的梦。这是关于求学阶段的梦幻,写到了宿舍、食堂、自习室、图书馆、课堂等校园生活。所有这些都写得颇具梦幻色彩,透露出这段经历的恍惚,但其中一些印象却如此深刻逼真,比如“吊扇发出滞涩之音”“教授声如洪钟”“寂寞的街被惊醒”等等。
“天运”卷以陶渊明的《责子》中的句子为引,“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这一卷中,诗人写梦,“我被困在时间中,疲软/肢体融化,成为无定形。”诗人以梦为中介,将古代空间和现代形象交叠并置。这样的写法,既可呈“大”又可显“小”,既有具体的感知形式,又有形而上的维度。诗人一面仰望星空,一面观察人间的喧嚣。向下书写的过程中,诗人歌颂人的劳动,“造物使劳动者发光,也使城市发光”。从第七节开始,诗人开始对人的社会性的思考,思考词语如何应对现代文明的存在。
“言归”卷颇为有趣,诗人用死后视角来反观世界,引《礼记·祭义》中的句子“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来凝固诗眼。他从死亡来追溯活着,但也明确表达死后的状态是混沌的光或量子扰动。诗人穿林打叶回到故乡,看到自己父母因为丧子而悲痛不已,并表达了容易被遮蔽的记忆和人的社会性的脆弱。诗人笔下,死亡并非灵魂超脱,而是灵魂还乡,回到精神之乡。第八节和第九节使死亡这一命题不再悲伤,而是拥有了哲学式的悲悯高度。死亡,就像是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漫游太空》,人类面向宇宙无尽的终极出发。
“击壤”卷取唐代柳宗元《首春逢耕者》中的诗句“眷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壤”乃土壤,“击壤”是刨地、锄田、耕种的动作。本诗中,诗人着力写耕种劳作、歌赞劳动者。农业时令,镰刀刈麦,四季轮回。诗人迈着沉重步伐,写拖拉机拉犁,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的劳动景象。诗人详尽描述了拖拉机的拉犁耕种、机械化作业的过程:“将生铁的耙齿深深插入/吮食硅元素的腥膻。”第四节中,诗人写老人耕种,视土地为生命,即便力气消尽但依然保持热血。“血肉的纤夫”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个比喻既苦又蛮,彰显着博大的生命力量。第六节中,劳动者咬紧牙关,以隐忍来蓄积更大的力。第七节中,劳作的风暴,在诗人笔下展开。既有劳动号子嘹亮的部分,又有细密画的精致细节。
“回响”卷,取陶潜《饮酒》中的诗句“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回响”实为余响,诗人继续以梦为马,用词语搭建起感觉的迷宫。这回,诗人写的是对一具衰老身体的拯救,身体上被替换的零件。后现代的全息影像,深夜的游荡与苦行,皆在身体的修行场展开。他写的是后自然时代的图景,一种依据当下所显现的某种苗头而描绘的未来可能图景。很显然,诗人将这种科幻图景纳入了诗歌的写作当中,去冲击诗歌写作题材的广度。
李越的故乡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这里地处河西走廊东部、祁连山北麓、阿拉善台地南缘。永昌县东邻武威、西迎山丹、北接金川,似乎是西域开始的地方。不知不觉中,《远游》从故乡就变成了一条黄河,那里冰川无序降临,记忆无数次升起,诗人用高超的词语嫁术,建设起自我认同的“精神之家”。我想,“远游”是郊游,也像美国的公路片一样是旅行,是云游,是重新发现自我的地方。兜兜转转,诗人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出生的起点死亡的终点,在此过程中,诗人完成了时间之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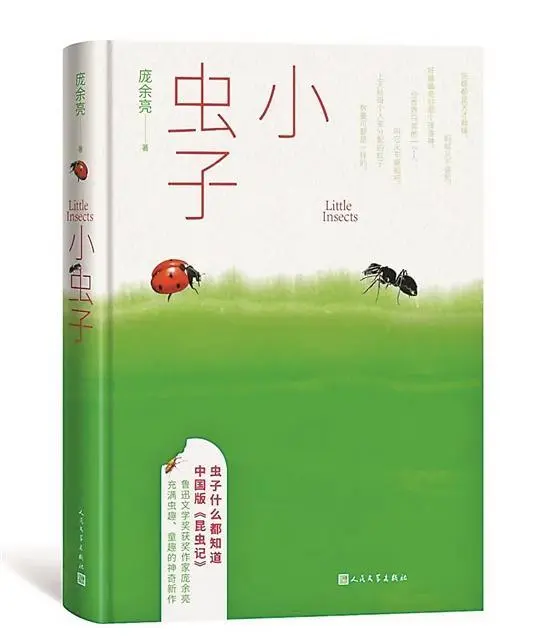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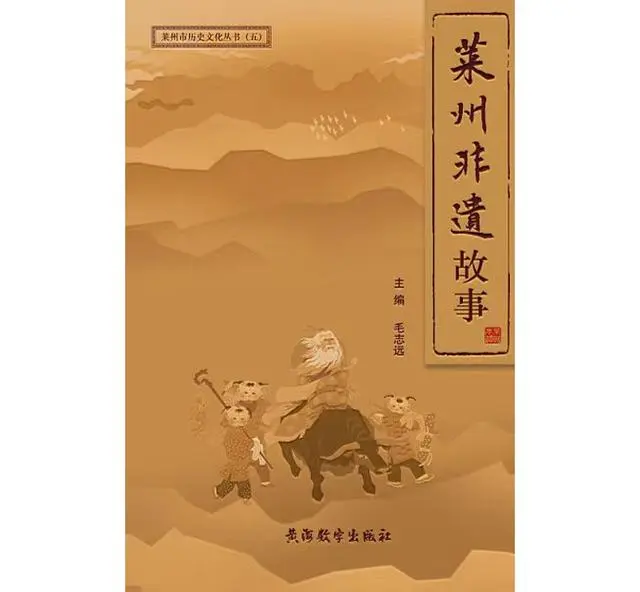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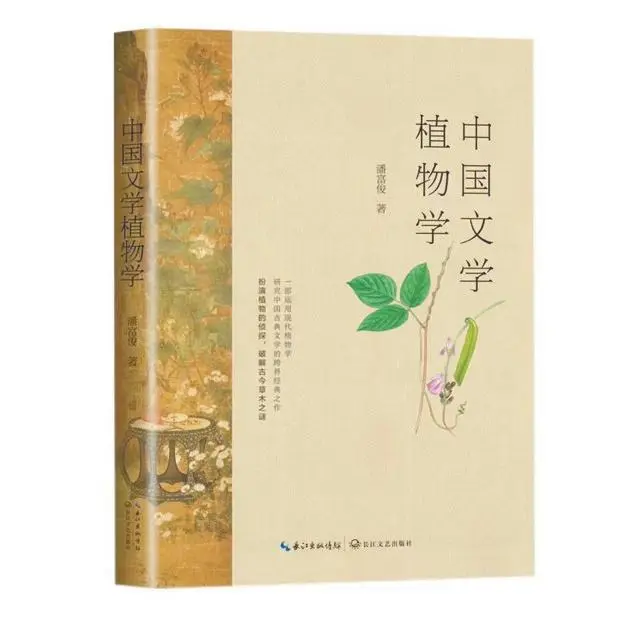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