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张翎,计划探访多位已故世界著名女作家的故乡或墓地,她将这份旅行计划形容为“带着点行为艺术式的行走”。同为女性写作者,张翎这份独特的探访愿望清单,本身就带有一种令人激动的成分,这种成分可以解释为向文学与爱情的古典主义的一次致敬,也可以理解为拨开纷乱的女性话语迷雾去寻找女性精神的一个萌发点或至高地。
现在张翎在她的探访名单中,已经给三个人名打了对勾,她们分别是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乔治·桑。为了到她们曾经生活过的现场,在一个个凝固或者流动的空间里,与她们实现一种类似面对面的气息交流。张翎分别去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艾默斯特、法国的诺昂。给她们带去的礼物,除了放置于墓碑上的一朵花或者一片叶子之外,还有属于张翎自己内心对她们的一种独特的认知与定义。
比如,张翎并不愿意在文学随笔集《三种爱》里,将勃朗宁夫人称之为“勃朗宁夫人”,每当张翎拥有了一个比较私人一些的探访空间或者思考空间时,勃朗宁夫人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婚前的名字伊丽莎白。于是,在《三种爱》里,读者了解了勃朗宁夫人,同时更深刻地认识这位名字叫伊丽莎白的作家:一位总是病容满面、不时咳嗽的矮小女子;一个迷恋写诗与通信的伟大文学家;一个违抗父权一意孤行的私奔者。
狄金森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过署名的作品,去世之后第一卷诗集甫一问世便震惊世人。在张翎看来,1830年12月10日并非狄金森真正的出生日期,她诞生于珍藏着她所有诗作的木匣子被开启的那一刻,“生前寂寂无名,死后万人景仰”,写作者未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荣光,恐怕是一大悲伤之事。
以写作小说赚取稿费谋生的乔治·桑,生前却活得热闹。在巴黎,署名乔治·桑的小说一本一本地问世,大红大紫的她与一大票男人谈恋爱,享受着“声名狼藉的日子”,直到她遇见了肖邦,“她曾经答应我死在她的怀抱里的啊”,肖邦在为最后一口呼吸而挣扎的时候对友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像是一顶桂冠,让喜欢穿男装的乔治·桑,愈发拥有了一种19世纪女子身上罕见的气概,这种气概的形成与文学有关,但更多与个性、生命态度有关。
《三种爱》的书名,在字面上理解,大概是想要表达这三位著名文学女性的不同情爱观,但我读完之后除了发现她们在世俗生活中有着不一样呈现自己的方式之外,内里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的精神世界与生命内部,都秘密地熊熊燃烧着文学与情爱之火,一生都极少走出庄园也好,总是一袭素白衣服也好,苍白的面孔很少有情感的流露也好,给人以冷淡、拘谨、不可捉摸的印象也好,一旦进入文学或爱情的世界,她们都成了勇士,骑着烈马,挥舞着利剑,战无不胜,她们调度、驱使着文字,让读到她们通过私密渠道传递出来的纸页的“读者”,心甘情愿地被征服,成为“猎物”。
《三种爱》当中,作者对三位人物有着两种形式的描写,一是作为访问者,带着冷静与感叹进入三位作家曾活动过、但如今却已经没有温度的现场;另外一种是作为旁观者合理地利用想象进入她们炽热、浪漫的爱情进行时——每每阅读到这些,便会发现张翎作为小说家的优势,她用准确的语言复刻着那些已经被风化的往事,为读者带来活色生香、光辉重现的一幕。
读完《三种爱》之后,我会愈加赞同“文学是激情的产物”,文学所带来的生命力,让19世纪的女作家们拥有了与男作家进行抗衡的能量,在那个漫长的文学黄金时代,所有与女性价值与女性精神的定论,都已经在诸多文学作品中有了清晰的轮廓。女作家对自身清醒的认知以及对文学坚定的探索,至今仍然具备启蒙大众读者的作用,她们在作品里所流露出的对自由的渴望、对平等的追求,尤其是简单、纯粹同时又不失深刻与隽永的爱情态度,现在看来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质地。
张翎还会继续探访并书写蔓殊菲儿、乔治·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芙、简·奥斯汀……不出意外,她仍然会挖掘到那些被淹没在展馆、故居与墓地背后的激情故事。对于写作者而言,这些故事可以带来能量与鼓舞,让笔下的文字更富有文学汁液。而对于读者而言,平淡的生活多么需要一场心潮起伏的阅读来填充,这本刚刚出版的《三种爱》,不会令你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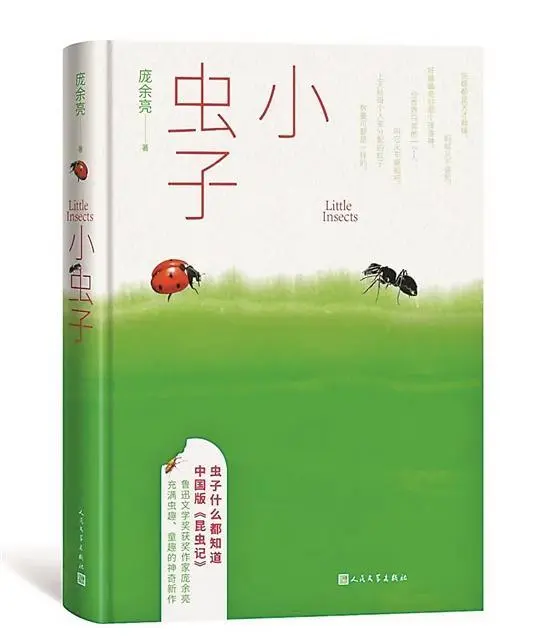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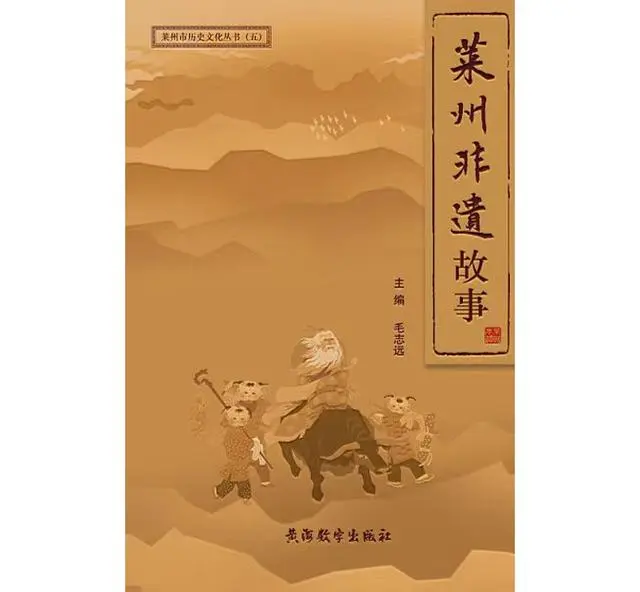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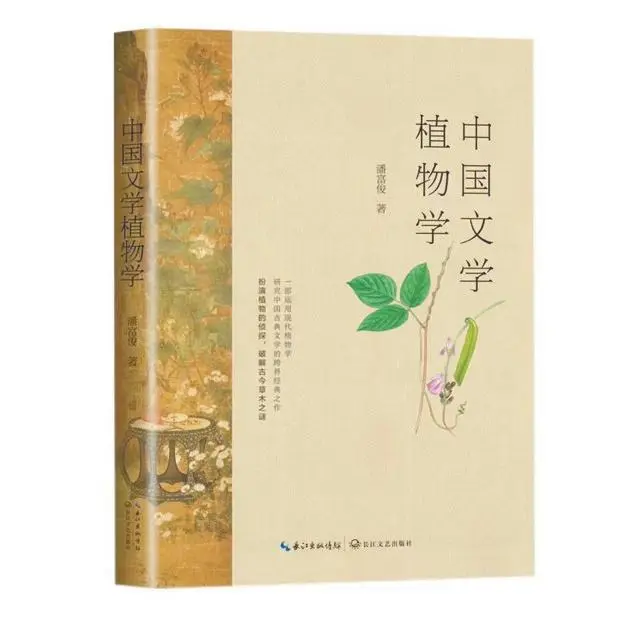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