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叶兆言、毕飞宇这几位当代重要作家的谈话录于近期新版。对谈中,作家们与他们信任的批评家畅聊自己的文学人生。其中,叶兆言和南京大学教授余斌的谈话录《午后的岁月》、毕飞宇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的《小说生活》,都是当初出版社定制的。王安忆和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的《谈话录》则是文学杂志约稿,后结集出版。
从这些即兴的聊天,我们可以看到,成长背景和人生际遇怎样影响着一个作家的个性与禀赋,他们的写作特色如何形成,风格怎样流变,他们眼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怎样一番景象,以及他们如何评价“同时代人”。
由于对谈的双方属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也是彼此信任的朋友,所以谈话中透露了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干货”。譬如叶兆言谈到早年工厂生活和编辑工作的不顺,还翻了和陈凯歌的旧账;作为“文二代”的王安忆,回忆了母亲茹志鹃对自己写作生涯的提携,还有对很多文学前辈的印象;毕飞宇则详聊了自己的阅读史,他那部著名的《小说课》,很多话题即发轫于他的这本谈话录。
值此新版之际,现代快报《读品》周刊连线余斌、张新颖和张莉,请他们就作家们的一些重要观点,谈谈看法。
读品:作家谈自己的经历、阅读、写作和文学观,通过对谈的形式来呈现,会有什么别样的效果?而且一方是现当代文学学者,一方是作家,属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这种对谈对彼此的工作——你们的研究和他们的写作,有何相互的促进和刺激?
余斌:涉及到文学的东西,叶兆言写过好多文章,最核心的、成型的观点肯定在文章里写过了。访谈这种形式比较随意、即兴,有很多不太可能组织到文章里面去的,这时候就出来了。两者是一个印证、互补吧。
张新颖:借助这个谈话,我对王安忆的了解会更多一些。对一般的读者来说,谈话录里面有很多王安忆在别的地方没谈过的东西,因为她不是一个喜欢谈自己的作家,她跟我谈得比较坦率,因为关系比较熟,所以很多东西可以说出来。在其他的场合,不一定会说得这么多,我觉得这是它的价值。但这个谈话对她本人的写作不会有什么促进,因为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作家。
张莉:毕老师自己说过,《小说课》的很多话题是从《小说生活》生发的。谈完了之后,他有很多东西想表达,就激发了《小说课》的写作。对谈意味着开放性,对谈者性别、年龄、趣味都有差异,才构成对话。比如我们讨论《水浒》时,我会直接说,作为女性,我不喜欢这小说中的某种趣味。当时是在南京的咖啡馆里谈的,旁边还有上海出版社的两个姑娘和速记。现场谈有很多想不到的、灵机一动的东西,他说话很幽默,气氛很好。
读品:总的来说,还是作家说得多,批评家说得比较少。
余斌:那是叶兆言的书,肯定我要就着他,另外呢,有录音机在旁边,我总觉得有障碍,他成名那么多年,接受过那么多采访,他比较放松,我不习惯。再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话方式,像我虽然不那么学究气,不那么书面化,但跟他比起来,还是没他那么随意,比较斟词酌句,有时候会蹦出来术语,可能会破坏他的谈话节奏。
张莉:对谈之前,毕飞宇写信说,希望对话是平等的,各占二分之一。但是,对谈当然是有主角的,读者最感兴趣的还是作家本人。所以,我内心有自己的设定,文字整理出来,大概他说三分之二,我说三分之一。当时对这本书的预期是,不口水、不枝蔓,要切实、要诚实。初衷应该是达到了。
读品:作家心中有一部属于个人的文学史,跟主流的文学史有重合,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叶兆言在8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论文里,就说杨朔风格过时了,把指导老师气得不行,因为老师是研究杨朔的;硕士论文写的是钱钟书,但答辩的时候,有老师还没看过《围城》,因为研究张爱玲、钱钟书,在那时属于“旁门左道”。钱钟书、张爱玲在我们主流的文学史里,现在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评价?你们怎么看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史的重写?
余斌:研究生都要有一个“开题”,我知道一些非主流作家,在有些学校开题都通不过的,当时意识形态的东西比较多,那时杨朔在散文写作上还是一个标杆、典范,叶兆言本科毕业写那么一篇文章,是比较离经叛道的,他把杨朔散文和“宫廷文学”联系起来,还是比较大胆的,在当时包括我们那个班上还是极少数。
现在主流的文学史,到底怎么去安放张爱玲、钱钟书这样的作家,我已经不太清楚了。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如果不是中小学作为指定的参考书目的话,已经没有读者了,钱钟书和张爱玲肯定比很多文学史上地位抬得比较高的人,读者要多得多。他们在文学史上应该已经有了一席之地,但具体抬到哪一流,我不是十分清楚,但基本上还是得到肯定的吧。“文学史”关键的问题是标准,根据不同的标准,写出来的文学史肯定差别是非常大的。我所见过的文学史,还是缺少鲜明的个人性。“重写文学史”这个呼声早就有了,但是一直是在大的框架下的修补,我看到的不同的文学史,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如果还是过去的文学史的框架,意味着那个标准还在,只是在一个比较宽容的位置接纳了他们,那就还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评价不可能太高,也不可能有充分的理解,就是“聊备一格”吧。
张新颖:钱钟书、张爱玲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史里面,当然已经有非常充分的肯定了,也是学生愿意研究、愿意阅读的,其实挺热的。
张莉:不管怎么重写文学史,真正好作品都会被人淘洗出来。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历经岁月依然鲜活。长远看来,好的文学史内在里是有一个稳定标准的。《诗经》《史记》《红楼梦》过了多少年都是瑰宝。
读品:作家们并不讳言,他们的文学滋养,普遍来自外国作家。比如叶兆言说“我想我的世界观,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给的”,王安忆推崇的是像雨果这样的欧洲古典主义作家,毕飞宇喜欢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彼此也有一些认识上的不同,叶兆言对中国20世纪文学,尤其小说,是不太瞧得上的,而王安忆认为,二三十年代作品中的语言和理想主义,在今天可能有了一种经典性。你们怎么看这种差异?怎么评价中国20世纪的文学?
余斌:叶兆言指的是1949年以前的文学,那些作家现在还站得住的,确实很少了。大多数作家只剩下史料的价值,也只有做研究的人去看,很多读者不会去看了。从新文学开始,文学已经另起炉灶了。“另起炉灶”的意思就是,不是在古代文学的延长线上了,就小说而言,新文学小说和古代小说完全是两个概念了。从鲁迅那一辈开始,他们的老师就都是外国作家,鲁迅自己明确讲过,他写短篇小说,主要仰仗的就是他读的百十来篇外国文学作品。一直到叶兆言他们这一茬的作家,你看他们的访谈,不是叶兆言一个人这么说,基本上谈自己的文学师承,都是马尔克斯、卡夫卡这样的作家。以外国作家来开启自己的写作,这几乎是普遍的。鲁迅他们的外国老师,可能是19世纪那一茬的;当代作家的导师,可能是20世纪及以后的。是这个差别。传统文学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只要你是中国人,它都会有的,但是在自觉层面上有意识去模仿的对象,毫无疑问是外国文学、外国作家。这不是叶兆言一个人的看法。包括对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也应该是普遍的。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普遍缺失文学性。
张新颖:作家有差异,这个很正常啊,每个作家都会有差异的,我觉得有这种差异才是好的。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他的文学资源不一样,这样才是好的,这样才会形成一个生态,就像一个树林子里面就应该是什么树都有的,不是一个单一品种。我不太同意说这个20世纪文学史里面提到的作家,只剩下了资料和研究的价值,不被人阅读,其实也有很多我们还在读,我们读鲁迅、读钱钟书、读沈从文、读穆旦,等等,很多。我不认为20世纪文学史是一个很虚空的东西,我觉得它的价值可能还需要我们继续去挖掘、去认识。
张莉:白话文学相对于古文的时间是短的,现在大家都在路上。20世纪文学的高峰当然是鲁迅,《小说生活》里,毕飞宇说鲁迅真正实现了“人剑合一”的作家,我非常同意。鲁迅是有硬骨头的作家,他的语言也非常有骨血,他是力量型、一击即中的作家。其实,20世纪文学里,有许多作家作品我们今天依然在读。
读品:一个优秀作家,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对文学趋势的评价是否更敏感,更有一种前瞻性?
余斌:作家的判断有时候更敏感、更准确,但也有可能不靠谱。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判断,他们更多的是“六经注我”。学者就不一样,“我注六经”的成分更多一点。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的体认,作家能够站到作者的立场,那种感觉更能摸得着,当然有一个前提,这个作家对了他的路;而学者更超脱一点,但他的优势和劣势都在这儿,因为超脱,有些地方可能进不去,对作品更幽微的地方,体认起来没有作家那么敏感,有时候就隔靴搔痒。
张莉:优秀作家和优秀批评都是敏感的。有时候一位作家对别的作家作品评价得一塌糊涂,可他的作品本身却具有预言性和前瞻性;有时候作家的创作谈写得很好、对文学趋势的理解说得天花乱坠,但他的作品会让人失望。情况不一样,作家的很多认识是体现在他作品中的。
读品:如何评价你们的对谈者?还有他们同时代的写作者?
余斌:他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水准,是在文学史上能够站得住的作家。后来的作家不太好下断言,后来阅读量下降了,也没有去跟踪。莫言和阿城,是我个人印象特别深的作家,阿城现在比较低调、沉默,但我是特别喜欢的,有他功力的当代作家很少很少。
张新颖:王安忆以及王安忆这一代的作家,写作的历史比较长,大概40年左右吧。他们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而且从他们开始,个人写作的历史变得非常长了,因为以前的作家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写作时间比较短。那么在这样长的历史里面,他们每个人也都会有变化,丰富性也逐渐呈现出来了。
张莉:“同时代人”有两个理解,一是身处于同时代,一是同年龄段的人。说到毕飞宇的“同时代人”,我更愿意谈李洱、艾伟、东西这几位,他们当时都是“新生代作家”,是先锋文学之后出现的一批作家。和先锋作家相比,他们的写作气质和追求是有差异的。我认为他们的文学审美至今依然称得上有新异,他们的文学贡献仍需我们慢慢去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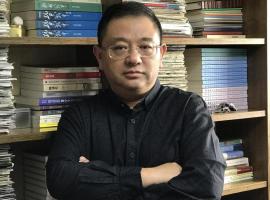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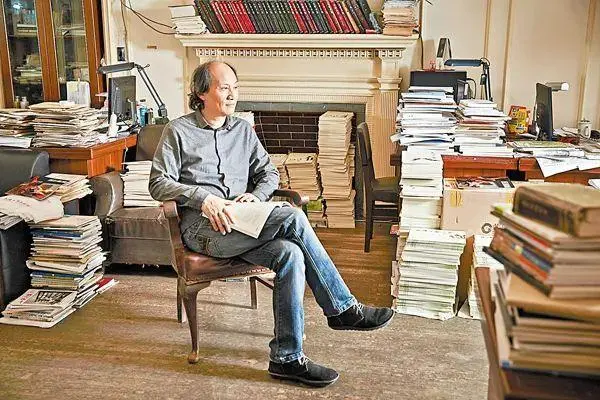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