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大一暑假,社会实践回来,我一个人留在学校读书。中文系的学生除了读书好像也没什么事可干。为什么读,我也一直没搞清楚,但8月的那个黄昏突然弄明白了。多年来一直想学法律,高考考砸了,进了中文系,像一脚踩空,整个人都茫然了。从来就没想过念不了法律系怎么办。所以整个大一我天天泡图书馆,没事就抱着本书,主要是为打发时间。但那天的打发时间一下有了意义。黄昏时分我看完一部名叫《家族》的长篇小说,觉得文学无比美好,一个作家竟然能够把我这样半毛钱关系没有的陌生人的想法知道得如此清楚,且表达得如此艺术和彻底,写作这个职业实在太好了。小说里的主人公跟我一样,多年来积郁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想法,我们有共同的困惑和疑难。如果不是知道那位作家现居哪里,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就潜伏在我周围。写的分明就是我嘛。那个黄昏红霞满天,即将落下的夕阳大得出奇,空旷的宿舍楼前长满齐腰高的荒草,我从宿舍里跑出来,满校园乱转,我想找个人说说话,我要告诉他,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文学的神奇足以拴上我一辈子
1997年8月的那个黄昏至今,一晃22年过去。就像在决定写作之前一门心思要学法律当律师一样,22年里我没再想过要做作家之外的任何一件事。当年我以巨大的激情发现了这个职业,该激情延续至今不曾有过丝毫减弱。我要做的就是把文学这件事干好。此后的求学、工作,也都是基于这个愿望展开。如果这算初心,那我可以不谦虚地说,我不存在“忘初心”之虞:文学的神奇足以拴上我一辈子。
我的主业是编辑,做文学的生产、管理和服务工作。有足够的创作经验和信誉,才能令人信服地从事文学生产、管理和服务工作;反之,在15年的编辑、管理和服务工作中,我又汲取了大量可以反哺自身创作的营养。习近平总书记说,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专业和业务完全可以融合相长,并非一定要非此即彼、顾此失彼。这个初心从不敢忘,从未忘,也从不会忘。
初心当是自发的,使命也要内在。使命者,出使的人要完成的任务;它是职业和身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你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可靠的使命理当是初心的延续,是为实现初心所必须付出的实践,无论多艰苦卓绝,都当甘之如饴,也都会积极、自觉、奋力地践行之。在文学的道路上前行,要说一点没感到苦,那肯定是睁眼说瞎话,但我的确在感到苦的同时发现了乐,而这个乐足以包容和覆盖掉苦,所以一觉醒来,睁开眼就深知这又是精神高昂、气力饱满的一天。那么就一个写作者而言,使命究竟是什么?
让你的艺术尽善尽美;你的写作能使你更好地与你的读者站在一起;你要在史的向度上自觉推进你所从事的这门艺术。
世上无所谓尽善尽美,但我们必须把完美之境作为理想目标来尽力逼近,让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恰如其分,让每一个字都闪耀着独一无二的真理光芒。一点都不夸张,信达雅,务求准确,准确到每一个标点符号。这是一个好作家该做的。使命首先表现在态度上。只有向绝好之境无限逼近的努力,才能让你的技艺不断提升,使优秀成为习惯。
在保证艺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与读者同在。在为谁写作这个问题上,一位著名作家说,“我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我的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我写了我个人的痛苦,写了我在社会生活中的遭遇,写出我一个人的感受,很可能具有普遍的意义,代表了很多人的感受”。写作者必须要与自己的读者最大限度地站在一起。
“这一代的”文学将会以何种面貌示人?
使命还在专业,即你能为矢志不渝地从事的这门艺术做一点什么。这使命同样不外在,也无法外在,只有深入其中,洞悉艺术自身的短板和局限才能寻到用力的方向。100多年前福楼拜就预言小说要死,100多年过去,小说还算体面地活着,只是有赖于无数作家在前辈们所走的路的尽头努力再往前走半步、一步,把小说的疆域往前推进一点、再推进一点,一寸寸地寻找新的可能性,才让它获得了广大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又到了路的尽头。
读者在远离文学。作为一个22年写龄、15年编龄、每年2000多万字阅读量的文学从业者,在一定程度上我跟读者一样感到了审美疲劳和厌倦。这种疲劳和厌倦既跟文体自身发展规律有关,长篇小说的确进入了发展的饱和期与平台期,也跟文体在新的时代没能及时有效注入新的元素有关,当然,还跟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缺少有效地重返我们现实和精神生活现场的能力有关。
面对一门艺术步入自身发展的瓶颈,写作者的使命何在?那就是意识到问题所在后,基于自身对艺术的理解与认知,做开疆拓土的尝试。意识到了,有那么一点理解和能力,那就勇敢地跳下水,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文学的演进从来如此。如果说,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那么,当这个世界发生巨变时,文学理应会做相应变化和调整。未必是亦步亦趋,但它得变。由此,才有所谓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由唐而宋而元而明清,文学一直进行相应调整,可见每一个节点,文学都在脱胎换骨,换个说法是:文学一直在开疆拓土。历朝历代的诗人、作家们没有懈怠,世易时移,他们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我想谁也不会否认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发生的变化,不仅在中国,整个世界同期都在经历以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为主导的巨变。面对如此巨变,“这一代的”文学将会以何种面貌示人?
当然,文学不是一咬牙一跺脚就立刻面目全非的,文学之变是渐变。渐变也是变,渐变也需要文学从业者们去奋力推进。当你面对既有的文学表达有所厌倦,当你觉得驾轻就熟的表达对这个变化了的现实力有不逮时,那就是你该反思、寻找和尝试的时候了。这是文学这一行当赋予它的从业者的使命。
正是在这种倦怠、不满足和警醒之下,10年来我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寻找一种与变化了的时代相匹配的表达方式。我希望我的作品,尤其长篇小说,能在形式与内容双方向上实现与故事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同构性。10年里主要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耶路撒冷》,花了6年时间;一部《北上》,花了4年。每一部小说耗费的时间都有一半用在寻找小说的结构上。《耶路撒冷》我用3年的时间找到了一种奇数章对称的结构,以此来表现全球化背景下,因为信息爆炸所带来的时间概念的变化,即因为信息传播足够快捷和传播路径足够多元,历时性的事件往往会呈现出共时性的特点。小说中还穿插很多非小说元素的偶数章,这些章节跟整个故事看似无关,实则相映成趣,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本张力。
找到《北上》的结构则用了2年。小说要处理从1900年至2014年100多年间的长达1797公里的京杭大运河,辽阔的时空跨度对我是个极大的挑战。我不想把它写成一个漫长的时空的流水账,笨拙懈怠地描摹这条伟大的河流是对它的敷衍。在寻找小说结构的时间里,断断续续我又把1797公里重走了一遍,读了六七十本专业书籍,我相信扎实的案头工作和田野调查会带给我惊喜。果然,我推敲出了一种时空交错勾连的结构,既像现代派的装置艺术,又像一种时空压缩折叠的技艺,未见得就一定科学和高明,但对这个题材而言它行之有效。我把这种张力巨大的新颖结构的获得,看作是对一个实证主义者的褒奖。
文学中充满了偶然,但对不懈的探求者来说,所有偶然都源于必然。这个必然就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深植于内心的“使命”,是他对所从事的事业及自身赋有的一份责任。如同哥白尼要去证明日心说、爱因斯坦要去发现相对论,对不对不重要,对错是时间的事,做不做是自己的事。重要的永远是做,是行动起来。是写作者面临文学的瓶颈与困局,像堂·吉诃德那样,舞起长矛,为理想中的文学开疆拓土。
我还是个文学编辑,就使命而言,扎根在写作者意识深处、为文学开疆拓土的责任感对我同样有效。推动文学进入“这一代”,不是哪一个作家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如同天下不是一人打出来的;也不是单凭一群作家完成的,作家也需要编辑、文学生产的管理和服务人员的提醒、引导、建议和助力。我愿意做那个一直呐喊加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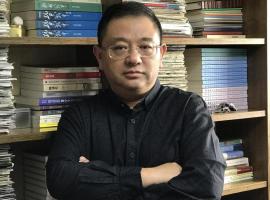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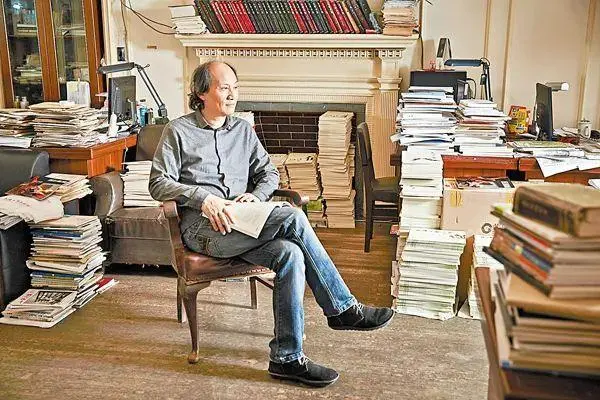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