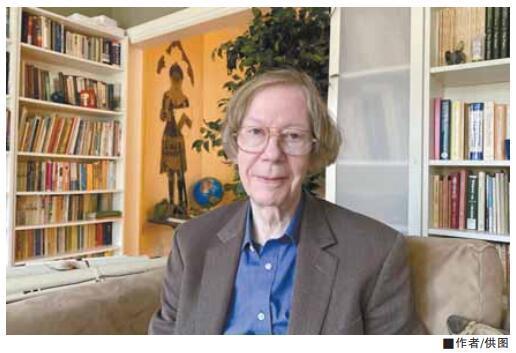
耿德华(Edward Mansfield Gunn),美国汉学家、康奈尔大学荣休教授,1974年在乔治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7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78—2012年任教于康奈尔大学文科与科学学院亚洲研究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教授,历任亚洲研究系主任、东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其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语言研究,代表性专著有《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1980)、《重写中文:二十世纪中文风格与创新》(Rewriting Chinese:Style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ose,1991)、《渲染地域:当代汉语媒介的方言用法》(Rendering the Regional:Local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2006)等。代表性论文主要有《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US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3)等,翻译著述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戏剧集》(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An Anthology,1983)、戴锦华的《救赎与消费:九十年代文化描述》(Redemption and Consumption:Depicting Culture in the 1990s,1996)等。
经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泉的引见,2018年夏天,我在北京西单首次访谈了与家人一同来华度假的康奈尔大学教授耿德华。他年逾古稀却精力充沛,外表儒雅温和、谈吐张弛有度,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风采。之后,笔者又多次通过远程交流的方式,向耿德华教授请教和提问。
作为开创现代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一位美国学者,耿德华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开始阅读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可说是一位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来深入理解中国的美国汉学家,而其心路历程与学术轨迹在同时代的海外汉学家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让人沉迷
张清芳:请问您为何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或者说触发您这个选择的契机是什么?
耿德华:我在20世纪70年代读本科的时候,读了大量的英文戏剧,也经常参加舞台表演。后来我大学毕业时,美国在越南打仗,几个月后我也去了越南当兵,在运汽油的卡车队当军官。我去当兵这件事情跟大学期间所学的语言、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见到越南老百姓受苦受难,见过许多血腥的事情,我很震惊,也很难忘,所以回美国后,就很难再把戏剧表演的事情继续下去。
此前我已知道中国文化是东方国家的一种中心文化,所以我在乔治敦大学英文系读研究生的同时就开始上中文课。我差不多是在1973年开始学习中文并阅读中国文学的。不过一开始我并没有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我的兴趣在敦煌文学。我还兴致勃勃地把法国学者收集的一些敦煌文本翻译成英文。但后来我发现,当时的北美已经找不出一个专家可以专门教我敦煌文学,所以有一位教授就建议我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让我作出这个选择的原因除了教授的建议,还因为那时候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术资料很有意思,非常吸引我。我一开始读的是张爱玲和钱锺书的作品,因为他们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最为推崇的两位作家。我的导师对我说:“你为什么只读这两位作家的书呢?你的硕士论文应该关注整个‘沦陷区文学’。”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就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从那之后我就投身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沉迷于此直到现在。
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我还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与一些研究性论文,像为《牛津学术参考》(Oxford Bibliographies Online)编写了中国现代戏剧戏曲类参考书目,还翻译了李小江的大作《后乌托邦批评:〈狼图腾〉深度诠释》(博睿(Brill)出版社,2018)等。
张清芳:您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或者说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耿德华: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是一个整体。独特的特征总在个体作品里出现,比如个体作品如何表现读者或观众已经很熟悉或很陌生的方面。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外国读者很少能欣赏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但是很明显,中国当代文学中却有很多外国读者欣赏的作品。我那时候看张爱玲、钱锺书、师陀、杨绛的书,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后来看其他作家的小说也一样。比如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莫言的小说,90年代我开设了一门研究生的课,让学生看14本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其中一本就是莫言的《十三步》。我觉得《十三步》是一部非常好的长篇小说。
张清芳:您为什么喜欢《十三步》?这部作品并不像《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那么有名,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吸引您?
耿德华:我觉得一个作家写小说可以写得“过分”一点,因为它需要给人以想象的启发,给人以感悟,给读者创造一个世界。《檀香刑》的想象力显然不如《十三步》,所以后者更能触动我。
在美国开创现代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
张清芳:您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时,为什么选择中国沦陷区文学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
耿德华:我是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位学生。最初我想研究清末民初文学,因为我在写硕士论文时发现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文人对清末文学非常关注,这给我一种启发。可是我的导师指出,继续研究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学最有前途。结合我自己的学术背景,导师的建议有远见又实际,我就照办了。我在2012年写的一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Us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况有过描述:导师极力鼓励耿德华完成和出版关于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北京两地的文学研究。该研究的起点是作家作品研究,像周作人,还包括导师自己推崇介绍的张天翼、钱锺书、师陀和其他人的短篇小说。还有,你此前已经发表的那篇学术论文《对海外中国现代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再反思——以耿德华的专著〈被冷落的缪斯〉为考察中心》(《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2期)中也指出:《被冷落的缪斯》的出版还弥补了我导师情感上的遗憾。后者在1978年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中曾提出一个写作计划:“抗战期间大后方出版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期刊,我当年能在哥大看到的,比起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来,实在少得可怜。……我计划另写一部《抗战期间的小说史》,把吴组缃、萧军、萧红、路翎,以及其他值得重视的小说家,予以专章讨论。”不过他直到2014年去世也没有完成该计划。《被冷落的缪斯》的出现可以说恰逢其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研究空白。这个评价或曰推测,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张清芳:那么您当时是如何查找相关研究资料的?
耿德华:其实那些基本的参考书我早就开始查找了。不过当时最大的限制是无法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做研究。我到美国的几个图书馆去查资料,那里有很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沦陷区期刊原件可供我阅读。不过美国图书馆中的相关资料并不完整,因此我后来又去了法国与日本的图书馆。最后还去了中国香港,因为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大学图书馆与书店有大量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书籍。正是在阅读和参考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我写出了这部博士毕业论文,算是正式踏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路。
张清芳:您在《被冷落的缪斯》前言中感谢了一些对您研究有过帮助的人,其中就有张爱玲,这很难得。据说她几乎不与外界接触,能否谈谈你们之间来往或沟通的过程,她对您的研究具体提供了哪些帮助?
耿德华:得以与张爱玲通信,是因为她认识我的导师。我们通信的过程很简短。我问了几个有关上海沦陷时期文化生活的问题,譬如谁是小山东,读者或观众在上海沦陷以后改变了没有,等等。她回答问题很客气很简短。后来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找出她在20世纪40年代期刊里发表但后来散逸的作品,她在《惘然记》里说,我把这些作品“影印了送给别的嗜痂者”。其实,我也影印了送给她,让张爱玲也参加我们“嗜痂者”的圈子。
张清芳:您的博士毕业论文于1980年出版,当时在海内外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唐弢在1982年发表的《复信》一文中曾指出:“美国有位Edward M. Gunn,写了一部书叫《不受欢迎的缪斯》(Unwelcome Muse),专谈中国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注意不够、而本身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采集许多材料,论点也颇有独到之处,作为一个美国人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但仍然有偏颇和不够允当的地方。”中国学者张泉把您的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书名为《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新星出版社,2006)。他在“译者序”中指出:“《缪斯》的研究视角主要不是文学的社会作用,也不是作家的道义困境,而是文学批评。”而您在该书的“前言”中也指出:“本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概括介绍战争时期上海和北京的文学发展史,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到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上来。”那么您为何会以评论“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为批评标准?
耿德华:探讨作品的文学价值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首先,我是受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说的“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观念的深刻影响,并深以为然。我们作为怀抱“文学作品至上”的批评家,都对抗日战争期间处于上海、北京沦陷区的作家们报以“普遍的同情”态度。其次,当时我之所以不从政治上来定位那些作家作品,并非因为我没有政治立场或是忽略那些沦陷区作家的政治倾向。我更愿意从作品内容和情感倾向上来探究北京、上海两地沦陷区作家的复杂心态。如你在论文中所说,“沦陷区作品其实包含了诸多抗日文化的反抗因素,显然是沦陷区作家主观意愿所致,这亦是作者不否定沦陷区文学和其文学成就的一个基本前提”。以批评家的眼光作出评价,目的在于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有价值的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
“反浪漫主义文学”概念的解读与反思
张清芳:如前所述,张爱玲与钱锺书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最推崇的作家。相较于其学术观点,您总结出来的反浪漫主义文学特征颇具个人学术创见,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您认为张爱玲、钱锺书和杨绛的作品是反浪漫主义的?
耿德华:我在《被冷落的缪斯》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反浪漫主义文学”的观点,可以说深受李欧梵的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的影响。这本书是李欧梵的博士毕业论文,发表于1973年,在我写博士论文时成为我经常翻阅的一本参考书。
具体来说,“反浪漫主义”这个概念是从李欧梵书中的“浪漫主义”概念发展并衍生出来的。李欧梵的“浪漫主义”主要指“普罗米修斯式的”代表者和其爆发出的追求社会理想的强大“物力”及消极而多愁善感的“少年维特”类的人物或英雄,这在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七位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然而尽管浪漫主义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新文学中得到酣畅淋漓地体现,但是当历史进入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沦陷区文学阶段,就开始形成与之前不同的文坛“新秩序”,浪漫主义就开始没落并从中发展出“反浪漫主义”概念且逐渐被后者取代。
我在阅读吴兴华的实验性诗歌《听梅花调宝玉探病》、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和短篇小说集《传奇》、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和杨绛的四幕话剧《风絮》等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时,明显感觉到它们体现出的是一种对“浪漫主义”的颠覆或曰完全相反,我在《被冷落的缪斯》中明确指出这种“反浪漫主义”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为:“在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任何理想化的概念,也没有英雄人物、革命或爱情。取而代之的是幻想的破灭,是骗局的揭穿,是与现实的妥协。高潮让位于低潮。唯情让位于克制、嘲讽和怀疑。机智代替了标语口号。不像他们之前那些完全站在浪漫主义范围之外的作家,他们断言,不存在任何社会目标,也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例如,张爱玲的“反浪漫主义”主要体现在“主人公们的冷酷无情的和不道德的欲望是现实世界的冷酷无情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与之相对立的”。而对于此时的杨绛和其话剧作品来说,“正如杨绛早期的戏剧,其中可能是浪漫主义化了的主题反而变成了怀疑早期传统的浪漫主义幻想的主题,并且把社会的理想与人类的心理现象分离开了”。钱锺书的小说世界也是非理想化的。至于中国沦陷区作家的“反浪漫主义”的独特之处与特征,我也在该书中进行了总结:“把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反浪漫主义作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作家相比,可以看出,前者不存幻想而并非幻想破灭,这一点能把前者与后者区别开来。”还有在你的文章中,也曾指出张爱玲、杨绛、钱锺书等作家用小说或者戏剧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反浪漫主义主张:“这些作家作品拥有的怀疑个人主义的气质、非理想化对待生活的方式、理智务实的婚姻爱欲观,以及对浪漫理想的批判和嘲讽,等等,才是构成反浪漫主义的基本因素。”
不过今天我再重新思考“反浪漫主义”这个概念,觉得自己当年对它的分析太浅、太流于表面了,缺乏更系统性的理论化与深度解读,也没有对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进行明确的定义,这是一个遗憾。这个遗憾除了我自身造诣不够深厚之外,另一个原因则在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西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研究状况限制了我进一步的思考。
张清芳:在您的书里,杨绛和她的戏剧占了较大的篇幅,连李欧梵都说,“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杨绛,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对您这样一个美国学者能把杨绛“找出来”感到很吃惊。您是如何发现杨绛的?为何对她评价如此之高?
耿德华:像很多别的作家和作品一样,杨绛是我从抗战期间居住在北平的法国牧师编的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戏剧参考书里发现的。杨绛说他们在抗战期间很穷,她写剧本是为了赚钱养家,作品很粗糙。就算如此,她的剧本间接地讽刺传统与反传统两种立场的习俗与教条,剧本的人物性格总在某些方面跳脱这两种框架。可以说这种人物没有被理想化,也可以说判断她/他们的文化框架也没有理想化。而且,她的风格并不刻薄。
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及趋势
张清芳:请您谈谈以美国为主的北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耿德华:我的论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把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当下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状况大致梳理了一遍,对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都进行了简要介绍和分析。该论文的内容主要包括9个方面或研究向度,分别是:早期研究方法和主题,文学和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研究,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中国当代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的思想与美学,对现代的定义,电影、视觉研究和媒介研究,方兴未艾的方向。在最后的一个研究向度“方兴未艾的方向”中,我提出:“近年文学研究者继续形成新的主题,如加入阵营的海外学者对互联网的研究。在文学与医学的研究领域中,近期同样已出现诸多专著,而文学主题、环境主题也正在唐丽园的《生态含混:生态危机和东亚文学》(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2)这类研究专著中出现。”这也代表着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近年的基本发展趋势。感谢你抽时间把我的论文翻译成中文,期待能早日看到它发表出来。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出现包括电影、视觉研究与媒介研究等在内的跨学科、跨专业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或产生或接受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我只具体讲一下我在康奈尔大学时的正面经验。每个学生都需要选择几位教授,请他们参加自己的“论文委员会”。那些教授中一定有一个或两个来自另外一个系,比如说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欧美文学、电影、戏剧等。那些教授很多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因此始终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影响学者和学生的研究与经验。美国实际上一直鼓励跨学科研究。
我记得很清楚,我在1980年作为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助理教授,教一门“中国文化纲要”的课,当时邀请几个其他系的教授作客座讲座,有一位教授是研究亚洲“大米经济”的农业经济专家。我以前看过几本有关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并了解小说中所描写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可是,当我听完那个农业经济专家解释农业社会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的办法,我才忽然醒悟了为什么那个时代那么注重农村题材的小说。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很笨,为什么没有早些明白这些。总之,在1980年竟然是一个农业经济专家帮我深入了解了中国现当代文学。
从文学研究转向汉语语言学研究
张清芳:自出版《被冷落的缪斯》一书之后,您又在美国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与散文并出版文集,近年还从文学研究转向语言学研究,请问触发您这种研究“转向”的原因是什么?还有,顾彬在《二十世纪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的前言部分说曾受到您的一些语言观的影响,您怎么看?
耿德华:我认识顾彬但不能说很熟。我不太明白他所说的“语言观”是什么意思,我写了两本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书,一本是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写中文》,我用的方法他可能喜欢。
早在20世纪80年代,康奈尔大学汉语历史语言学家梅祖麟教授邀请我参加现代汉语的语法转变问题研究。根据语言学的看法,任何语言的词汇在历史上都以比较快的速度有所改变,可是文法却转变得很慢。文法之所以改变的原因,研究者只好假定,譬如是不是社会文化有所改变,或者是不是一种语言的深层结构里,文法因素之间有规则性的摩擦,像一座火山里边引起爆发,引起文法的突变。梅教授知道我不是一个语言学家,更不是一个历史语言学家,可是20世纪60年代当我读本科时,因为生成语法等理论和早期计算机研究方法的出现,语言学和文学风格学很有前景,语言学家和修辞学家已经开始把文学当作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上过这类课,后来读研究生也上,包括汉语语言学课。所以我接受梅教授的建议。不过,虽然我加入梅教授的研究项目,可能对他关注的历史语言学问题有所帮助,但是我研究的目的是文学风格学。研究文法和语法,我觉得是现代语文风格转变的一种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另外也应该注意修辞与句子跟句子之间衔接方式的创新。而且,我的研究范围限于书面语。这项研究后来就成为《重写中文》一书的主要内容,关注语文标准化、规范化的过程。
梅祖麟教授还曾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语文在文法上有深刻的改变?”所以,我研究文学不能只看语言的问题,我要注意怎么能够用语言学、修辞学和另外一种研究方法——Sentence Condition(句子环境)。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在20世纪80年代与我同时关注Sentence Condition的研究方法。Sentence Condition就是指句子用什么方法来联系,句子里面有什么内容,一段中的几个句子怎么互相联系。我举一个例子:我读巴金小说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段是讲一个女人快要淹死了,一个男孩子划船去救她,他挥挥手,她大声地尖叫,他回答,他她他……在19世纪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句子,一定会用另外的文字来说明是谁在说话,谁在挥手,可是巴金可以做到,而且我们一看文字就知道写的是谁。
此外,研究语文规范化的过程中,不能不注意汉语方言风格的问题。而且,我正在进行研究时,中国大陆、港台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各种领域同时在扩大,其中有大量的作品是方言风格。因此,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研究中国当代媒介的方言用法。在研究媒介的方言用法时,我找了很多人帮忙,因为我只会说几句广东话,但那根本不足以去研究中国香港的方言,所以我聘请了学生当助手,也去采访别人。我一直都依赖中国人,有华裔和中国国内的人帮助我。为了进行这种研究,我会采取某些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和理论,譬如研究说某一种方言在整个社会的所有方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每个地方拥有的不同方言的相对层级。可是严格来说,我的研究是风格学,是研究作家与媒介作品所“安排”的语言表现,试图分析每一种作品的独特方言用法,并不是社会“自然”语言的用法。因此,我的书名是《渲染地域:当代汉语媒介的方言用法》。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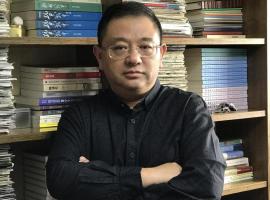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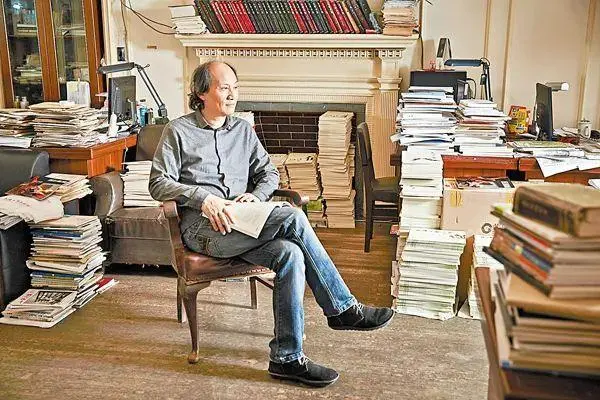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