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获得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
少年时代开始写作的石一枫,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稳健而顺利。他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具有相当优秀的理论素养。用著名评论家孟繁华的话说:“他引起文学界广泛注意,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几部中篇小说。这几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这个时代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
关注时代,关注现实,是石一枫的写作特色。他的作品写了小人物的无助与挣扎,内涵却富有历史感。他笔下的人物性格饱满,充满张力,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评论认为他的写作承继的是老舍和茅盾的文学传统,具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他说他供职的《当代》杂志就是一本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刊物,他在这里受到熏陶和启发,他的写作也因此更加贴近社会和人。
《瞭望》:你出生于1979年,属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茬人,作为一个作家,这个时代给你和你的作品带来了什么?
石一枫:人都是时代塑造的嘛,改革开放给个人带来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涵盖了迄今以来我所经历的一切社会变化。从日常层面来说,比如丰衣足食,这在平常看来就是生活的常态,但历史地想一想,其实还挺值得震惊的。我们这代人尤其是城市孩子,可能是中国几百年来不必为了填饱肚子而发愁的第一拨年轻人。在一个社会上升期度过青少年时代,还给人带来一个心理上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对生活抱有一种乐观的想法,觉得今天的不如意明天都能解决,觉得世界是前进的、蓬勃的,而我们的一大使命就是拥抱世界。这种心理搁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是心理暗示,搁在一小撮人身上叫集体无意识,搁在一代人身上就是客观现实了。
对写作的影响当然也有,文变染乎世情么。我承认比起以前的作家,我的东西包括我们这拨儿作家的东西普遍发“甜”,透着没经过事儿,哪怕哭天喊地的绝望往往也是装腔作势,但这其实没什么,毕竟“苦难令人深刻”这个命题也很可疑对吧?我想,只要能意识到那点儿“甜”是从哪儿来的、将来有没有可能继续“甜”下去也就够了。说到底还是眼界开阔点儿,心态开通点儿,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
《瞭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互联网等等带来观念和生活形态的多样化,你赶上了一个多元发展的社会,选择也是多样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为何要当一个作家?
石一枫:原来有句话叫“文学改变命运”,可能我也属于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反着改变的——我老开玩笑,如果干别的没准儿哥们儿早“发”了。还有个笑话,过去有个电影叫《中国最后一个太监》,讲的是一懵懂少年立志进宫,没想到刚一做完手术,听说皇上退位了。对比一下上世纪80年代所谓的文学黄金时期,我觉得我当了个作家的经历好像也差不多——搞了半天文学,文学没那么多人看了。不过想开了也没什么,社会进步的表现不恰恰就是多元么?要还是全国人民嗷嗷待哺地等着那一小撮作家启蒙,我都替作家臊得慌。说到底还是喜欢这事儿,能把业余爱好变成谋生的职业,这说来也算幸运。
《瞭望》:最早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是怎样的契机让你成为一个作家?
石一枫:刚开始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把发生在身边的学校生活写下来,一看还挺长。当时住的那个院儿里有个非常有名的作家,我们都看过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觉得他是大师,我父亲就把我写的小说拿给他看看。他看完之后觉得还行,推荐给了《北京文学》杂志,没想到就发表了。记得还是手写稿,我的字儿特烂,我妈怕拿出去让人笑话,就给我抄了一遍。后来科技进步,这个障碍也被电脑扫除了。还记得那时《北京文学》的编辑部在和平门的地下室,我去那里聆听过教诲。当时就觉得写东西好像也不难,人家能写我也能。当然这肯定是因为那时候其实还不会写东西,真上了道儿才知道难在哪儿。
《瞭望》:你高中时就能在《北京文学》这样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小说,无疑算是很早慧的作家,一般来说像你那个年纪的城市青年即使写作,或许会写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等,你却走了一条可以说更艰难更有使命感的纯文学道路,是什么决定了你这样的文学风格?
石一枫:可能还是个人趣味吧,小时候什么书都看,自己也能看出什么东西智慧含量高,什么东西水。也知道有的东西得仰着头看,有的东西得弯着腰看,看着看着真能把你气乐了。然后自己就想,以后要是也写东西,得尽可能地别让有见识的人笑话。当然也包括上大学和工作的经历影响。在学校里念的就是中文系,那个年代的那个环境还挺“言必称希腊”的,看个盗版电影都得挑各种有讲究的,从艺术到思想深刻的,更别提文学了,不啃两本卡夫卡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上班以后又编文学杂志,虽然也提醒自己别太矫情,不过经典的标杆在那儿摆着呢,就是80年代以降纯文学的那个路数。现在其实可以说,这基本就是一个被精英文化给塑造了的经历,当然,与我自己对文学的认识也相吻合。再一个方面,我觉得这样去写,写作的自由度也更大。
《瞭望》:你在《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特别能战斗》这些很有名气的小说中塑造了不少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你是如何“发现”这些人物的?
石一枫:应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观察生活吧。生活里总能遇到让你印象深刻的人,你把这些人写下来,想来也能让读者印象深刻。
至于说小说的写法,现在倒也没必要说哪种更新哪种更旧,归根结底没准都是前人尝试过的,我们往往只需要找到适合于自己的那个路子就可以得心应手地写自己所想表达的。有人愿意从结构入手,有人愿意设计情节,我的习惯是比较重视人物。当然这也不是说把人物临摹下来就完事儿了,还得琢磨人物的来龙去脉,想想每个人物和时代的关系以及对时代的意义,说到底还是得对生活有态度。
印象挺深的是《特别能战斗》这篇小说,原来就是那种特有精力、特有战斗意志的北京大妈让我觉得挺有趣的,但也没觉得这种人物多么适合写成小说,后来才发现,原来从这种大妈身上能看出新旧两种体制的错位,那么写下来似乎就有点儿意思了。
另外我们对人物的认识又是变化的,它本身就在向复杂的方向发展。比如老舍写《二马》,当时肯定觉得老马是落后人物,小马是先进代表了,可放到今天看,小马这种人其实挺乏味的,倒是老马能够在不经意间戳到时代的敏感点。我的小说《地球之眼》也是这样,里面有个坏人叫李牧光,写的时候主要让这人代表了资本之恶,但后来又想,这种人是不是也有着他的情怀乃至无奈呢?到有朋友找我商量改编影视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李牧光最好能写出点儿悲壮感来。
人物越琢磨越复杂,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复杂吧。
《瞭望》:随后你又写了《心灵外史》《借命而生》这样的小长篇,小说的内容似乎和你本人的生活拉开了距离,这个变化是如何形成的?
石一枫:此前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那些小说,确实和我的生活距离挺近的。比如里面老有一个游手好闲的文化混子,在好多人看来作家和文学杂志的编辑似乎也就那样儿。不过也是个自发的过程,一个作家老是写一个领域的事儿,自己可能先烦了。有句话说人一辈子真需要面对的也就是身边那几个人,确实,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面对同一拨人,这固然让我们觉得安全,但要是在写作中也这样,那写作的意思也就不大了。既然干了这事儿,那就总想写点儿新鲜的。当然要写那些原本自己不熟悉的人物和生活,或云拓宽题材,这又是个相对自觉的过程,该下的功夫还是得下。我们编辑部的老同志就总结过,中国作家有很多都是经历型的,写自己的经历得心应手,经历以外容易抓瞎。怎么和自己感兴趣但又不熟悉的人物建立通感,了解他们的想法和状态,再把他们尽可能看起来像地呈现出来,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坎儿。比较令人欣慰的是,我貌似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想法,这也让我有了再把写作进一步拓宽的信心。
《瞭望》:你的小说很注重对社会背景和时代变化的反映,这是很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你怎么看待现实主义这种经典写法在今天的生命力?
石一枫:还是一句老话,“艺术源于生活”吧。老有人强调现实主义和其他一些主义的区别,其实我倒觉得,哪儿有不关注现实的文学呢?只不过关注的方式不同而已。从这个角度讲,说“无边的现实主义”好像也有道理。中国的作家要对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发表看法,表达态度,这似乎也是分内之事。有人可能追求写出传世的作品,或者有所谓人类的普遍价值的作品,就像托尔斯泰和马尔克斯那样,不过我也老觉得,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肯定没考虑两百年后的人怎么看待这部小说,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的时候也不会琢磨他的书在国外会有多少个译本——如果他们这么想了,恐怕他们也不够真诚。总而言之在中国当作家,还是先把中国作家的本分做好吧。
当然还有个问题,就是也不只把现实写下来就算了。“有现实没主义”,这个状态好像也不能让写作的人对自己满意。在面对有时复杂琐碎,有时深沉不语的中国现实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具有一点总体性的、对生活乃至对世界的看法?这点儿看法又能不能引起别人的共鸣?这种能力也许才是让现实主义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地方吧。
《瞭望》:和同龄的一些作家不太一样,你好像不是特别强调写作的具体技术,而将精力更多放在了还原生活以及总结社会意义等方面,这跟你对文学的看法有关?
石一枫:我有一种看法,好木匠不会成天在一块儿讨论刨子的几种用法,好厨子也不会没完没了地研究怎么颠勺。写作技术当然也是必要的,不过如果在技术上用的心思太多,甚而变成了唯技术论,这会诱导我们忘记了写作之中更重要的东西。
也和很多艺术门类不同,文学写作好像是少有的那种“功夫在诗外”的行当,写作本身几乎不能称其为一门学问,更重要的还是对生活的发现。而对生活的发现、观念和总结又不是写作技术本身能带给你的,它可以和政治经济饮食男女等等一切方面有关,但就是跟写作技术无关。相比于焦虑自己是不是一个巧妇,我更希望自己不要去做无米之炊。
《瞭望》:你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的传统的,或者这么说,中国文学传统对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石一枫:除了语言方面的规范和影响以外,更多的还是看待生活的方式吧。这儿说到中国文学的传统,我觉得除了唐诗宋词古典小说之外,现当代文学本身也是一个传统,而且那个传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可能更直接。如何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去看待一个“现代的中国”?这个意识恰恰是现当代文学留给我们的,具体地说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代作家。我也不觉得我的写作就算跳出了五四新文化的那个传统,恰恰相反,那个传统正是我们在今天需要强调的。
《瞭望》:以前有一种说法,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当然现在不少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但成果还有待检验。作为一个北大中文系的硕士生,你觉得中文系的系统教育对写作有帮助吗?
石一枫:我倒觉得,既然写作的价值在于对生活本身的发现,那么那种教育背景是否有利于发现生活,这还真不好说。学院里那一套阅读、学习的方法当然有用,所谓街头智慧没准儿也有用。而我佩服的很多作家确实也都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至于中文系的教育,记得我刚入校的时候就听老师说,这儿不是培养作家的,这儿是培养学者的。跟一帮学者在一起几年,对我的好处首先就是对那些大词儿洋词儿免疫了,归根结底还是开了眼界吧。
《瞭望》:除了写作,你还翻译过外国小说,你怎么看待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石一枫:是翻译过一本《猜火车》,当时出版社拿到版权,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也行,但要翻译的话就用北京口语的调子来翻,我觉得那更符合原著的气质。对方答应了,权且就算做个试验,现在看来肯定算不上信达雅,不过后来搞外国文学的朋友也说挺独特的。
而一旦接触过具体的翻译过程,反而觉得对于外国文学本身也没必要太高估,而且人家那么写有人家的客观条件,跟咱们这边的情况大不一样。就拿《猜火车》来说,写的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像个社会问题小说,艺术上的独创也都以此为基础。脱离背景,单纯地把国外小说看成“写作圣经”,肯定是没必要的,干脆把所谓“翻译腔”看成“文学味”就更没必要了。
《瞭望》:看见你在文章中说你是先阅读了20世纪的文学,再读到19世纪的文学,这样的阅读经验是否让你对文学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石一枫:阅读的顺序及其影响,可能也跟年纪有关吧。比我年长的那辈作家刚开始看的是20世纪前的西方文学,他们看书的时候卡夫卡、福克纳还没大规模引进呢,都是先看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再一看《变形记》《喧哗与骚动》就被吓一跳。我正好相反,读国外文学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以后作家们似乎都读过卡夫卡、卡佛、卡尔维诺和村上春树等等。先读了现代的,再读古典的也能让人耳目一新。现在我还觉得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的很多写法特别必要,特别有道理,也可能跟当时的阅读经验有关,而哪种经验没准儿还真是顺序造成的。不过我觉得比我更年轻的作家也许就没有这种体会了,他们生活在更丰富的文化环境里,不会饥一顿饱一顿,也不会挑食,从而阅读口味也会更客观一些。
《瞭望》:文学编辑的身份对你的写作是否有所帮助?请谈谈对你写作影响比较大的人和事。
石一枫:肯定有。编辑嘛,就是看别人的东西,别人写得好的可以学习,别人没写好的地方无则加勉。我所在的《当代》编辑部还有个气氛特别好,一篇稿子往往好几个人都看,看完大家一起讨论,分析得失,只要是有心人时间长了还真能学会怎么写小说。
此外这个杂志也一直强调现实性,我对文学的很多看法,其实也是在学着编杂志的过程中养成的,然后又尝试着在写作的过程中实践一下。也挺有意思,编辑部上班的时候往往不太看稿子,稿子都揣回家看,大家凑一块儿就是交流心得。我从刚上班的时候就老听洪清波、周昌义他们几个老编辑聊天,到现在还经常跟洪清波老师一人一个沙发,一聊小半天,一会儿杨新岚和孔令燕她们也过来一块儿聊,上世纪80年代那些文学沙龙估计也就这气氛,起码编辑部的小环境是把上世纪80年代的气氛延续到了现在。而且看多了稿子的人眼光锐利,记得我写《借命而生》的时候,写到一个地方觉得该换个视角了,但一偷懒也就没那么做,后来洪清波老师看完跟我说,你这儿要是从另一个人物身上展开就好了。果然那小说现在看还是有点儿单薄,而我也只能在下一篇尽量处理得更合理一点儿。
《瞭望》:如果说文学是一种使命的话,你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使命的?
石一枫:说得多高也没必要,好像某项事业的意义一崇高,从事它的人也跟着形象伟岸了起来似的。不过起码的要求还是得有,否则也对不起这个行当里的其他人。既然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殊性,我们还是应该对时代的变化做一些必要的记录和思考,这些记录和思考在别的艺术领域里未见得能实现得像文学这样有效,而这也是文学的不可取代之处。
《瞭望》:你的写作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和肯定,你对自己未来写作的方向和目标有何规划?
石一枫:应该还是继续拓宽写作的领域和题材,争取每一部都跟上一部不一样。现在也在写长篇小说,用的是所谓传统的京味小说的调子,争取覆盖的人物与领域更广一些,不过能写得怎么样也不好说,尽自己之力去做。(记者 程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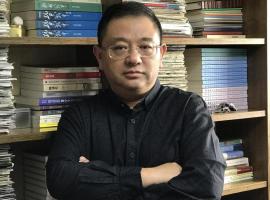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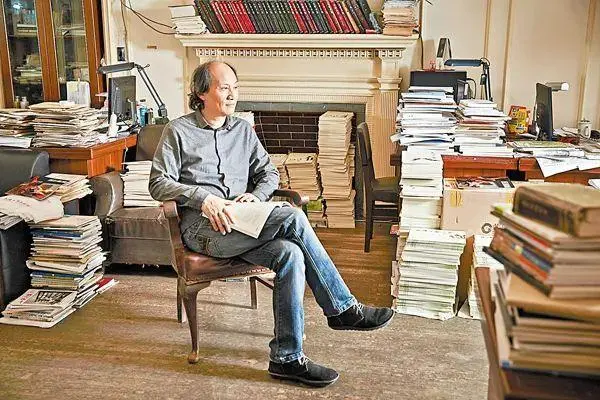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