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7年至1962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亦称中文系,系主任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李何林教授。我原来是怀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偏好报考中文系的,但当时南开大学古典文学的教师阵营显然要强于现代文学。记得现代文学课程是由三位中青年教师分别讲授的:一人先讲“五四”文学,以鲁迅为中心;另一人讲左翼文艺运动,以左联为中心;第三位讲延安文艺运动,以赵树理为中心。临毕业的时候,李何林教授才亲自讲了几个专题:《野草》研究,《故事新编》研究,鲁迅的文言论文解读。在他看来,这是鲁迅研究的难点所在。
据我所知,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这个历史时段,从事各种文体与写作或翻译的作家至少有6000多人,出版的各类译作至少有13500多部。但过往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都是单色调的,这并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多彩的历史状况。比如陆小曼,长期以来主要是作为一位八卦人物在各种艳闻佚事中出现,而人们忘却了她曾写过散文《爱眉小札》,出版过小说《皇家饭店》,还跟徐志摩合写过唯美主义的话剧《卞昆岗》。她的文字绮丽,才情潇洒,原本可以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基于这种状况,新时期以来有学者联袂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单凭一个抽象的口号来判断学术是非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因为同一个相似的口号可以反映不同实质的内容。“重写”可以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可以成为攀登学术新高峰的起点,但用什么价值观、文学观、艺术观进行“重写”那就因人而异了。
窃以为,在“重写”的过程中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匍匐在前人面前亦步亦趋,最后忘却了自己的步伐。这种“重写”其实是对前人的“重复”,实际意义不大。另一种倾向就是鲁迅1932年4月29日在自己译着书目结尾批评的那种做法,只用力抹杀别人,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仅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那些以搞颠覆为能事的人,那些片面追求“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的人,那些靠给20世纪文学写悼词而哗众取宠、文坛登龙的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
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奠基人有王瑶、刘绶松、丁易等。然而早在1932年,苏雪林就在武汉大学开设过新文学课程,不过偏重于作家作品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着和论文众多,视角各有不同:地域史、接受史、思潮史、文体发展史……大多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这些成果都值得肯定。但似乎有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有些研究者过于追求宏大叙事,似乎越宏大就显得自己学问渊博。
无限风光,不仅在名山大川,盆景方寸之间亦有风景。学者只要有心,就会发现学术风景俯拾皆是。如今,中国新文学园圃有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探索着中国现代文学新景观,令人耳目一新,澳门大学中文系的龚刚先生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
我跟龚刚素昧平生,缘悭一面,但粗读他的新着《中国现代文学十讲》,直觉是此书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十个新景观,像《杨绛、白先勇的中年危机故事》和《新文人的旧情怀:钱锺书与黄裳》两篇文章,以我的孤陋寡闻,这种选题似乎前所未见,但读后又觉得确有研究价值。《钱基博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和《穆旦新诗的哲学内涵》这两篇,也出乎我的料想,后来了解到作者是研究比较文学出身,又攻读过哲学系的博士后,就懂得他选择这些课题其实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这是他在多个学科交叉处发现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此外,《台湾现代诗的乡愁主题》是宏观整体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沈从文〈边城〉的语言风格与情感枢纽》是生命意识思考与艺术批评探索的有机结合,《新文人的旧情怀:钱锺书与黄裳》是历时性的传承研究和共时性的影响研究的有机结合。作者对周作人散文“旨趣”的分析虽然不能说十分充分,但他在认定周作人抗战时做了“汉奸”的前提下,再谈他散文的艺术特色,我个人特别激赏。我们不能因为周作人北平沦陷时期的政治表现而全盘否定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贡献,但也不能因为他昔日的光环而把名副其实的汉奸重塑为一个“文化抗日”的英雄。
龚刚还以矫正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读者对“个人主义”的误读为切入点,展示了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围绕算计和利益展开的一场博弈,实可谓褒贬得体,没有把这位传奇女作家忽而捧上云端,忽而抛进谷底。郁达夫是一位最无“创造气”的创造社元老,但他的小说多被人斥为“自我”“感伤”“颓废”。龚刚能从郁达夫笔下的“鸦片”“酒精”“乳峰”“大腿”背后清晰地看到了他自我净化的心灵历程。郁达夫如九泉之下有知,想必会对这种批评产生一种知己之感。
我感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与其仓促修史,还不如像龚刚这样从史料入手,尊重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清晰进行布局考察、个案研究之后,再从迷离混沌、复杂纷纭的状况中去发现那些规律性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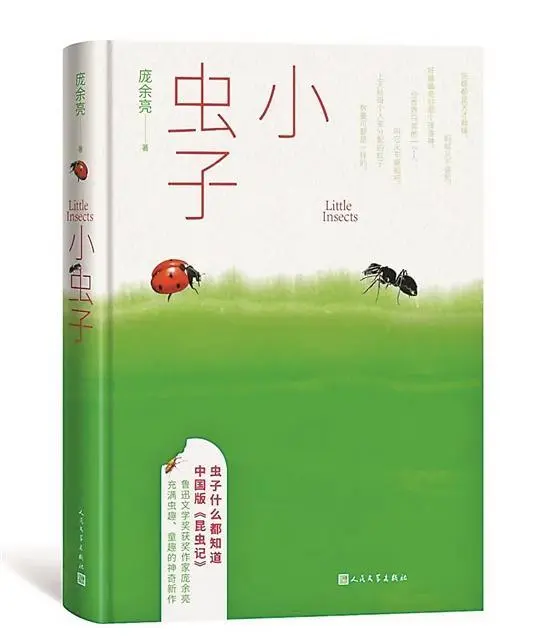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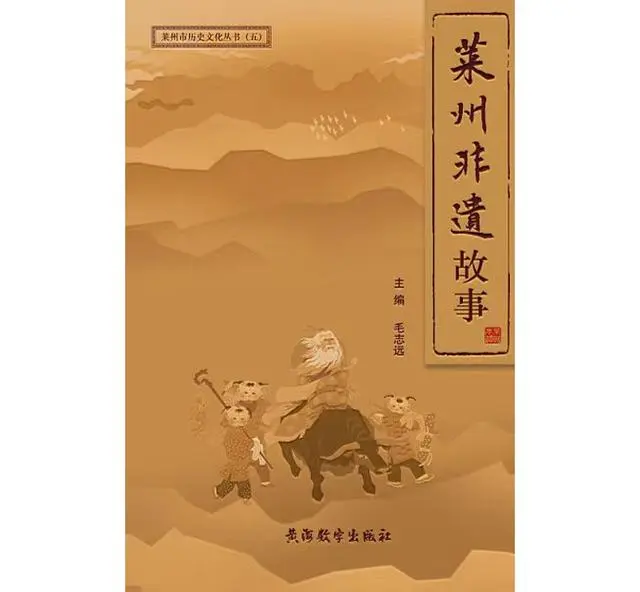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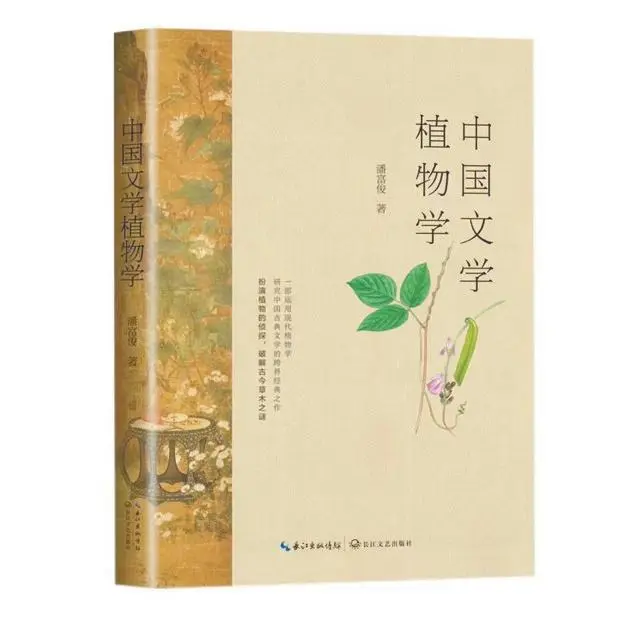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