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我有点好奇,对于一个我熟悉的人,他却有着陌生的另一面,这陌生的另一面就在他的写作里。
我读《一个人的世界》是重新了解他的过程,一个面部表情坚毅的人,一个竖着一个岩石脑袋的人,一个制造麦克风的人,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归根结底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没有危险的商人是一个好诗人。
《鸽子·麻雀》
在美国我经常见到几只灰色鸽子飞落在屋前路边吃着面包碎片并发岀咕噜咕噜声路边的几处景点成为悠闲场所养着这些懒散无忧的家伙我每次回乡路过晒谷场也见到偷食的小麻雀吱吱喳喳一有路人经过担惊受怕的样子令我恻隐之心
2019.5.17.纽约
这首《鸽子·麻雀》是《一个人的世界》最后一首诗,是他最近的作品。他在纽约有家,但他的“麻雀”在故乡,美国的鸽子与故乡的麻雀,在诗里或许有更多的意义,但我不想去解读它,诗的意义写出来时就在那里了,不必去挖掘,我只想通过他的写作来观察这个人,这个人在2019年5月17日干了什么?他在纽约写下了这首诗,他在中美之间穿梭,他既不是“鸽子”,也不是“麻雀”,他是一个商人,同时是一个诗人,事情就是这样的。但他记录了他的观察,这本诗集就是他观察的产物,所以值得信赖。
他在观察,观察是他写作的唯一手段,除此别无它法。在此我想强调这个商人的身份,他并不做买进卖出的贸易,他制造麦克风。我对做产品的人天生有好感,我曾做过进出口计算机软件,他对产品有兴趣。一个人的世界,他生产一集装箱一集装箱的麦克风,各式各样的麦克风,被他送到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嘴边,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会议室里通过他的麦克风发出各式各样的声音,有甜言蜜语,就有相互反对的声音,构成一个各种意见交织的世界。一个人的世界并不是他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一个人的诗并不是一个人的诗,而是许多人的诗,一个人的世界把许多人归结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的诗把许多人的声音收纳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人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必将是混杂的声音,是复杂多变的声音,就像风声,风声是单一的吗?不是,风声是复杂多变的,是许多风交织在一起形成的一种风声,这就是他的写作。
他的写作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持生活的原形,只有保持了生活的原形,才会发出世界最真实的声音。如果一个人通过麦克风后发出一种不是这个人的声音,而成了别人的声音,那非常可怕,所以诗歌写作就是要保持真实的声音。或许有的人就想伪造声音,有的人的写作目的就是想制造不是自已的声音,变成他人的声音,我听到过,一听就明白。但他《一个人的世界》是他的原声,只是混合了世界不同的声音,经过他的喉咙发出来,但一定是他的腔调,原汁原味的他的呼息,他的汉语组合的结果,保持原形,让原形本身发出它的诗意,不要强加给诗之外的东西。
诗之外的东西往往被我们当作了诗,其实事物本身就是诗,写作者并不需要特别费劲去挖掘诗之外的东西。过去很多年我们把过度的抒情与过度的修辞,当作了诗之外的诗了,这样的教训现在依然在毒害读者与新加入的写作者,把诗变成了一种低级的抒情与修辞。我与他都经过了漫长的这样低级的写作,人到中年方开始抛弃过度的抒情与过度的修辞,回到事物本身,把事物本身写好,尽最大可能保持事物的原形,拒绝诗之外的东西,只写诗本身,甚至在此我也只写诗本身,而不写诗之外的东西,过度的解读当然十分恐怖,我见多了过多的对诗的解读,令人难堪,破坏了诗,但我们的读者似乎习惯了过度的抒情与过度的修辞,更喜欢过度的解读,非要在诗中挖掘出诗之外的东西,这样就拉低了当代诗歌的水准。《床》
爱与罪在一起的词是名词也是动词是时间给予它太多一叶一菩提一床一世界这床是爱的床这床是罪的床罪在黑暗里爱也在黑暗里不在乎白天与黑夜一切皆在一念之间为了你爱与罪之间常常被自己忽略
2019.5.16.纽约
再次回到写作现场,他突然顿悟开了,我熟悉他过去的写作,朴素的抒情腔调是干净的,饱满的,他与我的老友吴茂盛合出过一本诗集《诞生在冬天的孩子》,那是青春发育期的声音,我们沉浸在发育的喜悦中,享受生活的动荡,当年我是一个孩子,我注视着另外两个孩子的照片,就像注视着我自已,我们都是那样写作,写作让我们度过了贫穷的少年,现在回首往事,那逝去的一切都构成《一个人的世界》中最坚实的底色。
我读《一个人的世界》,其实我读到了一个人的历史,他写的是现在的生活,但一首诗中往往有一半是过去的生活,他的诗构成了一个奇妙的现实与历史的世界。《鸽子·麻雀》是这样,这本诗集的倒数第二首《床》也是这样。不过《床》更为宏大,“爱与罪”被他写穿了,每一句都是子弹,一句都是铁锤,直接击穿了诗,锻打了诗,诗的质地坚硬发亮,“一床一世界”,先锋、现代、亲切。
他的写作水准并不低,是口语激活了他的写作,如果没有口语的意识,如果仅仅在传统抒情的格调里打转,他不可能享受到诗的快感,这本诗集虽然作品还不多,但我看出他在享受写作的快感,这就够了,一个素朴的商人本身就是一个朴素的诗人,老兄弟,你的写作带动了一波老兄弟,有人在问你:“他写得很快活呀”,是的他写得太快活了,这本诗集及时告诉老朋友们,你找到了写作的快乐。
我们生活在口语中,但往往我们在写作时就抛弃了口语,把口语看得低于书面语,我曾经还遇到过不用口语讲话的人,他与众不同,他说话全部用西方文论式的书面语,他把自已与众人区别开来,我们把他试为“高级的人”,在一起久了,我们慢慢习惯了他,但他偶尔也会忘记自己的书面语,突然冒出少量的口语,尤其在他有了孩子以后,因为孩子可不管他那一套,孩子要用口语说话,他的孩子还没有学会用西方文论式的书面语说话。
有很多诗人己经习惯了用西方文论式的书面语写诗,读者与同行们也习惯了西方文论式的书面语诗歌,形成了中国当代诗歌一个标准。成了标准就万事大吉了,只要往标准上一套就可以试别你写的是好诗还是坏诗。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你尽情以自己的口语说话,因为是你“一个人的世界”,你首先声明这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你们那一套标准对于我是无效的,如果要说标准,我建立了我的标准,我的产品我说了算,我制造的麦克风,你们谁都可以对着它说话,但出来的一定要是你自己的声音。我的诗就是我自己的声音。
《一个人的世界》里有很多诗写于纽约,我想纽约对于你更多是生活,是你的家庭,有了生活与家庭就有了诗。在中美两个不同的空间,你有了时空的想像,你的观察与你的口语相遇,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我熟悉的那个叫做“蓝战士”的少年诗人,我们是出生于同年同月的老兄弟,读这本诗集就像读我的诗集,我的喜悦是很多朋友的喜悦。蓝战士蓝战士,永远的诞生在冬天的孩子,你《一个人的世界》也是我们一波老朋友共同的世界,我们都来抢你的麦克风,我们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汇总为我们的诗歌混杂的声音。
从“蓝战士”到“冯桢炯”,经过了30多年,其实一切都没有变,你还是你,你朴素的腔调没有变,人最本真的情感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更为清晰,你在曾经的诗集《一种生命》《风铃小语》里的你,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更为坚实,你贴着自己的语言在写作,你找到了生活与语言最为妥贴的新的方式,你把你的观察记下来,你就写下了属于你的诗。
《一个人的世界》开创了你语言转向的新世界,在写作中我们都是中年孩子,像孩子一样说话,不说西方文论式的书面语,说本真的话写本真的诗。其实我们并不会说话,我从没见过你滔滔不绝,我们都是木纳的人,更多时候还是沉默寡言的人。是的什么人说什么话,我们长这么大还没有学会说经过包装的那一套语言,你是一个制造产品的商人,我曾经也是,我们只说产品说明书式的话,因为我们相信产品说明书最为直接,最为本真。我们的写作本质上只是要写下产品的构成,要按下哪一个开关,我们使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少的语言,我们不开口说话时就吃菜,把米饭扒到嘴里,我们说话时不拖泥带水,用简单的陈述,不用哪怕是多余的一个字,我们开始不相信形容词了,活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形容词了,我们像中年孩子一样写作,尽最大可能保持生活与事物的原形,在诗里不破坏生活与事物的原形。
(诗集《一个人的世界》冯桢炯著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周瑟瑟,著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电视制作人、纪录片导演。著有诗集《松树下》《栗山》《暴雨将至》《鱼的身材有多好》《苔藓》《世界尽头》《犀牛》《向杜甫致敬》(英、西、日、韩、瑞、蒙、越多语种)等,长篇小说《暧昧大街》《苹果》《中关村的乌鸦》《中国兄弟连》(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小说创作)等20多部,以及《诗书画:周瑟瑟》。曾参加哥伦比亚第27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第七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第三届亚太地区诗歌节。
诗人简介:
冯桢炯,1968年出生,广东恩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5年开始创作,已出版诗集《一种生命》《风铃小语》《一个人的世界》等六部,诗作发表于《作品》、《飞天》、《诗刊》、《诗潮》、《诗选刊》等刊物,获韩国“亚洲诗人奖文化奖”等奖项。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理事。现任纽约《中外诗人》杂志主编。现居江门和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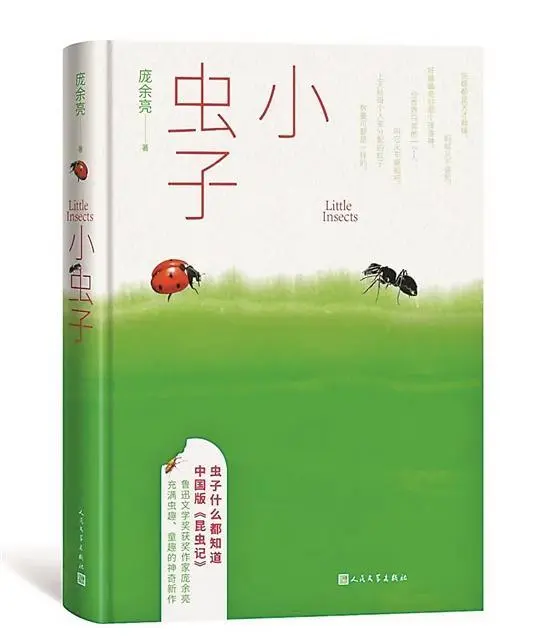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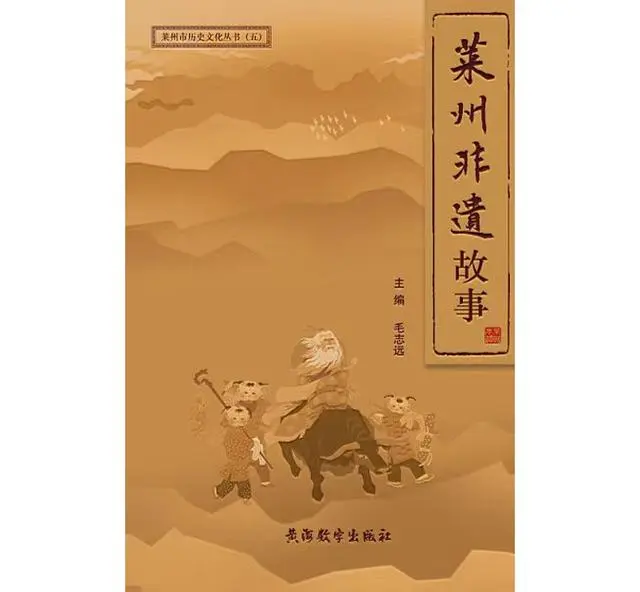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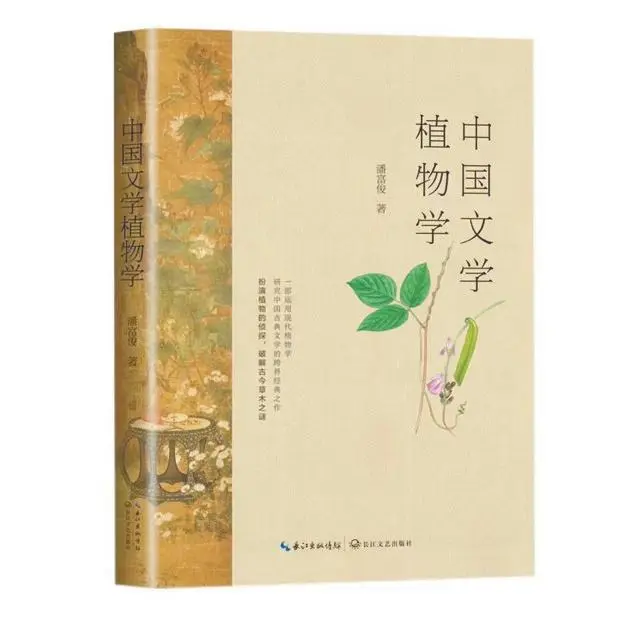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