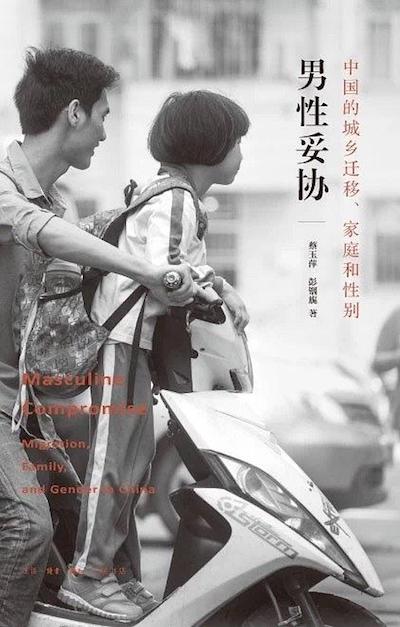
《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蔡玉萍、彭铟旎著,罗鸣、彭铟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7月出版,195页,38.00元
在时代的浪潮中沉浮恐怕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要在大潮中掬起一朵浪花,并将其轮廓形状完整清晰地示于世人,很考验社会研究者的功力。这也是《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一书的独到和成功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波澜壮阔、卷挟亿万农民工,相关研究论文汗牛充栋,却少有作品讨论男性在这一宏大历史过程中的主体经验,遑论他们在漂移不定的家庭生活中发展出的颇为细腻和纠结的情感。蔡玉萍教授和彭铟铌副教授在《男性妥协》中抓住了这一普遍存在、又常常被忽略的面向。她们以数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把在东莞、深圳和广州打工的一百九十二名男性农民工、七十一位女性农民工与十一对夫妇的生命经验浓缩呈现给读者。本书理论和文献的梳理缜密、案例类别清晰,加上对关键概念的提炼,显出社会学强大的思考力;与情感有关的主体叙述又颇能使身为男性的笔者感同身受、手不释卷。
正如本书标题所揭示的那样:男性妥协了——或者正在妥协。在城市里,他们与占据支配地位的、强调男性刚强有力、生殖力、财富和创业才能的男性气质论述妥协(17页、第2、3章);在家庭内部,他们与“男主外、女主内”的理想分工妥协(第4、5章);在家乡和城市之间维系家庭,他们与构成乡土父权制核心的从夫居制度,以及以从夫居为基础的、照看老人和后代的殷切期待妥协(第9页、第6、7章)。男性气概在经年累月的辗转城乡过程中打了折扣,用更通俗的话来讲,他们认怂了、服软了、变乖了——向爱情、向理想、向家庭、更向生活本身弯腰低头。
从章节安排上看,这本书从亲密关系、婚姻中的家庭分工和家务、父亲的职责和儿子的职责入手,分析男性气概的内涵与变迁,呈现作为恋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男性的主体经验和这些经验的内在张力。具体而言,在亲密关系上,年轻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园、城中村让男性青年有足够的机会与年龄相近、经历类似的异性互动和交往,不断迁移、与妻子分居的男性甚至也拥有了更多婚外情的机会。溜冰场、舞厅、酒吧、咖啡店都是让青年男女们怦然心动并发展一段关系的场所。在城市中的浪漫经历和性经验的多寡,也因此成为男性青年值得炫耀的资本。然而,浪漫和实用物质主义在都市约会文化中往往是混合的,爱情永远与消费捆绑在一起。经济能力不足或低下,都让“骑自行车”的男性在与“开宝马”的男性的竞争中处于下风。这些以浪漫开端的爱情,往往以父母介绍对象、放弃“真爱”、娶家乡邻近地区的姑娘成家作为终结。
“成家”是父权制的男性气概的核心。换言之,在传统的观念中,一个没有成家的男人不算男人。成家之后,父系观念和是否要延续从夫居(即婚后女性进入夫家居住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又成了处在流动之中的丈夫与他们的妻子拉锯的焦点。Stacey指出从夫居是中国父权制的基本结构(77页)。围绕着给儿子攒钱盖房子娶媳妇,不仅构成男方父母的压力,也对在城市里打工的已婚男性构成压力。为了延续父权制这一基石,男性在家的父母和在城乡间流动的男性自身两代人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甚至造成年轻男性倾向生养女儿,也使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获得了更强的谈判能力。根据传统,丈夫需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他们对故乡恋恋不舍、强调妻子对夫家和照顾子女的责任;而妻子在婚后倾向定居在城市或与娘家一起住,因此双方争执不休。由于经济的局促,丈夫们在往往妻子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大事儿”上妥协,而把孩子留给了在家的父母照料。与此同时,他们把财政权这样的“小事儿”,或委托、或沟通、或通过“表面让步”的策略让渡给妻子。如果说刻意作出“大事儿”“小事儿”的区分还是一种话语上的策略和妥协,那些将收入花费在与朋友喝酒吃饭、赌博、按摩上的男性则常常与妻子发生冲突,甚至不惜使用暴力,以维系日渐浅薄的尊严。
作者观察到,由于迁移而产生的核心家庭化(即一夫一妻共同居住、劳动、养育后代)的趋势,让城市中的女性不得不脱离对其它女性(例如婆婆)的依赖而承担家务,也让男性在参与家庭内部的劳动成为必要。做饭、带孩子、打扫房屋、洗衣服都属于家务劳动。有些夫妻延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这一般是在男性收入较高足以支撑家庭经济的情况下产生的,丈夫取得了家务劳动的“豁免权”。但更多的男性在参与这些女性习以为常的而又琐碎的家务过程中,呈现出一幅渐变的男性气概光谱。丈夫们或策略性地逃避、或选择性接受、或主动参与;有些家务劳动是被认为是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承担的,有些则是被认为更为女性化、为女性专属。而承担更多的和更“女性”的家务,正如作者所言,可能反映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和谈判能力。令笔者莞尔的是一位在家洗衣服、做饭和打扫卫生的丈夫。他特别担心邻居看到他在阳台挂衣服,也怕湖南老乡们发现他在替老婆洗内裤而嘲笑自己。这种暗中妥协、明里藏掖的做派,为作者笔下小人物平凡而沉重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喜剧色彩。
为了陪伴孩子,选择从城市回到家乡谋生的男人。(新闻图片)
在代际关系方面,外出打工虽然有限地增强了男人们经济能力,但是城乡二元分隔、现有的户籍制度却严重剥夺了他们把子女带在身边的权利。有的长期与子女分离的父亲,甚至需要说服留守在家乡的子女接受长期分离的事实:父母就像觅食的老燕子,不飞出去找吃的,屋檐下的小燕子就没有东西可以吃。这些话读来心酸,但父亲们并不吝啬(至少向研究者)表达他们因为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而产生的内疚、痛苦和自责。他们也从与子女在情感上保持疏离而维持威严的父亲形象,转为对子女在经济上和感情上进行双重供养,要么通过物质补偿、要么通过远程网络沟通与异地子女的情感。城乡迁移也造成了与父母之间关系的新问题,创造了一种“反常的代际机制……它使得成年男性无法履行对年迈父母对照顾责任与义务,……也意味着年迈的父母被动员起来解决年轻一代的照料难题”(149页)。但研究者敏锐地发现,虽然男性农民工不质疑“孝顺”的文化观念,在实际行动上,不少男性寄期望于妻子、或者由他们的姐妹照顾年迈的父母,而不由自己承担;他们也发展出了“合作照护”和“危机照护”两种策略,即根据家庭的具体情况在家庭成员中分担照顾任务、或者仅在父母危重时提供有限的照护。
两位作者通过对农民工家庭生活进行剥洋葱式的分析,向读者清晰展示了处于城乡迁移背景之下的男性农民工所面临的多个层面的拉扯,以及伴生的情感与伦理危机。这些拉扯和危机既涉及纵向的、与父权制有紧密关系的父亲—自我—子女的关系,也有横向的亲密关系与夫妻关系。一方面,由于城乡迁移造成的代际分离,对上孝顺、对下保持威严的传统男性气概遭到了挫败;另一方面,男人在家庭决策中起主导作用、或者“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模式也很难在迁移造成的困境和女性经济地位上升的背景下维持。“男性妥协”这一概念描述了“他们”为形势所迫,在行为上做出的调整、改变、退让的过程。同时,从多个维度的细心刻画,也保留了变迁中的男性气概的完整形态。然而男性妥协是有局限的。男性仍然坚持维护父权制的两大基础——父系氏族和从夫居。作者在文末不无洞见地指出,“具体的男性气质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179页)。我们从这里也许可以引发出更多关于社会变迁、文化价值和情感表达的讨论。
至少从男性农民工主体的叙述来看,文化价值观念之变与不变,情感表达是重要的观察窗口。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情感与文化价值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如人类学家Webb Keane指出的那样,诸如价值、伦理等可以视为生活的形而上学的范畴,实际上有其涉身性、情感性基础(Keane 2016)。在纵向的、父系的家庭关系(包括子职和父职)维度上,似乎自责、歉疚、愧疚、失望、骄傲的流露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而在男性对夫妻关系的表达中,我们找不到这些充满敏感性、动情的叙述,他们的“妥协”更关乎社会认可的、外在的面子,而不是出于内化的、涉身的伦理和情感印刻。在此意义上,笔者同意作者提出的男性妥协的局限性,但认为作者将男性妥协与诸如“性别平等的原则”的观念相联系(179页),似乎止步于从观念上探讨文化价值、而没有在作者已经开创的情感维度上,将文化价值的存废和男子气概的变迁的关系的讨论更进一步。此外,作者将传统男性气概仅仅与威严的父亲形象相挂钩,似乎有单薄化传统的男性气概之嫌。姑且不论传统到底采取“父严母慈”或“母严父慈”的模式(例如清末谭嗣同回忆自己家庭是“母严父慈”),将正统的儒家伦理和平民百姓的家庭伦理划等号也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这样有助于反衬出离开父母和子女的男性的情感喷涌状态,但平民老百姓的父系情感在城乡迁移背景下是否具有延续性、而不是仅仅是一种断裂?
此外,笔者注意到,男性农民工在城乡迁移中被边缘化的焦虑,部分来源于与在老家做生意、开餐馆、有房有车的朋友的比较(46页);而在城市里,为了维系男性纽带的消费行为,也常常成为夫妻在财政权上的冲突诱因(84-85页)。这似乎暗示着,在离开乡村家庭更近的地方,生活可以更好的延续。周大鸣(2006)指出,随着珠三角“村改居”的行政化措施的实行,城中村对农民工的工作、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非正式吸纳能力也在削弱。在任柯安(2016)看来,珠三角的农民工研究代表着一个极端,那里的城乡壁垒相对难以逾越、剥削也相对严重,而中国成百上千的县城则提供了研究城乡移民的另一个场域,那里移民家庭与原生家庭的联结并没有完全切断。在这些地方,男性气概会如何演化呢?迫使农民工妥协的条件,如作者所言,会不会发生变化或消失,从而出现更传统和保守的性别关系(180页)?还是因为生活境遇的渐进式改善,“小富即安”,而使得对于传统男子气概的坚持变得没有必要呢?其次,这些材料也暗示着,男性群体和男性纽带(male bonds)是一个塑造、强化男性气概的重要场所。不过,男性纽带在作者所引用的康奈尔(Connell)的框架中——在国家、工作场所、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等制度中研究男性气质(20-21页)——是阙如的,而在一些研究中国或东亚男性气概的作品中则很常见(例如Kam Louie 2002)。笔者在对进城男性小商贩的研究中观察到,在城市里,男性群体既是男性个体获取资源和经济上支持的重要场所,也是彼此竞争、情感表达和互相认可的圈子;这种圈子往往排斥女性,从而造成男性在处理“兄弟”关系和夫妻关系时左支右绌、甚至不惜以斥责妻子以维系男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维度是男性主体经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可以丰富对城乡迁移背景下男性气概演化的讨论。
本书由英文原著翻译过来,因此在译本中保留了一些向英语读者解释的内容,对于中国读者则略显冗赘。此外,尽管理论讨论缜密而丰富(尤其是导论和理论框架对学术读者大有裨益),恐怕也不能为大众读者所轻易理解。不过,鉴于本书讨论的实在是一些饶有趣味的性别话题——何为男人?何为中国城乡变迁背景下的男人?这些男人何以维系流动中的家庭?任何关心当代中国社会巨变之下每一个男人、女人、家庭、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终将老去的父母的命运的人,都可以受益于这本小书。任何像广大的农民工家庭一样跨越千山万水维系家庭、包括两位作者在内的“学术移民”(第4页),都可以在书里的故事找到自己的影子而感同身受。中国社会像一本打开的大书,可以正过来读,从宏观变迁读到个体命运,也可以反过来,从个体叙述读到社会国家。任何一位打开这本小书的读者,无论正着读还是反着读,相信都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细小的浪花跳跃翻腾,感受到笔者所感受到的社会研究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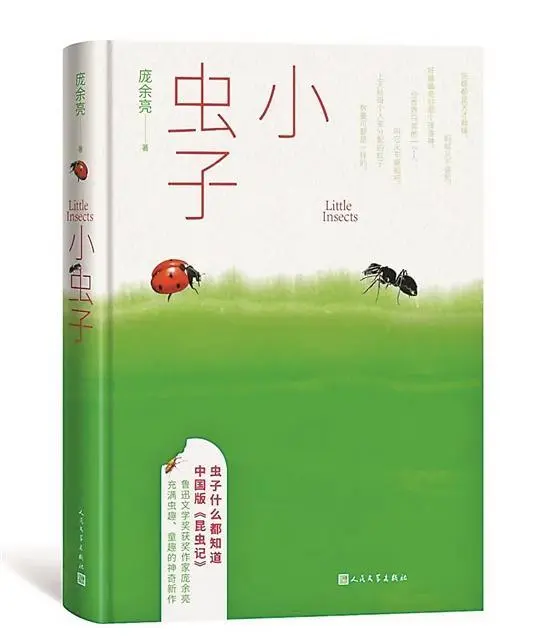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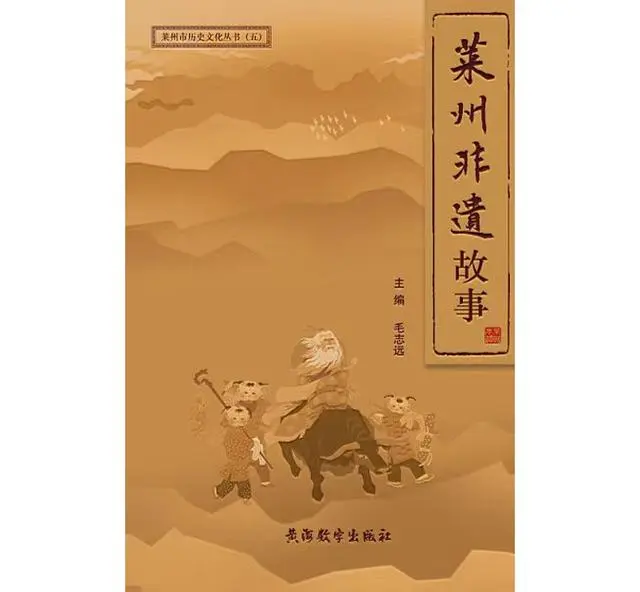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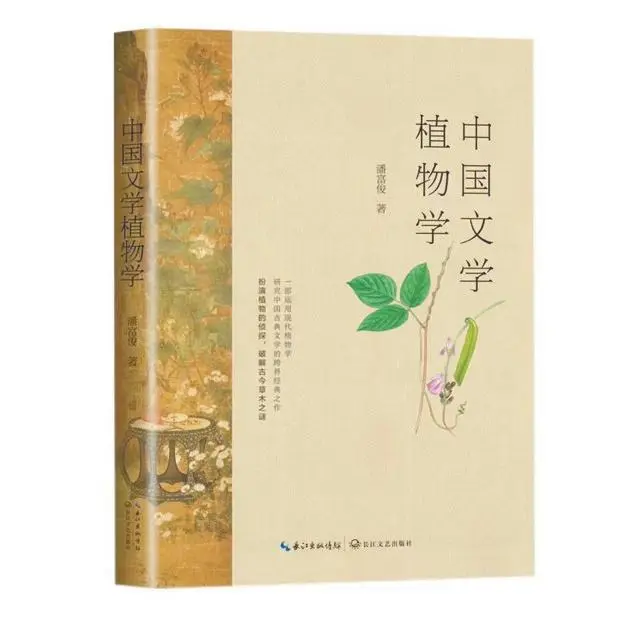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