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清茨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诗人,说她令人瞩目,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她的作品中体现了女性写作和古典写作的有机融合。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是,杨清茨的诗歌创作拒绝瞬息即逝的灵感捕捉,甚至拒绝现代诗歌业已形成的圆熟的逻辑和修辞装饰,她的全部文字都具有舞台性,也就是说,当她将一行行文字留在白纸上时,她把自己戏剧化了、意象化了。必须指出,杨清茨的艺术创作甫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她惯于利用“点、线、面”各种媒介表达和现实中不一样的那个主体性:所谓的诗、书、画不过是进入自己的“躯体”时的一次细致入微的装扮。
很难精准地概括杨清茨的文学/艺术表达,她的诗歌中鲜少现代性的冲突、新与旧的张力和社会矛盾的个人性汲释——这本是现代诗歌拯救灵魂时的种种高尚的目的性手段,如今因滥用而饱受诟病,甚至看不到“新红颜”写作的种种迹象,但她透过文白夹杂的语言运用和旧时王谢之堂的意境构造,形成了自己明清闺阁诗人的特质:通透,善感,灵性和冷清,似乎只有在《红楼梦》中一个幽静的园子甚至《聊斋志异》中一个半掩的窗棂才能找到这样的投影。我想,这种形象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贵族化的精神谱系和一个个体性的自我修持交织形成的意念场,有坚持,有拒绝,也有对烟火之气的种种“改写”。这么看来,杨清茨的创作就不是爆炸式的、冲击式的,这种女文士的艺术表达气质本质上倾向于一种自燃自爆乃并借此实现自我肯定和提升。由此,杨清茨实现了艺术创作和生活日常的无缝对接,实现了精神玄想和当下之境有机融合。亦即,单就诗歌这门文学体裁而言,杨清茨不是在创作,而是在生活,在践履,在展演,她就是舞台,而舞台上只有她自己,体现出了生命书写与文本自足的统一。必须指出,这种忽略技术、技艺、技巧的诗歌是无法创作、拒绝模仿的,除非创作者也能达到这样的心地修养和有无之域。
讨论杨清茨的作品,绝不可以忽略“心”“性”这样的逻辑语词和理论集束。通常会将诗学界定为诗学,将诗性翻译为人性,就在于诗歌和人这个“心性”之物是对应的。毫无疑问,诗歌是诗人情感、思维乃至现实反应的自然流露,诗歌和诗人相互表达,在此过程中,心体乃一个核反应堆,万事万物经此而为宇宙的声音。杨清茨的作品多是通过内在个我之感受处理外在客观,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是她个人形体和情绪的衍生品。在杨清茨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一些很通俗的物品,经过她普通的、略微生涩的语言提炼——似乎语言是跃动的,期待被她纳入怀中——表现出了一种陌生化效果。雪莱曾说:“人是一个工具,一连串外来和内在的印象掠过它,有如一阵阵变化的风。”若果如是,杨清茨可为神的工具(代言人),其笔下的描摹对象都非技艺的、技巧的、技术的,而是有神力附着却不留痕迹。我一直赞同这样的观点,诗歌并非苦吟或推敲而得,而是灵光一闪式的、神启的产物,即同柏拉图指出的:“若是没有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如果存在“心”诗人,杨清茨的作品毫无疑问必须基于神秘主义发生学上才可以解读和诠释。
外在印象上,杨清茨的诗歌有强烈的视觉化,这是否与她是一个画家兼书家有关,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诗歌的独特外在体验符合诗之所以为诗。我们都知道,诗人与诗歌是人与物的关系。进一步的解释是,人和物是相互参照、相互生成的。某种意义上,人是物,物是人。一首诗歌的诞生,意味着诗人和物发生了“肉体”关系。及物的过程,就是视觉。这种逻辑并非没有来自,因为语言就是及物的产物——物是语言的出发地——没有视觉,便没有思维、语言及其对物的反应。我坚持认为,杨清茨的作品契合这样的艺术规矩——创作诗歌即是立象,也就是创造意象——即把抽象的观念借以对应物的描写来象征性地暗示其意。这种通行的说法其实不免浅显了。必须指出,诗歌来自于人和物的相互发现,诗歌不止于立象,象本来就存在的,人要做的是通过发现物而发现己。诗歌为什么是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就在于她是虚实相立相生的——诗歌在物中,而不是只在我们心中,可以说,心/诗与物是相互本源的。借助杨清茨的作品可以给出进一步区分或界定,我觉得物是第一位的,没有物,就没有人和他的一切社会性活动:没有物的参照,我们就不能把自己自物中分别出来。杨清茨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借助日常之物之景来反应(似乎构建一词更为合适)自己内在的镜像,当我们阅读她的篇什时,很难将景、色、物和她区分开来,但她又明明站在笔下种种意象的对面,我甚至怀疑福楼拜说的“他们之所以伟大,反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指的就是杨清茨这类不写而写的诗人:写作有如神行,灵气逼人,诗路多元化,有如自然之气动,能感受的到,却了无痕迹。
聂鲁达在自传中斩钉截铁地说,写诗是一门手艺。不必计较这位大诗人是在何种情景下说这句话的,至少表面义上理解,确实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诗歌若是手艺,她呈现出来的将是静悄悄的文本,你无法感受到内在的火焰、波涛、电闪雷鸣是如何纠葛在一起,成为直击读者的、撕扯性的力量。至少,杨清茨的作品就不是手艺,尽管会经过删减、反复、择弃,但我们读到的却是一颗自然而然、充满光影交错的、有意味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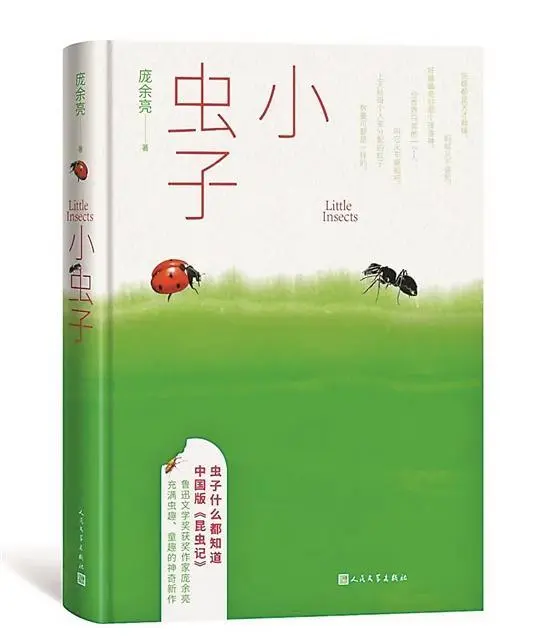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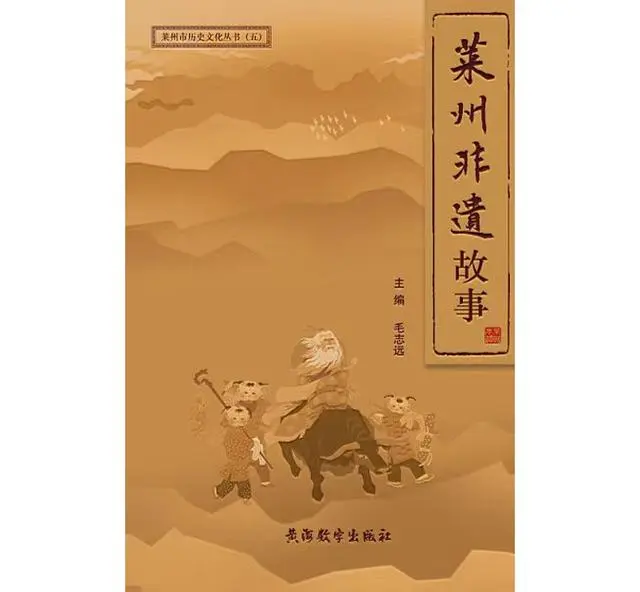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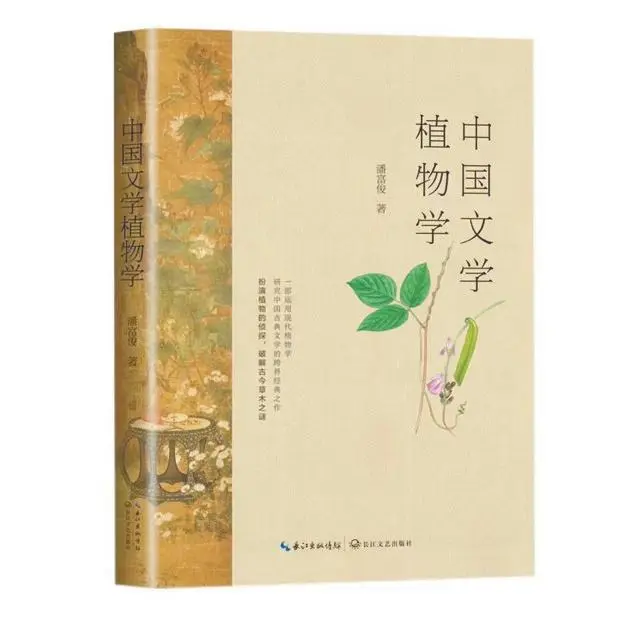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