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看到《黄牧甫与王秉恩交往考略(附黄牧甫原色印谱)》,为“秋水斋金石丛刊”的一种。因为印制相当精良,价格又和蔼可亲,就入手了一册。拿到一看,有点诧异。全书除序言、后记各两页外,共二百二十六页,由“黄牧甫与王秉恩交往考略”“黄牧甫致王秉恩信札”“《颉颃楼藏印》(黄牧甫卷)”“黄牧甫年谱长编”四部分构成。其中,与书名相同的第一部分才二十页,除去各种插图,内容约一万五千字。第二、三部分分别占十七页、九十四页,都是原件彩色影印。第四部分也厚达九十四页,约六万来字。
黄牧甫是晚清第一等重要的篆刻家,中国篆刻史上有数的人物。王秉恩作为张之洞幕僚,在清末曾任广雅书局提调,对黄牧甫多有提携、帮助。此书收集的十二通黄牧甫致王秉恩手札为私人藏品,向未在学界公开,对研究黄牧甫的艺术经历颇有史料价值。《颉颃楼藏印》(黄牧甫卷)原谱一函二册,为编者自藏物,其中内容也颇不常见。将这些资料公之同好,无疑是一件大功德事。
按学界惯常的思维,此书主体应是第二、三部分黄牧甫的信札和原色印谱。第一部分相当于一个学术性的前言,第四部分年谱才是附录。既然如此,该书似宜以“《颉颃楼藏印》(黄牧甫卷)”作为题名,或另拟一涵盖信札和印谱的书名。然而,编者直接以前言部分作为书名,实在未免有喧宾夺主之嫌。
无论如何,该书总共只有一册,就算书名与内容不符,总还在同一册上,即使别扭也不至于到十分。最近该“丛刊”又推出一种《陈豫锺与陈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陈印则〉原色印谱)》,别扭的程度可就更加严重了。
与前书相类似,《陈豫锺与陈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陈印则〉原色印谱)》也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带有研究性质的一篇“《二陈印则》及陈豫锺与陈曼生交游考述”,篇幅三十三页。然后是《二陈印则》原色印谱。由于该印谱篇幅甚大,原谱为线装一函十册,此次影印按“陈豫锺卷”“陈曼生卷”作精装两册。为了突出效果,编者收集了十四方二陈的印章原石,将印面、边款的高清照片,以及精挑出来的九十八方印蜕、二十八面边款放大影印,又单独编成一册。
实事求是讲,按“金石丛刊”的标准,这套书算是做得十分精彩的。《二陈印则》大约成书于1938年,是现代篆刻家高络园在辑拓著名的《丁丑劫余印存》的同时,将西泠八家中陈豫锺、陈鸿寿(字曼生)的印作单行而来的。前四册为陈豫锺印,计八十五方、九十二面;后六册为陈曼生印,计一百一十六方、一百一十九面。这批印虽然在其他出版物中不难看到,但此次影印的底本纸墨精良,辑拓水平相当高。将其加以高清影印,可谓造福艺林之举。
影印过程中,编者是用了心的。原色影印的效果,完全可以说仅下真迹一等。原书纸张的纤维、印泥的堆积感、边款的墨色和缩水痕,丝毫毕现。更难得的是该书包括了一些学术性内容。除了前面有一篇研究性序言,分析《二陈印则》原印的来源,以及二陈的往来、交游、异同,还列有“《二陈印则》四家藏印表”,直观地展现谱中各印的来源,以及在其他出版物中的收录情况。对每一面印蜕和边款都作了释文,书前列有“释文异体字列表”。
唯一让人感到别扭的便是书名。上册明明应该叫“《二陈印则·陈豫锺卷》”,现在被标作《陈豫锺与陈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陈印则〉原色印谱)·陈豫锺卷》。下册、附册本来应该叫作“《二陈印则·陈曼生卷》”“《二陈印则·附册》”,现在印成了《陈豫锺与陈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陈印则〉原色印谱)·陈曼生卷》《陈豫锺与陈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陈印则〉原色印谱)·附册》。如果说,上册标着《陈豫锺与陈曼生交游考述(附〈二陈印则〉原色印谱)》这个书名,里面多少还有一篇同名的文章在。下册、附册也叫这个名称,里面内容与这个书名可是没有半毛钱关系,不存在任何与二陈交游相关的文字和实物。
况且,该丛书既然叫“金石丛刊”,书名自然应该体现出一些金石味。现在两种书分别叫作“交游考略”“交游考述”,好像是史学著作一样。也许想画龙点睛或出奇制胜,结果却让人从书名上难以判断是金石学出版物,等于反而掩盖了它自身的特色。
笔者实在想不通编者为何要起这样的书名。不知是否出版流程上有某种难言之隐。作为读者,笔者对编者的劳动十分尊敬,也十分感激。在此提出以上的想法,旨在希望编者能把好事做到底。书编好了,索性把书名也起得恰如其分。要不然,写一篇序言就把它当作专著,而把相关原书当作附录,那么,写一篇跟《四库全书》相关的文章,是否也可以把《四库全书》当作附录一道出版?大家都这么做的话,学术界、出版界可就乱套了。
顺便说一句。不久前看到一本辑佚书,辑者从各种古籍中辑出一些古书片断,编在一起,里面除了一篇前言,编者不着一字,可是居然尽得风流,在版权处堂而皇之地写作“著”。令人不胜骇异。出版物的著作权类型,难道时至今日还能鱼目混珠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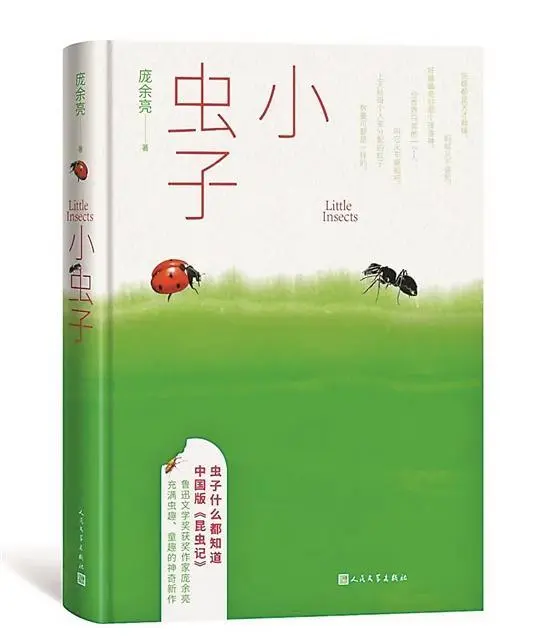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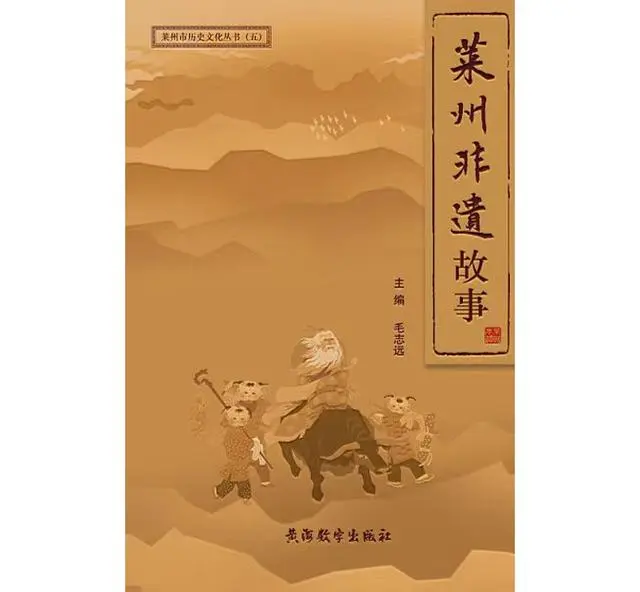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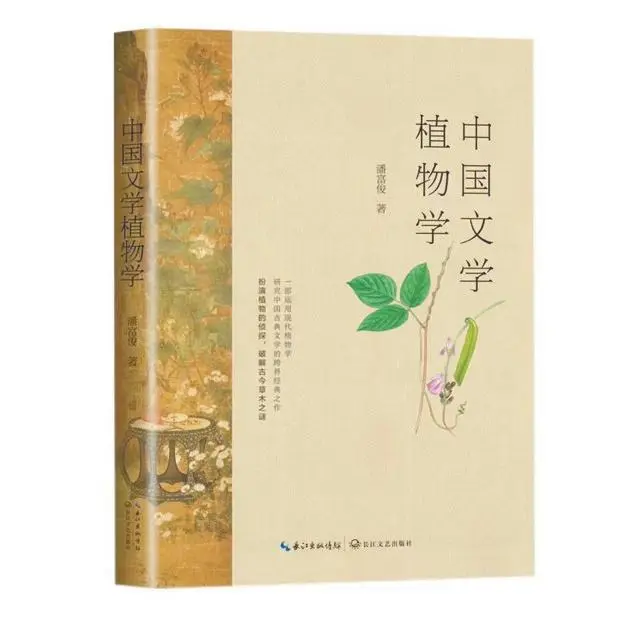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