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高校和研究机构是文学经典化和去经典化的主要推手,但近百年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20世纪以来,学院评价让位于文学奖项及媒介和市场联动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后者在文学场域所产生的压倒性优势仍在不断扩张。资本与技术合谋、大众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主义则为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如何因势利导、取法乎上,占领文学场域的制高点,也许不失为是一种突围。而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文学原理学批评。它是学院派文学立场、文学观念和文学生态的核心表征。
大众消费文化与经典解构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学者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艺术的非人性化》和《大众的反叛》中正式提出了大众消费文化和大众消费社会的概念。在他看来,这种文化将摧枯拉朽地颠覆几千年来由精英阶层建构的文明传统。当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站在社会精英立场上批判大众文化和大众社会,就像巴尔扎克曾经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上批判法国社会一样。但前者的片面性在于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大众,而在资本及其制导的消费主义。
为了抵制消费主义和艺术商品化,西方现代派开始有意无意地走上一条波谲云诡的道路:从乔伊斯到毕加索,一时间标新立异蔚然成风。但诡异的是他们不仅未能阻挡艺术消费主义大潮,而且使自己也迅速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横扫千军般的解构、重构、解构,已经没有人可以笃定地说文学如何、经典何如。即或文学概论和文学原理著述多如牛毛,却大抵彼此雷同或自相矛盾。随便举一个例子:近年成为热点的“世界文学”及其原理就相当不尽如人意。
自歌德至卡萨诺瓦、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的滥觞流经19和20 世纪,业已蔚为大观,成为一股热潮。但是,围绕什么是“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内涵外延却如云似烟。首先,人类各民族文学之和为世界文学,这是客观存在,毋庸置疑,也无需引号。其次,歌德于1827年萌生了“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怀想,谓“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歌德的这个“世界文学”是必须加引号的,因为他的这种理想主义怀想并不切合实际。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非常清楚。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再次,一切文学的历史终究是经典的历史。这就牵涉到经典的界定(包括有关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譬如,何为经典?“世界文学”的历史怎样书写?经典谱系如何建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鉴于之前笔者已就“世界文学”和世界主义的关系进行过评点,这里恕不重复。我想提醒和诘问的是:中国文学在这个庞杂得了无边际的文学地图中何经何纬?中国文学经典在这个由西方学者主导的话语天平中有何分量?最后,那些孜孜汲汲执着于社会历史书写的国别文学、民族文学是否进入了这个看上去十分可人的大画饼?譬如巴基斯坦文学,再譬如缅甸文学,人们又知道多少、关心几何?
还有各种文学奖项和市场的关系。这业已成为世界文坛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其一是诺贝尔文学奖明显放弃了诺贝尔关于奖掖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的初衷或愿景,越来越任意,甚至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和莫名其妙。在21世纪20位获奖作家中,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少之又少。其中的极端例子便是摇滚歌手鲍勃·迪伦。虽然我个人对他不敢妄加评论,但国际舆论普遍倾向于惊诧和怀疑。其二是目下奖项之多、评价标准之乱,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据曾艳钰教授统计,仅美国就有1100多个文学奖项。它们对文学及文学市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技术让渡
由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同大众文化、大众社会相辅相成,并被推到了前台。从网络文学到字节跳动,艺术的模态和生成、传播、接受机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完全不亚于文学从口传到书写的转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网络文学所改变的自然不仅仅是传播和阅读方式,模块化、程序化显然残酷“切割”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这充分体现于其类型化表征。一如过去所谓的“内容决定形式”,相应的旨趣或主题、传统或题材必然成为类型文学的润滑剂和定格尺。同样,受众群体,尤其是粉丝(拥趸)的参与和助推又无疑成为类型“格化”或谓固化的重要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由此导致的创作机理的演化使文学的个性化或个人化创造回到了众声喧哗的“新口传时代”。当然,这个“新口传时代”至少在当下是要加引号的;但我相信真正的新口传时代很快就会来临:多声部合唱共构。此为其一。其二是多媒体融合所导致的图文化和影像化倾向也早已露出端倪。卡梅隆的不少电影都是边写边导边改边演,分镜头剧本常常只是个楔子。从剧本、演出到剪辑,集体创作的权重越来越大。电视剧也是如此,先有剧、后有本的情况,在胶片时代终结、数字时代来临之后已非罕事。至于高智能时代人机一体,机器人、智能人越过目下的“二次元”而直接生成“三次元”已完全没有悬念。但这必定是导致正常人类“降格”的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未来目标,而且它并不遥远。
然而,网络文学终究还是文学,数字人文终究还是人文。譬如我国古代对文的界定,我们不妨视网络文学为广义的文学;又譬如未来很难再有自古以来西方相对“单向度”的文学流派: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等,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然是广义的流派。如今,文学这个偏正结构中的文与学,同样可以由机器人或智能人“代劳”。既然谷歌阿尔法狗(AlphaGo)可以战胜围棋顶级高手、微软小冰可以作诗撰文歌之蹈之,那么由它们(或他们)来代写博士论文(或各色八股)也完全可以想见。何况我们的一些形式主义篇章正越来越模块化、程序化,越来越“网格化”(圈子化),越来越脱离本该是主要受众的作家和读者及其重要关切,却美其名曰“标准化”“国际化”。用詹姆逊的话说,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正日益成为一个信息“传播概念”。用媒介学家麦克卢汉的话说,则几乎是媒介之外,一切皆无。但媒介、信息(二者相辅相成),或者网站和写手,它们(他们)的背后并非没有推手或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般的内核。而这个推手、这个内核也许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及其剩余价值。盖因无论网站还是写手或粉丝,在资本面前只不过是木偶般的道具。当然,出于“和而不同”或貌合神离、神合貌离的利益诉求,网站、写手和万千粉丝既可以是共同体,也可以产生使之歧出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但前提依然主要是资本的需要,尽管表象常常使人目眩:譬如粉丝的疯狂、写手的收益、网站的红火或者“一言不合”,各奔东西。这便是人文让渡于技术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用21世纪以来网络小说如何被“网格化”(在此也即类型化)来佐证——当“网格化”取代了“划时代”流派思潮,文学的“扁平化”便难以避免。
文学原理与评价体系
面对如此情状,阐述文学原理无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分明是人文之道。正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倘使取法乎下,那么我们将唯有失声。
广义上说,文学原理大致可以从几个层面切入。一是文学批评。在世界文坛,文学批评早已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专利,任何读者都可以借助大众媒介对作家作品发表意见。于是,众声喧哗,而曾经主宰文学批评的专家学者却只能在小众的文学报刊上“自说自话”。21世纪以来伊格尔顿等西方学者对此的严重关切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二是三尺讲台。从中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们在课堂上声嘶力竭的呼号,抵挡不住来自大众传媒的浩荡青冥和汪洋恣肆。三是文学史料。文学史书写历来是学院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界定经典的不二法门。然而,入史标志着作家作品被经典化,如今却变成了老黄历。不少文学史家甚至主动放弃崇高,入流大众趣味。四是文学原理。学院派通过原理学为文学立标制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悲剧设定为文学大雅,其中关于情节、语言、社会批评等方面的界定成为后世的重要镜鉴,反之便是相对脱离现实的柏拉图主义。
上述四者互有交织,难以截然分割,是故文学原理学由古至今,无数溪流汇集成烟波浩渺的汪洋大海。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从文学史和原理学两者反观自身。
作为界定经典、度量谱系的重要方法,文学史和文学原理学在我国已有近百年历史。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19世纪末由俄国人书写的。在此之前,我们固有经史子集和《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但未曾用史将其来龙去脉串联起来。早期窦警凡、黄人等的《历朝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等其实是偏离文学本体的所谓文学史,及至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创作《中国小说史略》,我们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如今,我国拥有各类文学史著作凡3000余种,其中包括数百种外国文学史。问题是数量对应价值标准的紊乱。这在有限的文学原理学著述中表现得更为清晰。从马宗霍到如今多种原理学著作,我们不难看出它是如何从窦警凡、黄人式的抱守残缺发展到全面苏化和全盘西化的。当然,这是大处着眼的一种扫描方式,难免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之嫌,其中的是非得失也无法在此铺陈。但问题显而易见,那便是标准的阙如。因此,如何建立既有内核、又有外延的同心圆式文学评价体系和文学原理学研究已迫在眉睫。这也是“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难以回避的中坚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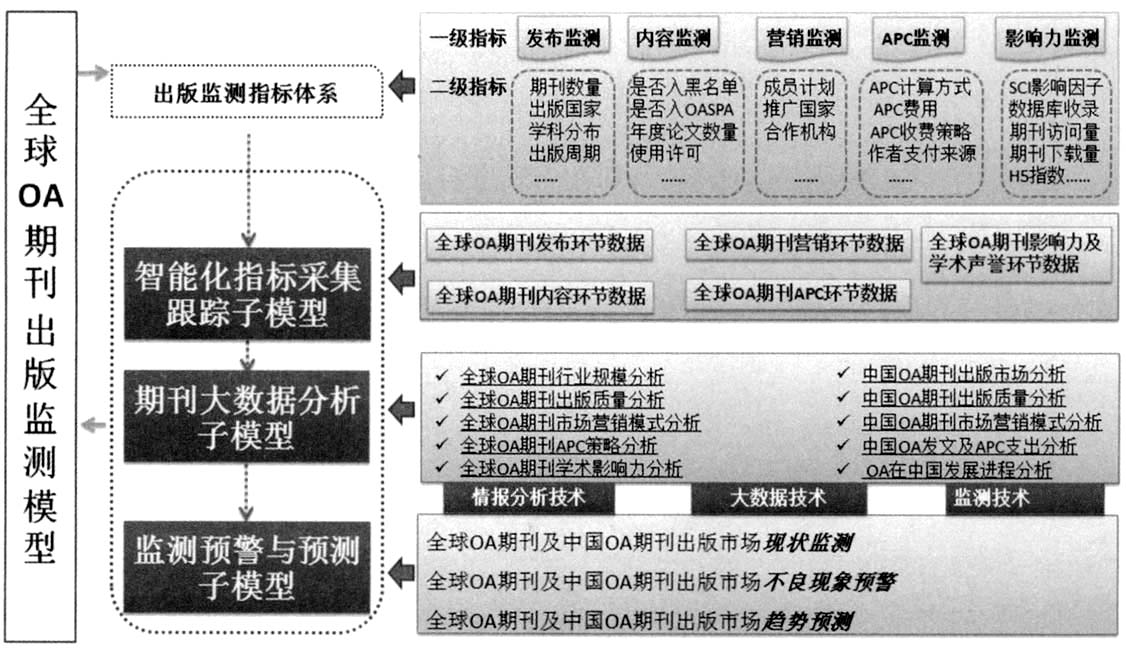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