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密切,但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独立存在的艺术类型,自然有其独有的美学形态与魅力。随着小说《芳华》被搬上大荧幕,研究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性是个有趣的话题。对于伤痛的处理,小说“芳华”与电影“芳华”有着相似却不同的注解,特别体现在对青春、人性和时代的不同阐释上,值得关注与深思。
关键词:《芳华》;文本间性;青春;人性;伤痛
我国电影在发展的过程中,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两者之间关系的变迁成了我国电影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第三代”到“第五代”导演,电影基本是拄着文学这支“拐杖”一路走过来的。导演张艺谋就曾坦言道:“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1]但是,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密切并不代表两者趋同,两者都作为独立的艺术类型,自然有其独特的美学形态与魅力。就现状而言,当前大多数人还是把从文学改编过来的电影以是否贴近原着作为评价其好坏的标准,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文学与电影作为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同一内容的表达必然会存在差异,引起热议的《芳华》也不例外。虽然是由严歌苓亲自担任编剧,电影版《芳华》与小说版《芳华》在情节、艺术处理上还是存在不小的出入,仅从前者的英文名“Youth”与后者的英文名“You touched me”就可窥见一二。对于青春,我们向来赋予美好、珍贵的标签,但习惯性的赞美与欢呼却难以掩饰成长中的伤害与被伤害。而对于伤痛的处理,纸墨“芳华”与银幕“芳华”有着相似却不同的注解,本文将从青春、人性和时代三个方面来探讨两个文本的“间性”。
一、青春的反思与挽歌
莎士比亚曾说,青春时代是一个短暂的美梦,当你醒来时,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对于《芳华》的电影与小说来说,或者说对于冯小刚与严歌苓来说,“青春年代”就是老红楼里文工团的那段芳华,短暂是必然的,消失了是必然的,但是不是“美梦”,或者这个“美”的程度有多大,这是值得更进一步考虑的。
在小说中,同样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的老红楼还是有梦的,多数的梦都美,也都大胆。”[2]但读过《芳华》就知道,这一句并不能给全书定下一个“明媚”的基调,相反,这段青春留下的“伤痛”痕迹更明显,疤痕一直都在,挥之不去。这部最新创作的长篇被认为是具有严歌苓浓厚个人自传色彩的小说,文中的叙述者萧穗子就是她自己。小说紧紧围绕“触摸事件”展开,以萧穗子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回忆了年少时的文工团生活及之后的人生经历,时间跨度近四十年。而严歌苓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也坦言:“萧穗子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表述出的所有反思和忏悔,当然跟我本人的真实感情紧紧关联。我为小曼的行为着迷,为她许多不可理喻的行为感到难为情,但更为形成她那些行为的社会和我们这个集体感到难为情。我痛恨把小曼扭曲成那种畸形人格的社会和集体的偏见和成见,正是这些偏见和成见升温成了迫害。”[3]从这些表述来看小说,会发现它不是一篇简单的对已逝青春的回忆和“致敬”,而是今天与过去的对话,是作家严歌苓对过去这段青春的重新认识与发现,而这个重新认识与发现的过程是痛苦的,忏悔的,“难为情”的……可以说,在小说中,青春的伤痛是大于美好的。
如果说小说是以萧穗子或者说是严歌苓的视角来谈这段青春,那么电影《芳华》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同样出身于文工团的导演冯小刚对已逝“红楼青春”的情感表达。小说重点在于围绕“触摸事件”写刘峰、何小曼、林丁丁、郝淑雯、萧穗子等人物在这四十年间的命运与变迁,侧重于事件的叙述与议论,而对文工团的日常生活则较少展现。而电影则恰好相反,其前半部分则浓墨重彩地对文工团的明媚青春进行了展现。电影一开头何小萍刚到文工团就看到了女兵们的排练,几分钟的时间里,音乐轻快欢乐,女兵们身姿曼妙,文工团的形象瞬间鲜活。之后,关于青春期男女的躁动也时有体现,如男兵给喜欢的女兵顺东西,男女兵在泳池嬉戏、共舞等,电影在这些细节之处的表现是小说中所没有的,而这些细节正是“青春芳华”最生动、最美好的画面。冯小刚在一次电影宣传时也提及,《芳华》是给了他一次机会,一次回忆部队文工团所有关于青春的美好的审美体验。可见,对文工团及文工团那段青春芳华的追忆与怀念,是其电影所要表达的重点。而这种感情的放大则体现在了电影中文工团解散前夕众人共饮同唱,不忍分别的场面,这是全片“文工团情谊”最深厚的一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工团解散的情节是小说中所没有的,在电影剧本中加入这场告别的深意也是很明显的,这场告别戏就是冯小刚以及那一代人的告别青春的表达。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简单地说电影中所展现的“青春”是美好大于伤痛的呢?明显不能。张颐武在评价《芳华》时认为电影里所展现的青春本身充满矛盾性,“青春有悔,青春无情;但又是青春无悔,青春有情”[4]。一面是刘峰与何小萍的让人感慨和心碎的故事,另一方面是关于青春的无尽缅怀和追忆。电影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之中,让受众在嗟叹人性暗淡处的同时,对青春的灿烂处也充满留恋。而关于《芳华》这两个版本对于“青春”伤痛的不同表达,明显是两者叙述的角度与表达侧重点的不同所造成的。严歌苓是置身其中,而冯小刚更像是一个旁观者,通过看别人的故事来缅怀青春。
二、人性的揭示与修饰
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芳华》其中所揭示的最大的“伤痛”应该就是“人性之痛”了。当然,两个文本对人性的探讨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别。从小说来看,其所要表现的主题在于对“人性”的追问与反思。所以对于“人性”,小说全篇都在深刻揭示,让我们意识到欺负小曼,批斗刘峰的人,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即我们自己。小说中的“人性之恶”同样是随着“触摸”事件的推进而不断显现的,当“触摸”发出之后,其所引发的伤痛不仅改写了刘峰一个人的命运,与之相关的何小曼、林丁丁、萧穗子、郝淑雯等人同样在内心深处受着折磨,这是一辈子都无法抹平的创伤。严歌苓接受访谈时也曾明确表明《芳华》的主人公是何小曼,讲述的是人性的迫害本能[3]。所以整篇小说在深刻的剖析人性的同时,也沉浸在强烈的负罪感之中,它无情地告诉我们:尽管大多数人会喜欢电影里的何小萍,会喜欢小说里的何小曼,但现实里是这样的人物是不会受喜欢的,否则她也就不会精神失常了。——这就是令人憎恶,令人悲悯的人性。与小说将“人性”作为重点表现对象不同,张倩玉认为电影《芳华》的“主角”是文工团,文工团的兴衰才是影片真正的表现对象[5]。影片紧紧围绕“文工团”这个核心展开,前一部分叙述了文工团的环境、生活以及解散;而后半段对文工团解散后的种种展现,也只是为了进一步阐明文工团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这个观点是与上文所论及的影片所表现的重点在于对“文工团”青春的追忆与缅怀是契合的,存在一定道理。正是由于影片表现的重点并不在“人性”,以及影片诞生时代的限定,比如它不可能过多地将人性的阴暗与那个扭曲的政治环境相联系,比如它即便想要表现人性的黑暗也必然会有所顾忌与保留,所以电影中对人性的描写是点到为止,留有空白的,当中还有温情的基调。
两个文本都对刘峰的“雷锋”品质进行了具体的展现。小说中明确地提到了刘峰的外号“雷又锋”(又一个雷锋),刘峰正如同“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的雷锋一样,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他要以无数平凡的小事成就不平凡的自己。而在电影中,刘峰是那个帮忙在大街上追猪、在抗洪救灾中弄伤腰、将进修大学的机会拱手相让的“毫无私心”的好人,他的好,别人望尘莫及。两个版本的不同在于,小说具体地写了“触摸事件”发生后的全过程,从事发后林丁丁与郝淑雯的谈话,林丁丁向声乐老师的告密,以及审讯过程都写出来了,特别是对批斗会的描写,人性之恶才真正爆发。“我们的孩提时代和青春时代都是讲人坏话的大时代。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会格外勇敢,人群会格外拥挤。”[2]而电影对于刘峰被集体“驱逐”的场景给予了淡化,并没有展现批斗刘峰的场面,似乎有意保存文工团的一点温情,也使人性的丑恶得到了一定的稀释。
严歌苓在一次访谈中提道:“尽管我们被‘平凡即伟大’的价值观误导,我们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的人性是从来没有信服过的。女性的心理基础,集体潜意识,是百万年的进化决定的,那就是雌性生物永远选取群落里最有力量、最凶猛、最有权威的雄性作为她后代的雄性基因。”[3]林丁丁能接受摄影干事和内科医生的示爱,却不愿接受刘峰的示爱,不只是因为刘峰在她心里应该是一个完美得毫无欲念的形象,也因为刘峰的地位不如前两人。好人虽伟大,却是平凡的,林丁丁骨子里的骄傲不允许她屈就于一个平凡的男人,她在婚姻方面首先考虑的是利益问题。在小说中,她先后嫁给了父亲是副司令的军事科学院研究生、移民澳洲的商人。而质问林丁丁为何不愿接受刘峰的郝淑雯,尽管认为刘峰是一个值得爱的好人,但要换成自己,却也无法和刘峰在一起。她可以把同情、善意、甚至崇拜都给好人,但要论及爱情婚嫁,还是把好人关在门外。郝淑雯最后与一个“军二流子”结了婚,也不无讽刺。而小说对这“雌性集体无意识”的深度剖析是电影所不能及的。
小说里的何小曼,电影里的何小萍,可以说都是被人的冷漠与偏见所迫害的对象。一“曼”一“萍”,前者是因为考虑到其父亲是个文人,后者则应是“飘零无依”之意。家庭对于何小曼(萍)的影响不言自明,可以说其孤僻、倔强、自虐、求死等性格倾向主要源于她不曾被家人接纳,没有得到过正常的关爱。小说对她的家庭与成长背景进行了具体的描绘,何小曼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因为不堪众人的诋毁与攻击而上吊自杀,从此何小曼随着改嫁的母亲过上了忍气吞声的生活,作为一个“拖油瓶”,她必须压抑自己的全部渴求。在弟弟妹妹出生后,她更是得不到一丝温暖,想要母亲的关爱只能靠熬出病,想要红衣服只能靠偷。电影则对何小萍的家庭进行了简化处理,只是从侧面交代了她父亲被下放到劳改场,多年未见女儿,最后凄惨去世。其间提到了父亲由于不想牵连女儿,十几年来都克制着不曾与她联系,在特殊的时代下父爱有着别样的表达。同时刘峰也帮忙隐瞒了她的家庭背景,这些细节中所体现的温情基调也是小说所没有的。
家庭的冷漠让她选择逃离,但让何小曼(萍)没有想到的是,她将进入的文工团同样是个对她冷漠的集体。在文工团对何小曼(萍)的态度方面,两个文本相差不大,但相较而言电影中文工团对于何小萍的态度更恶劣。“军装”事件中,虽然林丁丁没有过多追究,但众人的“问罪”与“搜赃”却在一开始就将何小萍排除在集体之外。之后,她们始终高高在上,嫌恶何小萍的馊臭,视其为笑话,还质疑其品质。而在男兵中,何小萍也同样不受欢迎,没人愿意和她搭档跳舞。萧穗子似乎是文工团中除了刘峰之外对何小萍最友好的人,她看不惯其他女兵对小萍的所作所为,但在“乳罩造假”事件中,萧穗子肆意地嘲笑却表明她也不可能对别人的隐痛感同身受。萧穗子的地位是优于何小萍的,因此,她更愿意与其他女兵站在同一阵线。正是由于家庭与文工团对她的排挤、偏见、冷漠,让她不得已将自我封闭,自愿在边缘游走,所以当演主角的机会到来时,她装病拒绝结果引来了处分,当在战场上立功成为“英雄”时,她无法适应从边缘一下子成为“主角”的反差而进入了精神病院,令人唏嘘。但不可否认,人性的偏见与冷漠是摧毁何小曼(萍)的最大凶器。
“能否呈现原着小说对特定时代人情的展示、人性的剖析,成为严歌苓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关键。但电影受到市场、形式的限制,有时无法像小说那样充分展开。”[6]这或许就是两个版本在表现人性时存在差异的原因。
三、时代的宽度与深度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芳华》的电影还是小说都无意于对某个特定时代进行批判与强调。但从对比中还是可以看出两者存在的差别,小说的时代背景跨越了四十年,对这四十年间的变化与人物的变迁都有叙述,每个阶段都有体现。而电影则侧重于表现“文革”及中越战争的时代背景,对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则作了简化处理。影片前一部分所表现的“文工团”恣肆青春与“中越战争”是从小说中由虚变实,而对后二十年时代的展现反而由实转虚了,这种叙事重点的迁移所造成的平面和散点,注定无法形成与小说一样的时代纵深感,从而也无法使观众对人物产生强烈的同呼吸的命运感。
严歌苓大部分的小说都是以“文革”为叙事背景,但她却从未在作品中对某个特定的时代进行集中而正面的抨击与批判。她作品的侧重点在于人的存在而不是社会的存在,她只是把“文革”等符号化存在于作品中,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展现特殊的时代与环境对人的改变和影响。在《芳华》的小说中,对于“文革”背景没有过多的强调。与外面时代的风起云涌不同,此时的部队文工团就更像一片净土,仿佛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作者似乎有意将文工团的这群人与时代隔绝开来,他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外面的世界,只需要刻苦练功以及完成表演任务即可。或许只有想到何小曼父亲的死,以及文工团集体对刘峰的“驱逐”,我们才会想起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习惯了把背叛当正义,习惯了揭发与出卖的年代。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在时代设定上却有着较为刻意的安排,如文工团所住的红楼的布置:毛主席的画像、标语的张挂,大街上人们的游行,毛主席去世后文工团表演曲目的变动等。但这样的设定也只是为了电影内容与结构的完整性,这样便于简要地交代人物的家庭背景,如交代了何小萍的父亲是被“文革”所改造的对象,为她的性格发展与被排挤作了一定铺垫。
对于“中越战争”,小说中没有对此进行正面描写,只重点记叙了刘峰在严重负伤时仍先指引驾驶员给战士们运送给养、何小曼搀扶腿部负伤的男护理员回野战医院的这两个情节。而电影对于激烈的战争场面则有更为惊艳的表现,“6分多钟的长镜头,一气呵成,用快速折返运动创造了一种急促、紧张、残酷的氛围,更是体现了艺术运用的能力和审美表达的勇气”[7]。这个造价700万的六分多钟长镜头,让我们重新记起了那场战争,记起了为国家奉献与牺牲的英雄。很多人都评价说冯小刚将青春与战争这两个热门因素进行结合,使其达到了更好的商业效果。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冯小刚没有忘记身为一个电影人的责任,文艺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与能量,并不是只有商业和娱乐。尹鸿对影片《芳华》评价极高,认为它是2017年的一部“现象级”电影。而之所以称为“现象级”是在于影片所表现的几乎都是当下“复杂中国”的敏感点,比如对1976年之前这段历史的还原,对西南边陲那场战争的再现,对“文工团”的特殊生活环境,以及退伍军人、战斗英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遭遇等的表现[7]。触及那么多的话题还能公映,这样的电影实属难得。这样的《芳华》必然会引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历史、关注人、关注“雷锋”符号之后的人性,这便是价值所在。在当今“娱乐至死”的大环境中,创作有人文关怀的、有审美追求的电影所面临的困难必定远远大于拍摄那些“娱乐性”的电影。所以,《芳华》值得肯定,冯小刚值得肯定。
小说与电影在对“时代”的表现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各个人物命运的抒写上。相比较而言,小说对市场经济背景下各个人物命运的变迁都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这部分的篇幅并不少于小说前半段围绕“触摸事件”的叙述。可见,这一阶段人物的叙述同样是小说所要表达的重点。而就电影的整体而言,其重点还是放在部队文工团时期的描绘,对市场经济时期的内容则做了简化的处理,对这段时期的人物命运也做了一定的美化处理。在电影中,刘峰没有与站街女小惠有过纠葛,也没有生病、去世,而是和何小萍相守;林丁丁没有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而是如愿嫁人、移民澳洲;郝淑雯也没有嫁给军二流子,没有独守空房、最终婚姻破裂,而是依靠南下经商的老公生活富足。而这些都是小说中的他们实实在在经历过的生活,或者可以说是苦难。想当年那群在舞台上风光一时的文工团少男少女,如今婚姻失败、生活失意、穷困潦倒、患病逝去……这样的对比与差距不得不让人嗟叹命运弄人。
电影的结尾是萧穗子的一段旁白:“我不禁想到,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可还是不难看出岁月给每个人带来的改变。倒是刘峰和小萍显得更为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愿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荧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而小说的结尾是刘峰的追悼会,一个只有五个人收到通知三个人在场的追悼会,而且这场追悼会并无安宁,还出现了市场经济下租用灵堂而出现的闹剧。昔日的“雷又锋”,今日的闹剧,对比起来不免滑稽。他是个当今谁也不需要,谁也不尊重的人了。而那个会爱的刘峰,早在林丁丁喊救命的时候,便已经死了。而对于何小曼,“她潜意识里有求死之心”。
细细品味影片,会发现其就像严歌苓紧握手中的瓶子,而瓶子里装的是冯小刚的酒,浇的是一个时代的块垒。而纸墨“芳华”则更像是严歌苓自己珍藏的高脚杯,里面所盛的是她自己所酿造的红酒,馥郁芬芳,历久弥香。总之,《芳华》的两个文本之间因为关注重点的游离,情感指向的不同,表现手法的差异,呈现出耐人寻味的文本间性。
参考文献:
[1]张鸿声,王晓云.中国电影与文学的关系[N].文艺报,2010-07-07.
[2]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3]舒晋瑜.反思平凡的英雄、雌性集体潜意识和最凶猛的雄性基因严歌苓:我们被“平凡即伟大”的价值观误导了[N].中华读书报,2017-07-26(18).
[4]张颐武.《芳华》:重访青春的残酷和美丽[N].社会科学报,2018-01-04(8).
[5]张倩玉.论《芳华》的青春叙事[J].电影文学,2018(18):94-96.
[6]宋菲.严歌苓文学创作及其影视改编研究[J].电影文学,2017(19):97-99.
[7]尹鸿.这一年,有部电影叫《芳华》[N].中国电影报,2017-12-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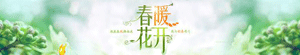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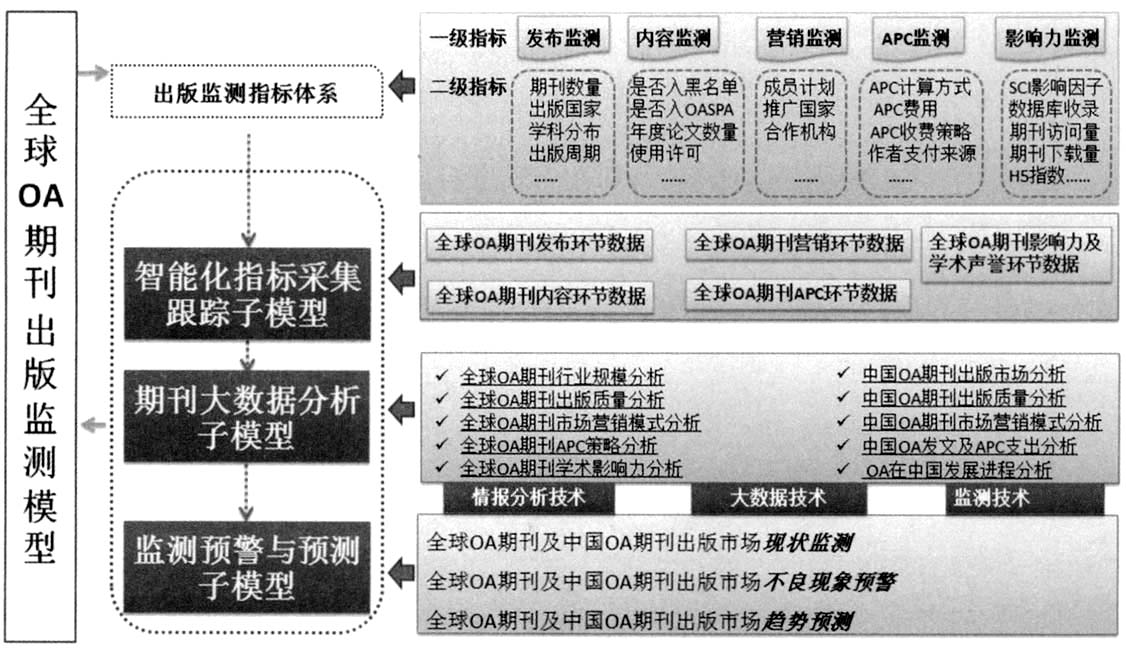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