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中国,诗歌选本编纂与诗歌创作的阶段性演变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倾向,使得彼时的选本以工农兵诗歌选本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启蒙思想的重建,诗歌选本编纂开始向精英化转变。与这一改变而来的,是诗歌选本功能的变迁和诗歌选本类型的多样并存。诗歌经典化的文学史建构功能和文学现场的构筑功能成为此时诗歌选本的重要功能。
关键词:诗歌创作;选本编纂;文学变迁
诗歌(包括词)选本自古以来十分发达,近现代以来亦是如此。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而言,1949年前后有所不同。其中,1949—1979和1979—2009前后两个三十年具有研究的典型意义。1949—1979的诗歌选本与建国前解放区的诗歌选本a有一脉相承之处,即偏向于民歌或诗歌的大众化倾向。此一时段的诗歌选本也与小说、散文等选本颇不相同。这一倾向自1979年后才有大的改变。1979—2009年这30年的诗歌选本编纂,接续1949年代以前的倾向,诗歌创作回归精英化的同时,诗歌选本的精英化趋势也日趋明显。
一、诗歌的大众化与中国向来有之的民歌传统有关。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诗歌选本中,文人诗歌选本很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相比之下,工农兵诗歌则数量甚巨。除了有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之外,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百首》(1—3集)、《新民歌三百首》(1959)1、《上海新民歌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莺歌燕舞》(农村读物出版社,1977)等等。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诗歌选本中,新民歌占所选诗歌总数的绝大多数。这一情况的出现,固然有新民歌运动的全国推广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诗歌最为容易走向大众化有关。与此相关的,是新民歌的无名化倾向。很多新民歌的作者都是没有具体作者的。比如收录于《新民歌三百首》中的那首着名的新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陕西)”a在这里,作者的无名化其实是作者的名字的泛化的另一种表现。即是说,作者的无名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大写的人名——即“人民”——作为背景式存在。这是“人民”在写作,其主体是工农兵作者。这一逻辑下,很多时候,有没有作者或者说署不署作者名,其实是没有区别的,也是不证自明的。
但是,就选本编纂而言,这一诗歌创作的无名化倾向的出现是有过程的。可以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几个诗歌选本为例。《诗选(19532·9—1955·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3)可以看成是建国初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精选。“这个集子里的作者有年长一辈的和在历次战争时期中出现的诗人,也有在不久以前刚刚显露才能的青年作者;有专业的诗人,也有农民、工人和部队中的诗人;有汉民族的诗人,也有少数民族的诗人。”b既然是总结和回顾,这一诗集其实带有构筑诗坛格局和秩序的意识形态功能,从前面所例举的作者构成中可以看出新中国建国后的诗人群体的构成。在这一群体中,工农兵诗人占了一定比重,出现了农民诗人王老九,工人诗人李学熬,军人作者李志明,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作者。也有集体创作的痕迹,比如《青年农民和布谷鸟》的署名作者是“青罕农村俱乐部集体创作故城县文化馆王德通执笔”。但总体上,这部诗选仍旧以专业作者为主。这是就诗歌作者队伍而言。就形式而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诗歌创作的民歌化,比如说苗得雨、张庆田的诗,是以“民歌形式”c写就。这一选本的另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于,收录了一定数量的民歌、快板、歌词和唱词,比如说有署名的民歌《民歌八首》,署名“重山”的唱词《工地两姑娘》,署名“佟志贤”的歌词《勘探队之歌》,山歌《蓝天高来绿水长——山歌联唱》,等等。其中还出现有经过专业作者整理过的诗歌,比如说《阿细的歌》,由彭肃非整理。相比之下,《1956年诗选》则具有过渡性。这一过渡性即表现在文人参与到民歌的整理中去。其中有署名山川搜集的《陕西新歌谣》。搜集的新歌谣,所做的常常只是搜集工作,很少有改动。而像周良沛整理的《藏族情歌》则带有文人化的倾向。此外,《1956年诗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收录了旧体诗。这里的旧体诗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旧文学,而应视为新文学的一部分。这是旧瓶装新酒。与毛泽东的论述有关,即所谓古典加民歌的新诗发展道路的提倡有关。《1956年诗选》某种程度上正是毛泽东诗歌发展道路提倡的结果,这里的诗歌主体仍旧是知识分子作家。从前面的两部诗选可以看出,建国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诗歌创作的两种明显倾向,即民歌化和文言化,而这,恰好对应于毛泽东提出的新诗发展道路的两端:古典和民歌。也就是说,建国后的诗歌创作,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民歌(新民歌、工农兵诗歌)、旧体诗词和文人新诗(专业作者诗歌)。这在《1957年诗选》中有明显的表征。较之前面两部诗选,这一诗选的不同的地方在于,民歌选入的数量有较大幅度提升,专业作者整理的民歌越来越多,旧体诗词创作蔚然成风,其占篇幅也从《1956年诗选》中的24页(占比5.8%),上升到61页(占比12%)。
那么问题是,这三部分构成中,应由哪一部分主导诗歌创作格局呢?《1958年诗选》(《诗刊》编辑部编选,作家出版社,1959年4版)的编选很有症候性。这一选集的目录中,标明作者的有114人次(除毛泽东的《蝶恋花》和《送瘟神》外),没有标明作者的有35首。但若翻开内容看,便又发现,这35首中,并不都是没有作者的,其中很多都有署名,或标明集体创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目录中不标明作者,内容中却注明作者这一现象呢?应该说,标与不标,并非无意为之,相反是有某种深意在的。这种深意表现在,目录中未标明作者的那些人,大都是没有名气的、刚刚创作诗歌的,或者说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兵作者。而标明作者的那些,则是专业诗人,或者是早有名气的工农兵作者,如王老九之类。从这种区别可以看出《1958年诗选》的意图所在,即诗歌创作的主流或主部,仍旧是要以专业诗人(包括那些成名的工农兵作者)主导,虽然这些专业诗人也都在从事古典加民歌的诗歌写作。而这,也意味着,在关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中,编选者仍旧侧重于提高,尽管这里的提高并不真正有多高。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专业作家(诗人)仍是主导力量,而不是普通工农兵大众。因为毕竟,这类诗选的编选者是由中国作协主管的《诗刊》编辑部。
而也正是这种分野,可以说构成了20世纪50—70年代诗歌选本的两种景观,一是以专业诗人为主的诗歌选本,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作协编选的诗歌年选,还有各地作协编选的诗歌年选、阶段诗选,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十年选集·诗选(19495—1959)》(1960)、《江苏诗选(19496—1959)》(江苏人民,1962)、《山西诗选(19497—1959)》(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等等。《上海十年选集·诗选(19498—1959)》所选诗歌中都有署名,《江苏诗选(19499—1959)》同《1958年诗选》类似,《山西诗选(194910—1959)》中采取的策略是在目录中的作者前面标明作者身份,如农民、工人等等。另一类诗歌选本则专注于工农兵作者或新民歌,这些选本数量很大。如周扬、郭沫若编《红旗歌谣》,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北京的歌——工农兵诗选》(1973),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工农兵诗选》(1972),湖南新苗月刊文学社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跃进山歌满洞庭:湖南新民歌选》(1959),暨南大学中文系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荔枝满山一片红:华南新民歌选》(1959),山西火花文艺月刊社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粮棉堆成太行山:山西新民歌选》(1959),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唱得长江水倒流:安徽新民歌选》(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编选出版的《上海新民歌选》(1975),《山西群众文艺》编辑组编的《山西新民歌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74),《莺歌燕舞:农业学大寨新民歌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77),《莺歌燕舞:新民歌选》(农村读物出版社,1977)等等。
二、虽然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专业诗人选本和工农兵诗歌选本的分野,但要看到它们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也就是说,专业诗人的选本主要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在这期间是两分天下,但自60年代以后,专业诗人选本逐渐被工农兵诗歌选本或新民歌选本取代。这种情况的改变要到“新时期”以后。“新时期”以来,诗歌选本编纂的构成中,仍旧有民歌选本出现,但这时是作为通俗文学的面目出现,其地位也由主导降为附属和补充一级了。
这一转换是于无形中完成的,其完成有赖于“新时期”以来启蒙主义的重提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而在大众化的1950—1970年代,不论是民歌还是新民歌,是不存在雅俗之分的,当时的说法只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关于这点,可以以贾平凹的长篇《秦腔》作为佐证。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秦腔在1980年代以来所遭受的极大冲击,正说明民间文学的式微,其原因既包括有市场逻辑的因素,也包括文学上雅俗对立格局的重建。这种转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选(194911—1979)》中有明显表现。“除了《天安门诗选》部分包括若干旧体诗外,旧体诗、儿童诗、歌词、民歌一律未选”a。这里,表面上看只是选或不选的问题(即除了《天安门诗选》部分外不选旧体诗和民歌),但其深层次的表征却是,旧体诗和民歌不属于主流诗歌文体,它们是作为民间文学或旧文学出现。诗歌创作主要是指新诗,此前诗歌创作的三部分构成,此时应是一部分构成。但问题是,既然不选民歌,新民歌应不应该选,其属不属于主流诗歌?从这一诗选的编选篇目来看,其态度和立场较为模糊,这一诗选中选入了部分工农兵诗人的诗作,比如说农民诗人王老九的《想起毛主席》等诗。王老九在20世纪50年代常常是被作为民歌诗人即“民歌手”看待的a,他的诗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新民歌”的范畴,对于这一些诗人的作品,《诗选(194912—1979)》却收入其中,这一选的行为正透露了当时的矛盾态度和过渡形态。再来看《诗选(194913—1979)》的姊妹篇《诗选(1979—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4)。这是由《诗刊》社编选的,与《诗选(194915—1979)》具有“衔接”b关系,其中所选诗歌,不见民歌和新民歌的影子,更不用说旧体诗了。
民歌和旧体诗自诗歌选本中的消失表明的是诗歌创作的精英化,而这也带来或表明了诗歌选本编纂功能的某种新变,一是通过诗歌选本中的编选以达到诗歌经典化的文学史建构功能,一是通过诗歌选本建构诗歌流派或通过诗歌年选的编选以建构文学现场的功能。第一类选本有代表性的是谢冕、杨匡汉主编的《中国新诗萃》2卷(包括20世纪初叶—40年代和50年代—80年代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出版和1985年出版),周良沛编《新诗选读111首》(花城出版社,1983年16),张永健编《中国当代短诗萃》(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17),吕进主编《新诗三百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永健、张彦芳主编《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8),牛汉、谢冕主编《新诗三百首》(3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新诗三百首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诗选》(1990年)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选》(2000年),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等。第二类诗歌选本主要以思潮流派诗歌选本为主。这一类选本很多,有《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白色花——二十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彼得·琼斯编《意象派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年)、吴欢章主编《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周良沛主编《七月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9)、钱光培选编《中国十四行诗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等等。这一类选本中,尤以朦胧诗、新潮诗歌为最多。1980年代,朦胧诗选为数不多,最有代表性是阎月君等人编选的《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五人诗选》(1986)。另外还有中国作家协会江西省分会和《星火》文学月刊社联合编选的《朦胧诗及其他》(1981,内部读物)、《朦胧诗精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等。新潮诗歌选本则有《探索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唐晓渡、王家新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朱先树编《未名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骚动的诗神——新潮诗歌选萃》(花山文艺出版社)、溪萍编《第三代探索诗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情绪与感觉——新生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等。谢冕、唐晓渡主编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6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包括《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鱼化石或悬崖边的树:归来者诗卷》《与死亡对称:长诗、组诗卷》《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另外还有黄祖民主编的《超越世纪:当代先锋派诗人四十家》(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20),等等。相对而言,诗歌年选则带有阶段性特征。诗歌年选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常态,而后逐渐消失,21世纪重又出现。一定程度上,诗歌年选的编选对于建构文学现场的意义,表现在构筑代表诗人,而不在于诗歌经典作品的选择上。
就文学现场的参与的方式而言,诗歌选本与小说选本编纂实践颇为不同。小说选本除了年选和思潮流派选外,还有争鸣作品选和获奖作品集两大类。获奖诗歌选(集),在20世纪80年代偶有出现,比如《诗选(197921—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22),其中“上辑”部分收录的是“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获奖作品”。另外还有蓝棣之选编:《当代诗醇——获奖诗集名篇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获奖诗人诗歌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23)。诗歌争鸣作品选则更少,有代表性的是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争鸣诗精》(1996)和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争鸣爱情短诗抄》(1991),而即使是综合性的争鸣作品选,如北京市文联编选的《争鸣作品选编》中入选争鸣诗歌(朦胧诗潮除外)也只有2首,而小说则有17篇。如果说争鸣主要发生在小说领域,争鸣诗歌选的量少相对还好理解;诗歌评奖也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评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获奖诗歌选(集)却很少。这说明了什么?可能,这与诗歌和小说体裁的不同有关。也就是说,诗歌是主情的,而小说则倾向于叙事。争鸣主要是针对小说叙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相比之下,除了作为一种写作风格曾被引起激烈争论(朦胧诗最初被批判即与其写作风格上的“朦胧”有关)外,诗歌很少以其内容引起争议。获奖诗歌选,比如说蓝棣之选编:《当代诗醇——获奖诗集名篇选萃》和《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获奖诗人诗歌选萃》。后者只是打着“获奖诗人”的名号,其实并不是获奖诗歌选,其某种程度即是80年代诗歌选a;而前者也只是以“文学性”的名义,对获奖诗集进行一次再度精选。简言之,这两部诗集的编选,与获奖的关系都并不大。即是说,获奖诗歌选的编选,与获奖本身关系并不大。获奖诗歌选,某种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选本。获奖诗歌选与文学现场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关系。不难看出,主情的诗歌,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诗歌选本参与现场的方式,往往更多以思潮流派诗歌选本和诗歌年选的面目呈现。
这里需要注意,诗歌流派选本的编选,最开始是以文学史选本的名义出现的,也就是说,最开始出现的诗歌流派选本主要是现代诗歌流派选本,而不是当代诗歌流派选本。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九叶集》《七月诗选》《白色花》等等。这说明,前面所说的两种倾向,只是一种大致的分类。事实上,现代诗歌流派选本,作为一种文学史式选本,仍旧是以批评的方式在参与文学现场的建构。比如说周良沛编《七月诗选》,周良沛是诗人,诗人编诗选,其意味格外令人寻味。按他自己的话说这“完全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编选‘七月’派的诗”b,但换一个角度看便会发现,这里的“文学史的角度”其实又很可疑,因为这是以选本编纂的方式对“七月派”的命名和正名,以恢复它的文学史地位c。也就是说,“文学史的角度”其实是一种循环论证。如若联系周良沛编选的《新诗选读111首》(花城出版社,1983年24),便可看出,周良沛对“七月派”的倚重,其实仍是一种新诗批评观。在这一《新诗选读111首》中,周良沛并没有选入“五四”以后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代表诗人诗作(比如李金发、穆旦等九月派诗人),即使是戴望舒和冯至,也是选择他们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选入的冯至的作品是《雪中》《饥兽》《人皮鼓》,戴望舒的诗选择的是《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示长女》。这一诗选中也收入了朦胧诗人的作品,比如舒婷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和北岛的《回答》,但周良沛的解读的角度却是截然不同的:《回答》中“人民正义凛然的气概,通过缜密的诗的结构表现出来??这首诗和《扬眉剑出鞘》,是诗的气质极其相似、艺术风格又迥然不同的作品”d。也就是说,周良沛并不是从朦胧诗的流派,而是从北岛这首诗的思想内容的表现方式的角度高度肯定这首诗的。可见,周良沛仍旧是一个现实主义诗歌风格的提倡者。他编选《七月诗选》的意图,很大程度上在于通过诗歌选本的编选达到他对现实主义诗歌风格的肯定,这一点在他另一本带有诗歌史性质的诗歌选本《新诗选读111首》中亦有体现。联系此时的语境,便可做出判断,周良沛是通过诗歌选本的编选提出自己的诗学观点和对当前诗歌创作的批评态度的:“对任何诗人都是这样:个人的艺术个性在思想感情通向人民时表现出来,就可能写出被人称道的好诗;否则,目光短视于个人狭小的天地,就只能只是自私、阴暗、卑琐的感情的表现”a。这段话是紧接着对舒婷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的高度肯定后提出来的。在这句话之前,周良沛指出:“这首诗,从一些意象与抒情的方式,更看到这种影响(即外国诗的影响——引注)的作用。但‘飞天’袖间的花朵,总蕴含着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感情,才使这种作用成为有益的”b。周良沛对朦胧诗的某些批评态度,至此已是呼之欲出。
诗歌选本编纂的大盛,是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诗歌选本编选出现了高峰期。其中出现了三套具有代表性的大型选本。一套是谢冕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一套是洪子诚、程光炜主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30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一套是谢冕主编的《百年新诗》(10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三套之外,还有洪子诚、奚密、吴晓东主编的《百年新诗选》上下两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5),李朝全主编《诗歌百年经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26),陈超主编《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两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柯岩、胡笳主编《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上下两卷(作家出版社,200527),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家经典诗歌系列”,其中诗歌包括《九叶派诗精编》《朦胧诗精编》《新月派诗精编》《湖畔社诗精编》《最美诗精编》等,《第三代诗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唐晓渡、张清华选编:《当时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1979—2009)》(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吕叶主编:《70后诗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28),张清华主编《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东方出版社,2015年)等。另外,新诗年选重又恢复,并且出现了好几种版本。
这样一种大盛,显然与新诗百年有关。即是说,新世纪以来诗歌选本虽然仍旧可以从批评性选本和文学史选本两个层面考察,但其时代性特征却又是很明显的。其时代性表现在,这些综合性或大型诗歌选本,是在“百年诗歌”的层面展开的经典构筑、文学史重述和文学观表达的。比如说李朝全编选的《诗歌百年经典》中就把歌词也纳入诗歌选本中,其中收入光未然的《黄河颂》、乔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王莘的《歌唱祖国》、晓光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同时还收录了毛泽东的两首词《沁园春·雪》和《忆秦娥·娄山关》。这也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百年诗歌,不仅仅是新诗的历史,也是白话歌词的历史。但这里,歌词只是点缀和补充。也就是说其编选的虽然都是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歌词,但这样的歌词并不仅仅是入选的这几首。从这个角度看,把歌词纳入其中就带有权宜的色彩了,并不能真正改写百年诗歌史的脉络和走向。但若比较洪子诚等编选的《百年新诗选》和李朝全编选的《诗歌百年经典》,便会发现,前者学术性更强,更注重文学史意识和美学价值,就像《编选说明》中所说“编选者对新诗历史和美学(自然)拥有广泛共识”c,而后者则倾向于以流传和影响度。虽然李朝全例举了经典的五种标准,但其最为注重的其实还是最后一种标准,即“时间和读者的检验”d,也就是流传和影响度。而这,其实反映的是两种经典观。在李朝全看来,经得起时间和读者检验的文学作品就是好的和经典的作品,而对于洪子诚等人眼里,文学史的地位仍是文学经典的重要表征。
再比如《中国新诗总系》和《中国新诗百年大典》,这两套大型选本各有侧重。前者侧重从阶段性的角度考察百年新诗,把20世纪新诗发展叙述为大致十年一个发展阶段的演变史。而后者则从代表性诗人的角度,把百年诗歌按诗人出生年月梳理出300余人规模的诗人群图谱。这两套诗歌选本,虽也注重诗歌经典的构筑和诗歌流派的梳理,但其意更在于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待百年诗歌的发展,这对此前从流派或诗歌经典的角度构筑百年新诗传统的选本编纂是一种补充。也就是说,重评不是它们的意图所在,这两套诗歌选本,通过选本编纂的形式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对于诗人,应从百年诗歌发展的阶段性和个人创作的整体历程去理解和把握,而不应特别突出其流派性或个人独创性。这或许也是更为稳妥和公允的文学史观。一直以来,诗歌史或文学史的书写,总是倾向于在流派的脉络中定位诗人或者强调诗人的独创性,而不太注重两者间的平衡。两套选本,在这方面应该是有益的尝试。从这个角度看,这两套选本其实也是在展开一种新的诗歌史叙述。
三、通过对当代诗歌选本的大致梳理不难看出,就数量而言,诗歌选本可能不及小说选本,但就种类而言,诗歌选本却要多于小说选本。
这可能与诗歌作品比较短小有关。小说选本主要就那几种类型,比如说主题题材选本、思潮流派选、小说年选、阶段选、获奖作品选、争鸣作品选等。而诗歌选本的类型却颇多,小说选的主要类型,诗歌选本基本都有,比如说小说选按篇幅分有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诗歌选本里有抒情诗和叙事诗选。诗歌选本的分类还包括诗人性别和身份划分,如《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未凡编《当代女诗人情诗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诗歌选本中有一种选本是小说选本所没有的,那就是“百首”选本。这一方面与其篇幅短小有关,一方面这也是新诗经典化的重要方式。其取意“三百”,显然有与古代的所谓《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的编选对话的意图在,但与古代这类选本又有不同。其不同在于,这类新诗选本大都具有建构新诗史的意图所在,即是说,既要注重名家(代表诗人)又要注重名作,是两方面的综合与平衡,而不像《唐诗三百首》那样,杂糅性较强,所谓三教九流皆选入其中a,或者像《宋词三百首》以某一风格为旨归,虽也具有史的气度,但难免有所偏废和偏颇。b不难看出,古代所谓的“三百首”之类选本,诗史的建构方面的功能较弱。新诗“百首”选本有《诗刊》社编《新民歌三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29),牛汉、谢冕主编《新诗三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吕进主编的《新诗三百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周良沛编《新诗选读111首》(花城出版社,1983年30),张永健、张彦芳主编《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31),蔡天新编《现代汉语110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等。
而说诗歌选本种类多于小说选本种类还指,就同一类选本而言,比如说思潮流派选本,诗歌思潮选本数量要多于小说思潮选本,比如说有关朦胧诗的选本,截至目前为止初步统计有近10余种之多,而关于第三代诗的选本,则更多。再比如说,在小说选本中按年龄划分在特定年代较为突出,比如说20世纪50—70年代,当时叫“新人”(80年代,也有“青年佳作”)。但诗歌选本分类中,年龄划分却是常态。80年代以来,以“青年”为编选原则的诗歌选本数量众多,除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诗歌年选《青年诗选》外,还有如谢冕主编《中国当代青年诗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牛汉、蔡其矫主编:《中国青年诗人十三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周俊编《当代青年诗人自荐代表作选》(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朱先树、周所同编《当代中青年抒情诗选》(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滑板露珠——青年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宗鄂编《当代青年诗100首导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阿人编《写给男人的情诗——当代青年女诗人爱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等等。20世纪50—70年代的选本编纂中,“青年”或“新人”主要是指青年工农兵,而在80年代的语境下,“青年”则是专业诗人。
诗歌选本中主题题材选本需要特别注意。这类诗歌选本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爱情诗、爱国诗、田园诗等。比如《恋歌:爱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尹仲曦选编:《爱情诗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32),李发模、陈春琼选编《中国百家爱情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林贤治编选:《金葵花燃烧的土地:新乡土诗选》(漓江出版社,2013)等。按照题材、主题划分编选诗歌的集大成者,是谢冕主编的《百年新诗》(百花文艺出版社),这是一套10卷的百年诗歌选本,包括“人生卷”、“情爱卷”、“女性卷”、“社会卷”、“情谊卷”、“家国卷”、“都市卷”、“乡情卷”、“咏物卷”、“艺文卷”。但这一大型选本,在分类上其实存在重叠和矛盾之处。其中既有题材上的分类,又有诗人身份的区分,又有表现方式上的分野,如“咏物卷”。
应该看到,主题、题材诗歌分类选本,不同于百年诗歌选,也不同于诗歌年选。如果说诗歌年选的意义在于建构经典诗人,百年诗歌选的意义在于构筑诗歌作品的经典化,那么主题、题材诗歌选本的意义则在于诗歌主题的经典化。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爱情诗选和爱国诗选,这都是历来就有的。而像谢冕主编的《百年新诗》的10大类其实是构筑了百年新诗的几大核心主题,这些主题有爱情、爱国主义、亲情、乡情等等。谢冕主编《百年新诗》的意义体现在,通过某一主题或题材,比如“情爱”主题,从中可以看出百年来的诗人围绕“情爱”上的不同表达,这种不同,其实也是百年中国人的情感史的诗歌表达。可见,诗歌主题、题材选本仅仅以一两本的篇幅,就可以浓缩百年来的情绪表达,而对于同类题材、主题小说选本而言,则需要大型的系列选本(比如乡土小说大系)才能完成。另外,通过主题、题材选本,比如说“情爱卷”,让我们看到,这不仅是永恒的主题,同时也可以说是诗人写作的惯常的主题,我们看到,诗歌史上的名家,几乎没有谁没有写过爱情或情爱诗。主题、题材选本让我们感到,我们和诗人、诗人和诗人之间,其实是心意相通的:时间或空间的距离,是微不足道的。即是说,诗歌主题、题材选本与同类小说选本相比,地域性的分别往往是不明显的。比如说乡土诗,虽然也出现具体的地名或地方风物,但其在诗歌中往往只是符号性或心象性的存在,只是为表达乡情或为乡愿服务。
注释:
1a比如说东北新华书店(沈阳)编辑出版的工人诗歌选集《钢铁的手》(1949年8月)等。
2a中国青年出版社编:《新民歌三百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第57页。
3b袁水拍:《诗选(1953·9-1955·12)·序言》,中国作家协会编:《诗选(1953·9-1955·1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序言第1页。
4c袁水拍:《诗选(1953·9-1955·12)·序言》,序言第5页。
5a《诗刊》编辑部:《诗选(1949-1979)·编选说明》,《诗刊》社编:《诗选(1949-1979)》(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编选说明页。
6a郑伯奇:《农民诗人王老九和他的诗》,《读书》1959年第17期。
7b《诗刊》社:《诗选(1979-1980)·编者的话》,《诗刊》社编:《诗选(1979-1980)》,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编者说明页。
8a参见蓝棣之的《选编者序》,“本书将所选中、老年两代诗人和新时期开始时年纪尚轻的朦胧诗人群中那些更富于艺术活力、艺术创新和实验的诗人三十家,介绍给海内外读者,希望与本丛书中的‘后朦胧诗选’一书结合起来,为各界提供一个80年代诗坛富于活力和生命力的整体面貌”(蓝棣之选编:《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获奖诗人诗歌选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选编者序第2页)
9b周良沛:《七月诗选·序》,周良沛:《七月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序第27页。
10c周良沛:《七月诗选·序》,序言第2页。
11d周良沛:《新诗选读111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284页。
12a周良沛:《新诗选读111首》,第293页。
13b周良沛:《新诗选读111首》,第293页。
14c《百年新诗选·编选说明》,洪子诚等主编:《百年新诗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编选说明页第2页。
15d李朝全:《编者的话》,李朝全:《诗歌百年经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2页。
16a金性尧:《唐诗三百首·前言》,蘅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2页。
17b况周颐:《宋词三百首·原序》,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原序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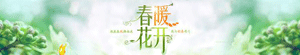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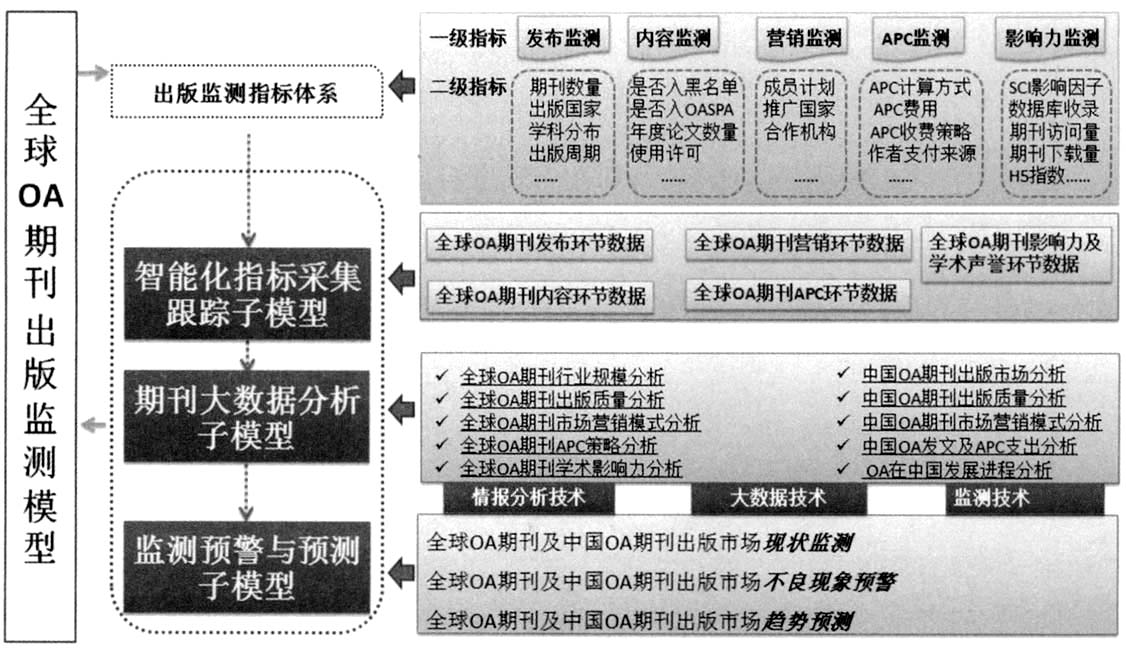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