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延宕三年之久的英国“脱欧”进程已然变成一部肥皂剧的当下,读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以下简称“本书”)一书,倒是显得颇有几分应景的感觉。两百多年前被迫“脱美”的“效忠派”,最后仍在彼时尚是旭日东升的大英帝国之内寻到自己的归宿。不知道今天的英国“脱欧”之后,又能向何处去呢?
打开这本书,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一幕触目惊心的场景,或者用本书作者、美国学者马娅·亚桑诺夫(以下简称“作者”)的话说,是一场“内战”。传统史学往往将美国独立运动勾勒成一场“万众一心”、反抗宗主国暴政的革命史。然而,当时的北美十三州,绝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铁板一块。反对脱离英国统治的群体,被激进的革命者称为“头在英国,身体在美国,脖子应该扭断”的“托利党人”(Tories),而他们则自称为“效忠派(Loyalists)”。按照本书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这个群体在当时的北美洲英属殖民地的白人中占据大约五分之一的比例——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少数。
“效忠派”都是些什么人呢?过去的观点曾经认为,他们只是由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社会上层人物组成,“包括从英王那里获得土地执照的大地主、特权商人、南方一些富有的种植园主以及英王任命的官吏等等,站在英国一边,反对和破坏独立战争”。而本书则以一个事例证明,这些“反动分子”的构成并非如此简单。1776年11月底,“效忠派”在华尔街组织了一场《依附宣言》的请愿活动,期望“迅速恢复(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同盟”。在请愿书上留下自己名字的“效忠派”既有“纽约城里最富裕的商人”这样的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也有客栈老板与木匠这样的普通市民,甚至也有农民。这就意味着,“效忠派”与“革命派”之间,在身份上并不存在一条无可逾越的鸿沟。许多人都知道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协助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政治家、美国建国元勋之一。但本书却告诉读者,他的儿子,时任新泽西殖民地总督的威廉·富兰克林,就是个不折不扣、且顽固到底的“效忠派”。
父子反目、同室操戈当然令人感到无奈。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北美英属殖民地,选择“效忠”还是“革命”,更多的只是理念之争。尽管在独立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维护殖民地的权利可以说是当时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最大公约数”。1776年,纽约的一名牧师查尔斯·英格利斯(Charles Inglis)撰写了一本名为《公正地论述北美的真正利益所在》的小册子,其中指出北美真正需要的是改革帝国关系,以确保北美人的“自由、财产和贸易安全”。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诉求并无不当,至多是比较“温和”而已。然而,革命有自己的规律,一旦爆发便只会越来越激进。于是英格利斯的小册子很快被禁,而他期望“像其他文字一样被世人遗忘的”《常识》(托马斯·潘恩著)却在一年内出售了五十万册,相当于每五个北美人就有一本。“勇敢、果断和永不屈服”的托马斯·潘恩在书中声称,美洲服从英国的殖民统治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北美独立的果实已经成熟,独立的时机已经来到!同样是这位托马斯·潘恩更实际而苛刻地提出,“一个人如果不是各州独立的支持者……就是美国人所谓的托利党人,当他将托利主义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时,他就成了一个叛徒”。
当这样的激进思潮席卷北美的时候,便容不得“求同存异”的“中立”路线了。所有人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参加革命,或者沦为革命派眼里的“叛徒”。一时之间,暴力横行,邻里反目,每个人都被迫在重压之下做出选择。不少被认为是“效忠派”的北美人被施以酷刑,涂上沥青,插上羽毛,当众羞辱。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美独立战争的正当性,在本书所提到的印第安人与黑人“效忠派”的存在之后进一步被消解了。长年以来,北洲殖民地的地主和部分农民连续不断地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迫使他们逐年西迁,殖民地的商人和他们进行不等价交换,骗取他们的贵重皮毛,殖民者还经常对他们无情杀戮,更加剧了他们对殖民者的痛恨。而英王则颁布了“1763年法令”,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亚山以西扩张。这在客观上对印第安人起了保护作用,自然使得印第安人倒向了“效忠派”一方。至于黑人奴隶,他们期望的是以革命为契机,获得自由。由于英军答应给效忠英王的奴隶以自由的许诺,吸引了不少黑人奴隶。按照本书的说法,甚至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名下的几个黑奴也趁机逃跑了。而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居然有多达两万之数的黑人奴隶站在了英军一方战斗。
当然,“效忠派”的努力最后付诸东流,英国人没有赢得这场与北美殖民者之间的“内战”。旋即,“效忠派”的土地被霸占,财产被没收,选举权被收回,就连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获胜的美国人对“效忠派”的报复“已经从温和的舆论批判上升到谋杀的级别”。有鉴于此,那些迫于生存压力的难民不得不选择“脱美”,如同一位“效忠派”人士所说,“让一切从头开始”。
根据本书作者的估计,大约三万六千名“效忠派(包括白人和黑人)”前往今天的加拿大,五千五百人去了加勒比群岛的英属领地(包括巴哈马群岛与牙买加),一万三千人(内有五千自由黑人)的目的地则是英国本土。加上零星前往其他地方的人数自由,“脱美”的总人数就上升到了五万五千五百人左右,但仍然比其他一些研究中的八到十万人要少。从革命造成的紧张环境并由此引发的人员流动来看,美国革命远远超过以暴力闻名的法国大革命。当然,在法国大革命中很多反对派来不及流亡便被送上断头台或是死于战场也是一个原因。无论如何,假如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效忠派”显然是可以载入当代史册的第一批大规模“政治难民”。
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便是用来叙述美国独立以后这些“政治难民”的命运。作者以“自由的流亡者”作为本书的主标题。看上去“自由”与“流亡”似乎是一个悖论。从本书的描述看,书名中的“自由”有一层含义指的是“效忠派”有着选择“流亡”何处的“自由”。书中所举的“效忠派”路易莎·韦尔斯家族的例子令人印象深刻。她的父母早早跑路去了英格兰;哥哥威廉和詹姆斯带着家族的印刷设备去了东佛罗里达;她的未婚夫曾是其父的学徒,去了牙买加。至于路易莎·韦尔斯本人,则费了很大力气变卖剩余家产,经过五个月的航行终于在英国肯特海岸登陆了。但“流亡”毕竟是“流亡”,从经济上看,“效忠派”才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留在北美的财产被美国政府充公拍卖,随身携带的财物也在流亡路途上丧失殆尽。作者提到,一度富裕的贝弗利·鲁滨逊一家四口,只能在伦敦郊外以每周十二英镑的租金住进了区区一个“面包房的一部分”。
可以令他们感到些许欣慰的是,“永失美国”之后,英国政府并没有忘记在战争中曾经做出巨大牺牲的“效忠派”。伦敦方面成立索赔委员会,开始统计“效忠派”所损失的财产,最终付出了三百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三亿英镑),其中那位与父亲反目成仇的威廉·富兰克林获得了数量可观的两万五千英镑。尽管对许多因为“效忠”而失去了一切的“效忠派”而言,五英镑或者十英镑的补偿远远称不上是慷慨大方的,但考虑到当时英国国债也不过一千万英镑,三百万英镑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实际上,在当时也只有英国有能力为战争的受害者做出经济补偿。至于名义上取得胜利的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就很快因巨大的军费而陷入无法自拔的财政危机,并最终将路易十六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实际上,英国人对“效忠派”的救济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不能称之为捍卫大英帝国荣誉的一大壮举。虽然当时的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英帝国在失去北美后即将终结,就像西班牙与荷兰一样。就在美国正式独立的那一年(1783),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就宣布,“英国已降为二流强国”。
另一方面,尽管“效忠派”的流亡地几乎遍布英国及其殖民地,但就像作者所统计的那样,就近抵达加拿大的人数占据了多数。由于人数的关系,也只有移居加拿大的“效忠派”发挥了重大作用。美国革命对加拿大,就如同对美国一样重要。美国革命在创建美国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创建了加拿大。用本书中的话来说,“(美国)革命促成了两个而非一个国家的统一。就在南方建立共和北美的同时,效忠派和英国当局在北方重建了一个帝制北美”。独立战争前的加拿大,仍然彰显出浓郁的法国文化的特色,甚至有英国官员毫不隐讳地称其为一块法属殖民地,其中,卡尔顿爵士(Sir Carlton)的话显得颇具代表性。他说:“就是想一下都让人震惊——这个国家终将被法裔人种主宰!他们扎下的根如此之深,足够湮没一切讲英语的新移民,看来只有一场巨大的变革才可能扭转这种状况。”而“效忠派”的到来正是一场巨大的变革。效忠派的大规模移居,大大地增加了英裔居民的数量。英国政府对那些前往加拿大的效忠派给予了慷慨的物质援助,先是免费提供食物和生活用具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紧接着便以分发土地的方式补偿他们的财产损失。从1783年春天开始,“效忠派”中的一家之长免费获得一百英亩土地,其余的家庭成员每人也分得五十英亩土地。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度过了艰难时期,顶住了北方恶劣的自然条件的严峻挑战,决心“促使英国体制所崇尚的尊重权威、公正、秩序的传统在没有受到污染的新大陆传承下去”。
仅就加拿大而言,本书副标题中的“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自然有其道理。1791年,英国制定了英属北美的宪法,相比之前的北美殖民地,英国派出的总督权威大大增加,他可以否决殖民地立法机关的决定,甚至解散立法机关。以“效忠派”为主的居民对此俯首接受。在作者看来,这实际上是一次成功的利益交换。美国人由于背负着战争债务,赋税负担很重。1790年代的纽约人为土地缴纳的税款相当于加拿大邻居的五倍。因此“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你可以成为积极参政的公民,但为此要支付的也是真金白银。而在加拿大身为英国臣民则意味着接受帝国的权威,但却无须支付高昂的税负”。这块北方的英属领地经受住了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的考验。尽管战前的美国人妄图“把不列颠人从美洲大陆上赶走,我不想止步于魁北克,我要的是整个加拿大!”英军和“效忠派”仍然联手击退了美军。一个“绝对忠君,彻底反美”的英属北美(加拿大)就此在地图上确立了自己的存在。
不过,本书企图让读者相信的并不止于加拿大一隅。在作者看来,“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东山再起”,都有“效忠派”的作用在内。本书提到,“(18、19)世纪之交,效忠派难民散布在整个大英帝国,从再度繁荣起来的英属北美诸省的数万殖民者,到帝国的最远边界澳大利亚的区区几个人”。按照作者的说法,正是纽约出生的詹姆斯·马里奥·马特拉提议将“效忠派”流亡者安置在澳大利亚东岸的新南威尔士“。在政府的保护下,那里有迄今最有利的前景。”问题在于,随后的事实并非按照他的如意算盘在发展,澳大利亚并没有成为“效忠派”的天堂。最终到达那里的英国殖民者是本土的罪犯,而非“效忠派”难民。诚然,这一决定其实与美国革命有逻辑上的联系——原本英国罪犯的流放地是北美殖民地,美国独立之后本就需要另觅他处——但“效忠派”毕竟未在澳大利亚拓殖中起过什么作用。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遥远的印度。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美国的独立标志着“第一英国殖民帝国”的瓦解,继之而起的“第二英国殖民帝国”转而以经营印度为中心。英属印度很快成为经济上最有价值、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的殖民地,或者用更为形象的说法,它是“英国王冠上的一颗宝石”。作者在本书提出,“印度作为高风险但上升空间极大的职业舞台,尤其吸引那些野心勃勃但又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的人,像没落贵族、苏格兰人、爱尔兰新教徒——以及北美效忠派难民”。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里,的确有“效忠派”的身影,就像作者提到的贝弗利·鲁滨逊家族的一位成员就坐船去了印度,而指挥英军与骁勇善战的廓尔喀战士作战,并最终赢得英尼战争的戴维·奥克特洛尼将军同样也是在1758年出生于波士顿,当母系亲戚成为“效忠派”之后便以军校成员的身份前往印度。如果没有革命,这些“效忠派”或许还会安稳地继承家族在北美的产业,但如今他们却变成了印度的乡绅。从个人命运角度而言,作者称之为“失去了纽约,但得到了印度”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历史的进程难道就真的因为英属印度寥寥无几的“效忠派”军人而改变了么?恐怕首先站出来反对这一论点的,就会是从1757年开始就经营着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吧!
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的主标题(“自由的流亡者”)与副标题(“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似乎并不存在很大的关系——至少这种关系不如作者期望让读者相信的那么大。换句话说,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效忠派”“脱美”的历史意义。当然,类似做法,在当今一些英国政客的“脱欧”宣传中,似乎仍旧依稀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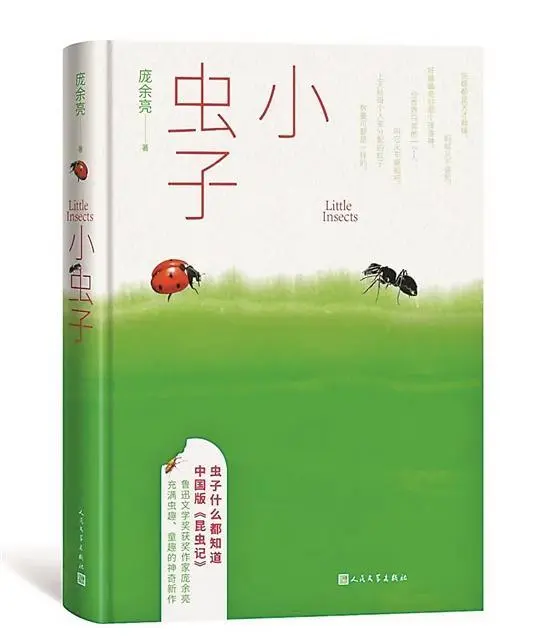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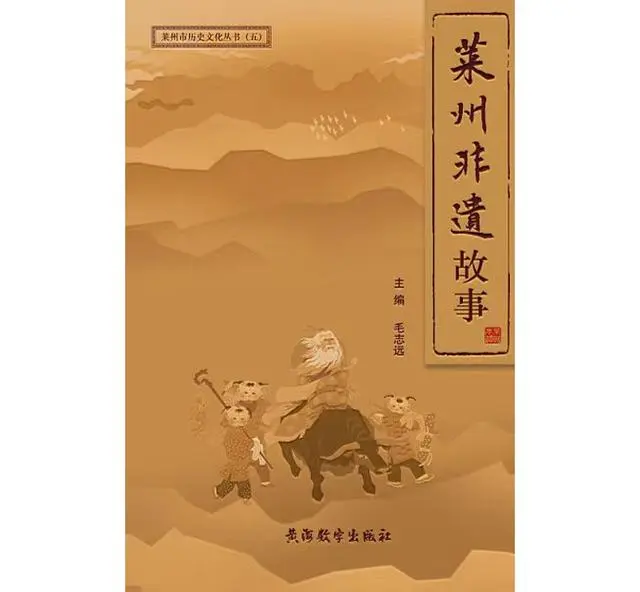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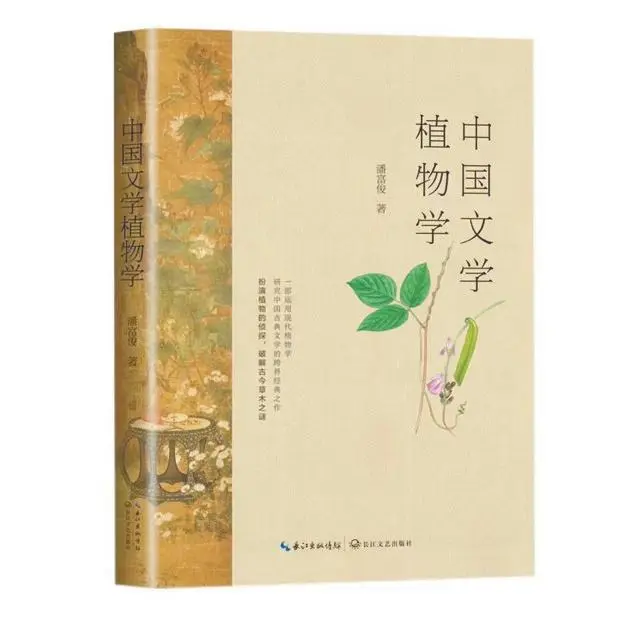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