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出版于1927年)自1987年经陈嘉映、王庆节翻译成中文出版,已经三十二年了。这三十二年间,海德格尔在中国的哲学界一直是所谓显学。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大哲学系,据说历届几乎所有的外国哲学博士论文,不是研究海德格尔,就是研究维特根斯坦。其中又以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为主导,甚至出现过一届博士研究生全部做海德格尔的盛况。在著名知识付费网站中国知网检索会发现,仅在2018年就有三百零五篇以“海德格尔”为主题的论文,也就是几乎每天有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发表。
时移世易,近些年来,对海德格尔的热情明显消退不少。这首先与国内西方哲学研究不断深入有关。这十年,国内学界先后经历了研究古希腊和早期近代政治哲学的两次浪潮,这一势头的最新进展似乎集中在了黑格尔和谢林研究上。这三次浪潮不断冲刷着我们对西方思想的理解,让我们发现了西方许多不同的思想面相。诚然,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为理解海德格尔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但遗憾的是,从国内到国际的“海学界”,都被一些八卦带偏了路。
很明显,这几年关于海德格尔“纳粹问题”的讨论,在不断把海德格尔推到公众面前的同时,也使其本人的名声江河日下。如果说施米特在许多人眼里是纳粹的桂冠法学家,那海德格尔大概就是纳粹的哲学王了。在这些人看来,由于二人与纳粹的纠葛,他们的思想便是“邪恶的”“有毒的”。然而,且不论实践行动与理论智慧的距离,即便海德格尔的思想有毒,他提出的哲学问题是否也不值一提呢?海德格尔围绕“存在”(Sein,或译“是”)的一系列讨论——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自然、存在与技艺、存在与生命是否也丧失了意义?吊诡的是,恰恰是在这些人看来,哲学主要以“问题”,而非“哲学史”为核心,但具体到海德格尔的时候,他们往往罔顾问题,单单瞩目海德格尔的“私人生活史”。
相较而言,来自大洋彼岸——许多人眼中意识形态对立日渐严重、阶层分化日甚一日的美国——的一位哲学研究者,反倒显得更加“面向事情本身”。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1929-2017)的《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Being-in-the-World: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Division I,下文所注均为中译本页码)无疑是一本可以帮助我们从八卦绯闻、秘辛野史制造的迷雾中解脱出来的优秀研究著作。
二
美国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已经有较长的历史。1963年,威廉·理查德森(William Richardson)出版了第一本研究海德格尔的专著《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到思》(Heidegger: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理查德森较为遵循海德格尔对其本人思路的诠释,区分了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在整体思路上更加倾向于海德格尔后期。而他的学生,斯坦福大学教授托马斯·希恩(Thomas Sheehan)则一反其老师建立的经典范式,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理解海德格尔:一种范式转换》(Making Sense of Heidegger:A Paradigm Shift),以《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的意义”问题为核心,完全按照现象学的方式解释整个海德格尔哲学,在欧美现象学和海学界掀起了讨论热潮。
与这对师徒以及他们周围的许多学者(如理查德·波尔特[Richard Polt]、瓦莱加·努伊[Daniela Vallega-Neu]、理查德·卡波比安科[Richard Capobianco]等人)在海德格尔文本之内形成的争论不同,德雷福斯更为注重海德格尔哲学的实践面相。
德雷福斯早年的成名实际上就源于他在人工智能领域对海德格尔和现象学思想的运用。贯穿整个学术生涯,他以海德格尔思想考察人工智能问题,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影响很大。早在1965年,德雷福斯担任兰德公司顾问的时候,他就撰写了一份名为“炼金术与人工智能”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其后他又在1972年以这份报告为基础,出版了著作《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What Computers Can't Do:The Limi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该书也成为了以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讨论人工智能的经典著作。1992年,德雷福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出版了《计算机仍然不能做什么》(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中文学界在1986年即翻译了《计算机不能做什么》,比《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还要早一年。德雷福斯的这些著作集中批判了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模式,后者又包含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两大流派。他认为,传统人工智能学说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还原为一套形式化规则,这种理性主义还原论的做法实际上源于西方形而上学一直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之相反,德雷福斯认为,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原初方式并不是认识与知识,而是实践。人在生活中最为原初的行为不是遵循某些形式化的规则,通过理性反思在头脑中形成规则再付诸实践,而是在具体情境当中与人或物打交道,在这种打交道里理解意义,不断改进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应对(coping)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状况。德雷福斯实践倾向的学问风格也影响了他的学生,据托马斯·希恩(Thomas Sheehan)教授说,德雷福斯的学生中甚至有将海德格尔哲学与医学护理结合起来的。而他许多成名的弟子如豪格兰德(John Haugeland)、奥克兰特(Mark Okrent)在风格上也与乃师保持一致。
德雷福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很明显依赖于他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模式的批判,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笛卡尔式的认识论的批判如出一辙。海德格尔的思考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此在的在世存在优先于认知”(此在,Dasein,海德格尔用来代替“主体”“自我”等传统哲学界定作为个体的人的术语)。海德格尔正是通过描述此在“在世生存”,并在世界之中与工具打交道的原初生命经验,来批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认识论模式。德雷福斯无疑化用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人工智能领域展现了这一思想的穿透力和实际可应用性。而体现德雷福斯对海德格尔思想精深研究的正是《在世》一书。该书是德雷福斯思索海德格尔哲学的集大成之作,我们由此也可以将它视为德雷福斯思想的隐秘核心。
三
《在世》虽然凝结了德雷福斯的核心思想,但它首先是一本对《存在与时间》上半部作注疏式解读的作品。注疏经典著作在中西思想中都有传统,经典著作内在包含的张力及其复杂性使这种注疏非常必要且重要。《存在与时间》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本身包含了许多生僻艰涩的术语、词汇,而由于海德格尔本人试图在此书中重新追问古老的“存在”问题,不可避免地将漫长哲学史中许多重要问题以及不同流派的思想融汇在了一起,这就使得这本书尤为难读。因此好的注疏式著作便更为不可或缺。(现今国内学者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相较国外同行已经相差无几,比如张汝伦教授的《〈存在与时间〉释义》完整解读了整本《存在与时间》,比之德雷福斯此书也不遑多让。)
按照海德格尔本来的计划,《存在与时间》要写成两部分共六篇。在导论第八节中,海德格尔将他原本的规划论述如下:第一部分分成三篇:(一)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二)此在与时间性;(三)时间与存在。第二部分同样分成三篇:(一)康德的图型说和时间学说——提出时间转态问题的先导;(二)笛卡尔的“cogito sum”(我思我在)的存在论基础以及“res cogitans”(思执)这一提法对中世纪存在论的继承;(三)亚里士多德论时间——古代存在论的现象基础和界限的判别式。而实际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只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前两篇。一般认为,海德格尔从1927年到1930年代的一系列讲稿,比如《现象学基本问题》(全集二十四卷),两本康德书,以及关于哲学史的大量讲稿,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计划的展开,甚至1962年的讲座稿《时间与存在》也可以视为这一计划的延续与终结。
显然,《存在与时间》作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完整系统的“著作”,构成了海德格尔一百余卷全集的核心和基础。在德雷福斯看来,《存在与时间》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挑战了传统哲学的五个假定(第4-10页):
一,清楚明白(Explicitness)。德雷福斯指出,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都认为,我们是通过运用规则来认知和行动的,并认为我们应当清楚这些预设的规则,以便能够明智地掌控我们的生活。与之相反,海德格尔则认为,使我们得以社会化的那些人所共享的日常技艺(everyday skills)、辨别力(discrimination)和实践(practices),让我们能够分辨客体,将自己理解为主体,或者一般来说,为理解世界与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海德格尔强调,只有当这些实践保留在背景(background)中时才能起作用。这种保留在背景中、无法被言明的实践称为“存在的领会”(the understanding of being)。对于存在的领会无法以清楚明白,且不依赖于语境的方式被详加说明,从而传达给任何理性的存在者,或在一台计算机中被描绘出来。
二,心灵表象(Mental Representation)。根据传统认识论和认知主义,为了能够感知和行动,并且与客体相关联,在我们的心灵中必须有能够把心灵指向每一个客体的某个内容、某个内在的表象。海德格尔质疑这一点,也就是说,海德格尔不认为经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带有心灵内容(内在之物)的自足主体和一个独立客体(外在之物)之间的关系。这种主客之间的认识关系,实际上以在世存在的、超越主客对立而得到理解的更根本的方式,为先决条件。
三,理论整体主义(Theoretical Holism)。海德格尔否认如是观点:必须有一种关于日常的有序领域的理论,特别是,假定能够有一种关于常识世界(commonsense world)的理论。与之相对,海德格尔认为我们需要返回人的日常活动现象(phenomenon of everyday human activity),停止对内在的/超越的、表象的/被表象的、主体的/客体的等传统对子,以及主体内部如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清楚明白的/默会的、反思的/非反思的等对子变换花样。
四,超然与客观性(Detachment and Objectivity)。传统哲学假设,超然的理论视角优越于有因缘(involved)的实践视角。换言之,只有借助超然的沉思,只有在描述事物和人之前,从日常的实践操劳中撤离,才能发现实在。而在德雷福斯看来,海德格尔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一样,都反对这种观点。
五,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德雷福斯认为,海德格尔反对将哲学活动最终还原到个体主体的活动之上,而是与狄尔泰一样,认为文化的意义和机制必须被看作社会科学和哲学中被给定的基本事物。他认为,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类似,十分强调诉诸对日常社会实践的描述来消解哲学问题。
实际上,不难发现,德雷福斯列出的海德格尔反对的五个传统哲学设定,组合在一起正是笛卡尔哲学中“我思”的形象:为哲学寻找一个确定的个体化的基础,从这个被还原到超然与客观性地位的个体主体的心灵表象出发,以清楚明白的方式建构关于心灵与世界的整体理论。这个略有些漫画化的笛卡尔形象也是近五百年西方认识论哲学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德雷福斯构建的海德格尔哲学的形象,是一个深刻卷入(involve)到日常社会生活中,不会主动在自己与外物之间建立对抗,进而以抽象的原则简化客体,而是直面事情本身的复杂性,从对“存在”的理解出发应对(coping)事情本身的实践者形象。
正因如此,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仍然有一个向来我属的此在存在,但这一此在在德雷福斯看来却是“通透”(transparency)的(80页)。所谓通透,指的是此在通常以一种日常的、四处走动的方式来把握其周围的世界。这种把握被海德格尔称为“循视”(Umsicht,circumspection),也就是说,此在的日常活动是非专题的、非自我指涉的,这些活动中“存在着意识,但没有自我意识”。就此在的通透来说,学界已有许多讨论,德雷福斯的细致之处在于,他非常敏锐地分辨了通透与一个完全透明的机器人或昆虫之间五个方面的区别:(一)循视是一种知觉样式;(二)关联行止(Verhalten,comportment)有适应能力,以各种方式应对情境;(三)关联行止绽露了不同方面的存在者;(四)如果什么出了错,人和高等动物会吃惊;(五)如果行动遇到了困难,我们必定集中注意力,切换到蓄意(deliberate)的主体/客体意向性(83-84页)。正是这五个特点,使此在的行动并不是无心灵的、机械的,不是单纯对世界的反应行动。
相应地,德雷福斯创造了“应对”(coping)的概念来解释此在的活动。应对是构成德雷福斯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在世》开篇,德雷福斯就说,“海德格尔的新路数的基础是一种关于作为一切可理解性之基础的‘无心的’日常应对技艺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mindless’everyday coping skill)(第3页)。此后,他又说,“海德格尔想搞出一种对日常的、非蓄意的、正在进行的应对活动的阐释”(70页)。显然,德雷福斯的应对概念与海德格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化用的“明智”(prudence)和“操心”(Sorge)一脉相承。应对活动就是日常活动中无意识的、正在进行的、针对具体情境所采用的具体应对手段。这种应对活动包含此在对于存在的预先领会,同时也包含此在自身传统和文化中,被给予的那些事实性要素。
但与此在的操心活动不同,应对活动似乎更偏重存在者层面。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海德格尔关于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区分,那么,应对活动似乎是处于非本真状态层面的活动。也就是说,应对活动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消散于世界之中的、正在进行的活动,实际上与此在的沉沦关系更为紧密。此时的此在没有受到良知的呼唤,也没有在畏之中作出决断(畏,Angst,字面意思即害怕,根据海德格尔的区分,怕总是怕某个具体存在者,但畏之所畏是不确定的、非具体的,畏的是在世本身,是“无家可归”),而只是沉浸于对具体事物的处理之中。这种应对活动虽然已经有了对于存在的预先领会,但恐怕尚不自知。就此而言,德雷福斯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完全看作“关于作为一切可理解性之基础的‘无心的’日常应对技艺的现象学”似乎是有失偏颇的。
当然,这里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海德格尔本人思想的张力。在论述“沉沦”的第十三章,德雷福斯充分展现了沉沦问题中的内在冲突。德雷福斯区分了沉沦的结构意义和心理意义:前者指沉沦作为生存论结构,表明此在被从其存在的原始意义那里拖离;后者指沉沦源于此在从畏那里逃离。在德雷福斯看来,“此在在消散中从自身坠落的结构性倾向,甚至是它抵抗这一倾向的失败,都与此在的心理上的诱惑不同,这种诱惑积极地拥抱消散,为的是隐藏其令人不安的无性,即为的是从畏逃遁”(272页)。然而,如果结构性的沉沦源于心理的沉沦,这就意味着此在本质上就是非本真地沉沦于世,本真的生存就不再可能。显然,海德格尔的思考不会止步于此,德雷福斯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在附录关于沉沦的解释中,德雷福斯说:“(本真生存的)决断是如此导致的敞开状态:接受了关于透彻的总体性选择的伦理幻象的失灵,并意识到了自我是无力的和空洞的……此在根本没有进行选择。相反,此在作为揭示存在的一种方式接受了承认其本质性的、空洞的敞开状态的呼声。”(379-380页)很明显,这种接受了存在的呼唤、接受了自己无力状态的此在,恐怕无法去“选择它自己的英雄”(287页),而应对活动也无法在这种此在的活动中取得根本性的地位。
如果说在沉沦于世的社会化生活中,应对活动仍然是此在的主要活动,那么,在经过这一存在的呼召之后,此在接受了自己的无力,转变为一个等待存在来临的空场,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转变,恐怕很难以单纯的应对活动来加以理解。纯粹从实践出发对海德格尔的解释,无疑在《存在与时间》的文本中就遭遇了困难。这也许是德雷福斯没有在此书中对应对活动给出一个明确定义的根本原因。
即便如此,我们会看到,德雷福斯以实践和应对为核心,所描绘的这样一个与传统哲学孤独沉思者形象大相径庭的实践者形象,仍然切中了海德格尔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相。海德格尔之后,以阿伦特、施特劳斯、列维纳斯为代表的不同思想流派,凭借各自不同的思想渊源对实践哲学的复兴,无疑是继承且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的这一面。但仍有必要强调的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没有就此穷尽。
四
在《在世》附录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讨论中,德雷福斯通过比较海德格尔与克尔凯郭尔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
后期海德格尔对于如下问题没有多少兴趣:一个人如何能够发现生活是值得过的,哪怕是在一种虚无主义的文化之中。他所关注的反而是对哲学培植虚无主义的方式进行诊断,并保存尚未屈从于技术至平整化的那些文化实践。拯救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体的文化的可能性,乃是海德格尔后期作品的关切核心。(405页)
与之相应,德雷福斯得出了如下结论:
这些存在领会中的每一个都容许有不同种类的存在者显现。古希腊人在事物的美和力量中遭遇它们,把人作为诗人、政治家和英雄来遭遇;基督徒把受造物作为被恰当归类和使用的东西来遭遇,把人作为圣徒和罪人来遭遇;而我们现代人把对象作为被主体控制和组织以满足它们的欲望的东西来遭遇。或者,最近我们进入了技术的最后阶段,我们把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经验为仅仅为了越来越高的效率而被改善、转变和订造的资源。(402-403页)
显然,海德格尔后期将技术作为人类整体所面对的最大危机,导致他所理解的自然(phusis)在与技术的对立中走向了超善恶的境地。这样理解的自然显然不同于古希腊与习俗相对的自然,这也许才是他写下《黑色笔记本》中许多言论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需要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海德格尔具体政治言论的对错与否,而是海德格尔哲学思想所能展开的世界图景或者政治图景。当他在1930年代中期讨论民族此在,当他讨论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概念以及“争斗”(Auseinandersetzung)“冲突”(Streit)等概念,当他在战后又突然仿佛穿透世事一般谈论“泰然任之”“最后一个上帝”——这其中的思想线索是否一脉相承?还是说,在每一个不同时段,其中仍有许多可能的思想图景没来得及展开?对于每一个哲学研究者来说,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参与到上世纪最大的政治事件所带来的冲突和张力,以及由此引发的他本人思想的断裂与延续,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关心并检讨的。德雷福斯此书显然为这种检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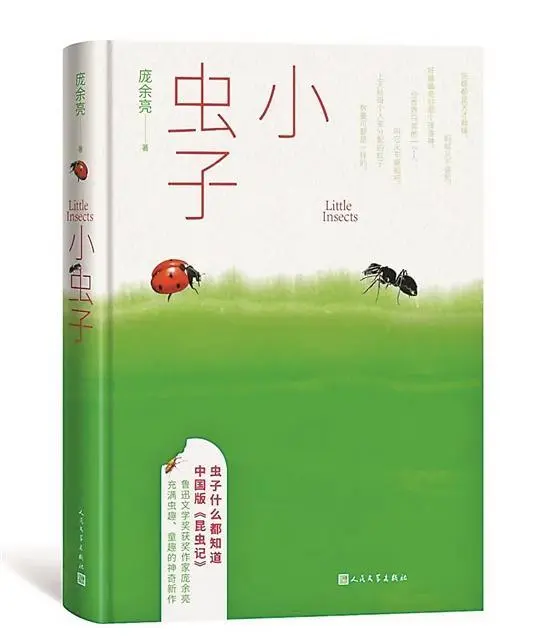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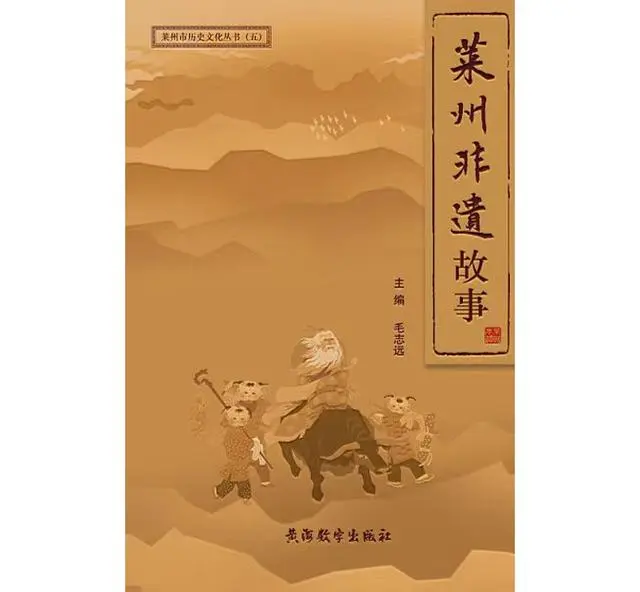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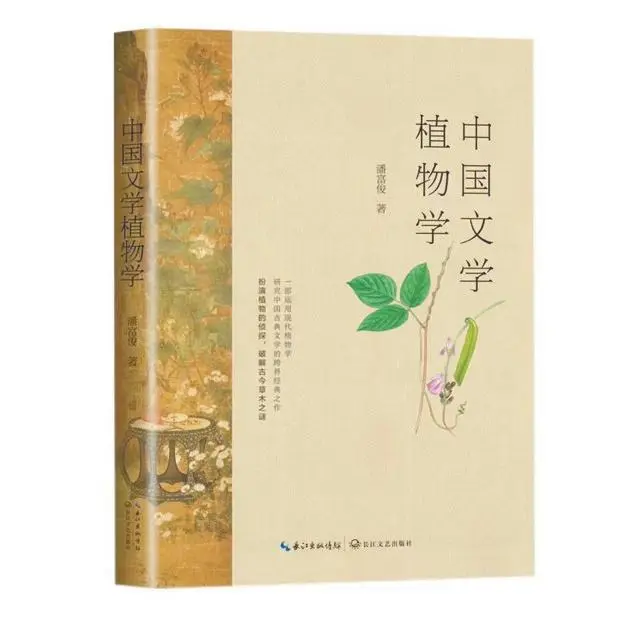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